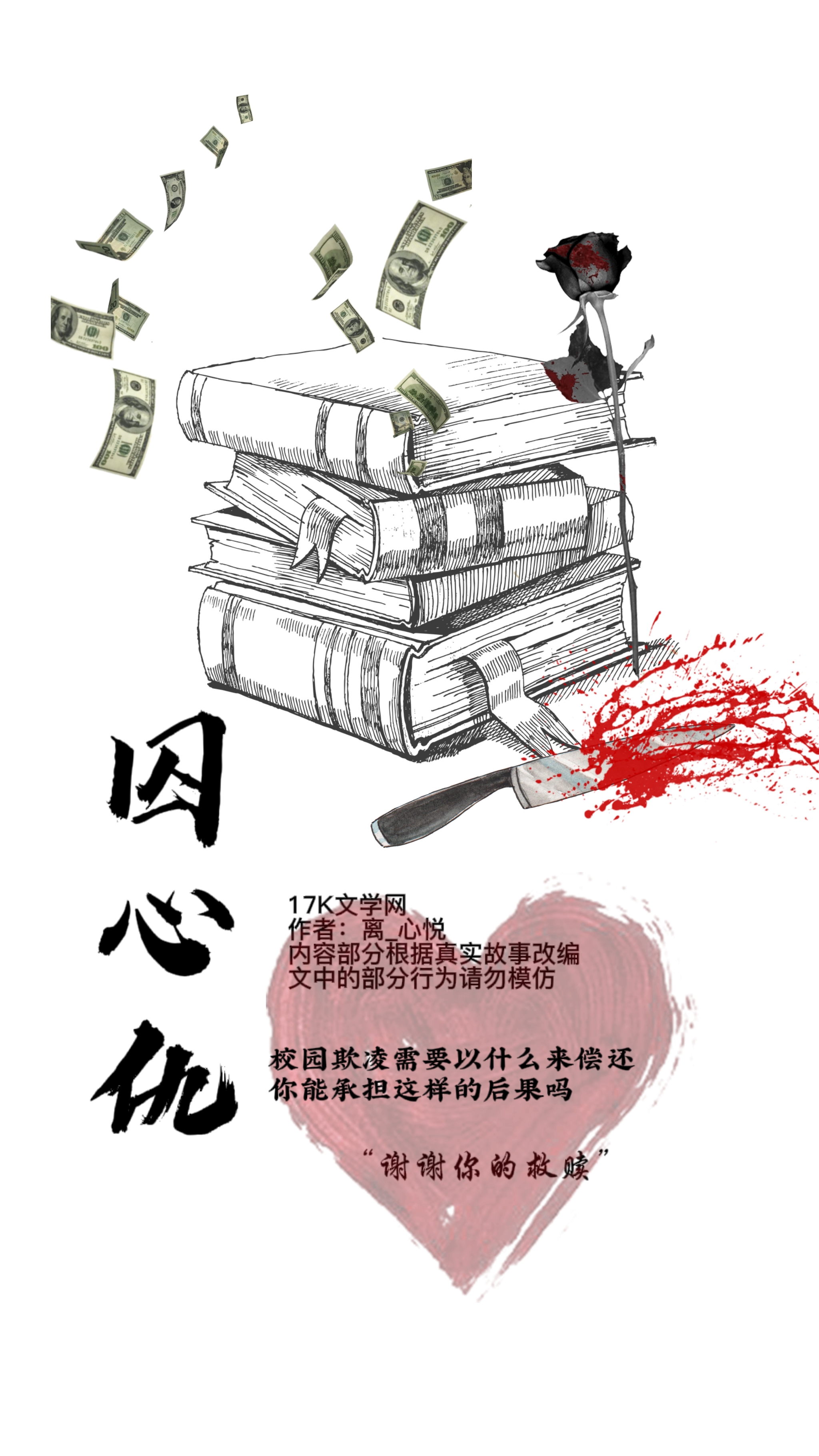此后的日子只剩下灰色,我和含枫还是带着西月云母隐居了起来,我的话很少,常常一个人发呆,含枫总是包容我,对那些事情只字不提,只是细心地照顾我,可我知道,我们之间隔了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裂痕,那便是湘剑的死。我的灵魂如同枯槁的落叶,身体如同虚设的躯壳,日子一天一天过着,平静而没有波澜,转眼就这样过了半年。
回忆充盈着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在满是落叶的季节里,我走在金黄色的小路上,踩着枯槁的落叶,听落叶发出的声声沙哑的低鸣,看不见北雁南飞,看不见黄昏的霓虹彩霞是怎样的光彩照人。
不知不觉走到河边,河边一片萧瑟。脚步声近了,是我熟悉的。
月白色的袍子一角停在我眼前,我能听见头顶他急促的呼吸声,抬起头,他英俊挺拔的身姿映入眼帘,伴随着冲进我视界的还有天空的那片霓虹。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含枫心疼地看着我,修长白皙的手指抬起替我抹去眼角的泪,开口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晨儿,对不起,我今天不该这样着急,我知道你心里痛,但我会一直陪着你,会一直等你。你不要生我的气,更不要流眼泪,好不好?”
含枫一口气说完,我难以置信他会如此卑微的妥协,我想我是明白他的心的,只是一直逃避。可这一次,他又一次将美景带入我的眼中。
含枫还想说什么,我伸手封住了他的唇,我掏出一块薄丝手帕,含枫眼里是一闪而逝不易察觉的黯淡,却是摸着我的头关心地说,“别太晚睡,也要注意休息才好。”
我知道我房间有很多这样的帕子,绣着的都是些荷花,小船,萤火虫,都是我的回忆,他也知道。我看着含枫的样子却是扑哧一声笑了,“你猜我绣的是什么?”
含枫摇摇头,眼睛看向别处。
我将手帕翻过来,上边却是绣着一对鸳鸯。
“这是我为我们绣的,含枫,我想完成半年前的那场婚礼。”我对着他扯出一个微笑。也许,该放下了。
“晨儿,你。”含枫明显一愣,却是别过脸不愿意看我,“晨儿,你不需要补偿我什么,能够守在你身边我已经很幸福,很满足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跟邻居的大娘学刺绣,这块鸳鸯手帕,是她教我绣的。十几年前,大娘的夫君随军远征,再也没有回来,大娘时常叹息,“这块手帕,我原想在他出征前送给他,可是有一片荷叶,还缺了个角没有绣完,我想送他一张最完美的手帕的,却不曾想,再也没有机会了。孩子,你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不是手帕上的荷叶缺了一角,而是爱人就在身边,却没能好好珍惜,而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
而我那个时候,总是执着而又倔强,一次又一次地将含枫的好意拒之门外。
“大娘,我能理解您的感受,我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
“痛,是因为失去吗?那如果有一天,含枫也离开了你,你会怎样?”
大娘的话,我答不上来。每一次,看到含枫为我奔波取药,默默付出,看他隐忍而安静,宁可自己委屈也还是照顾我的小性子,我心里不是不难过;每一个睡不着的夜里,推开门,看到同样辗转难眠的含枫坐在花荫之下,一杯一杯地喝酒,我不是不心疼。也许,真的不应该让一个人的悲伤,夺走两个人的快乐,湘剑,是这样吗?
含枫没有接我的手帕,而我亦站在那里出神,安静的空气中,两个人各怀心事。
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夺去了那张帕子,帕子随风飘扬飞上蓝天,含枫连忙夺步去追。
我的目光随他而去,这时,一个身影闯入眼帘。
人群蠕动的那边,那个熟悉的身影虽只是一闪而逝,便消失在人群中,可我一眼便认了出来。
我的大脑一空,本能地去追,却只能看着那艘载着他的船消失在天边。
“船家,快,往那个方向追。”我抛下一锭银子。
船家看到银子的那一刻眼睛一亮,想到什么,却是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姑娘,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命的问题啊!那个方向,传说是魔鬼的水域,所有去那边的渔船,都是有去无回啊!”
我急得直跺脚,掏出一整个银袋,往船家怀中一扔,
“你的船,我买了。”
前方是结界引发的巨大风浪,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将一切靠近的东西隔绝在外。我抽出宝剑,用力一劈,一股翻腾而来的巨浪将小船卷翻,而我亦被卷入海中,意识渐渐模糊。
醒来的时候,阳光透过素纱布的窗子照进来,他端着药走到我旁边,英气逼人的脸因为阳光的原因温和而安详。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手里的药抖了抖,却是从容地用另一只手接过放到桌上。
“姑娘、、、”
“湘剑,真的是你吗?你还活着、、、”
我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伸手想要抚摸他的面庞,他却红着脸避开了,
“姑娘,我叫阿牧,你认错人了吧?”
“你在说什么?你还在怪我吗?我、、、”
我还想再向前抓紧他,他却是又后退一步,用陌生的眼光看着我,打断道,
“我是阿牧。”
我的手僵在空中,怎样也动不了,我的心像是狠狠地抽了抽,他,把我忘了?
眼前的少年,一身粗布衣裳,一如既往的英俊,可他的眼睛却是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那双眼睛清澈得没有一点杂质,如同琥珀,就像是回到了儿时的那个他,可这双眼睛不认得我,陌生得让我害怕。
我紧紧盯着他的眼睛,多么希望他像以前那样狡黠一笑,“我逗你的呢。”可他没有,他一直奇怪地看着我,像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平静的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们就那样默默对视了三分钟,直到他有些不耐烦了。这时一个风烛残年,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奶奶,你来了。”
“阿牧,你先出去吧。”老婆婆温和地看着湘剑,而湘剑顺从地点了点头。
他转身离去,没有再看我一眼,走到门口时,只是没有表情地说了句,“姑娘,记得喝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