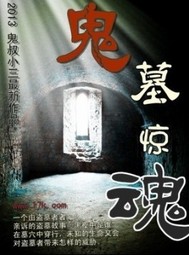再次醒来的时候,我人已经躺在巴车上。
正值凌晨,车上的人稀稀落落,衬得整个车内格外冷清。我的身子斜倚在最后一排,脚搭在坐垫上,左右的位置都空荡荡的。颠簸的车身加剧了脑海里阵阵传来的痛感,支起眼皮,我手撑着从座位上坐起来,视线模模糊糊地看向前面一排,两个熟悉的身影坐在那里。见我醒来,两人纷纷转过头来。
记忆回溯,先前的场景如片段般回放在脑海里。
夜半到警局去盗墓,回来后被人堵在了楼上,千辛万苦地逃出来,逃亡途中,又遇到了一支来历不明的搜查队,之后,我被人打昏了,醒来后就出现在车上。看着前面一左一右的两个身影,我有些明了,敢情是杨冽在我背后搞偷袭,给了我一下。揉揉酸痛的脖颈,抬眼望向窗外的天色。
这一晕不知道过去了几个小时,原本暗沉的天色此刻已经透出了几缕淡淡的光亮,东方的天空渐渐透明起来,黎明的到来让沉寂的车厢里多了一丝生气。
张开嘴,声音有些破碎和沙哑,我咽了咽喉咙,冲着坐在前排的聂远问道:“几点了?”
“四点多。”同样有些偏哑的声音从前排传来,不大的声音在寂静的车厢里却显得格外突兀。我顿了顿,看着窗外的景色再次问道:“我们到了哪里?”
“河北。”
这一次回答的是杨冽,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神情有些空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坐在旁边的聂远默默地抽着烟,表情也严肃得很,却始终没再开口。
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
我见他们俩都一副奔丧的模样,忍不住凑上去,拍了拍聂远的肩膀:“欸,给我也来一根。”
他不说话,只看了我一眼,就从怀里掏出一盒烟,直接扔了过来。我很少见他脸上挂着这么颓丧的神情,立马觉得有些新鲜,想说话,却又觉得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太合适,而且也不是幸灾乐祸的时机,我们都是自身难保,谁也没有资格拿谁来开玩笑。
想到这,我悻悻地靠回了座位上,随手点燃一颗烟,将烟盒扔在了我旁边的空位上。很快,周围便烟雾缭绕起来,我想打开窗子通通风,却发现窗户是死的,上面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硬是推不动,一想到这是长途大巴车,窗户被封也不奇怪,只是一般情况下最后一排的窗子应该都是可以打开的,我有些奇怪地看了一眼,却没有深想。
杨冽坐在前排,样子看起来要比我和聂远镇静,克制力也似乎要比我们强。两边的烟味一阵阵飘过来,他却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连烟盒都不碰一下。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个不沾烟酒的人,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抽烟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顶多纾解一下烦躁的心情,偏偏他这种人活得又很理智,越是这样的情况就越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来逃避情绪。
我掂着手里的烟,心里想的却是,对于我来说,抽烟并不是简单的排解烦恼,而是变相地思考,每次一抽烟我就会发现自己特别有灵感,有些原本想不通的事情瞬间就想明白了,所以我才会喜欢在这种时刻抽烟。说白了,也许就是感觉到那了,抽颗烟,酝酿一下情绪,感觉对了有些事情自然就来了。
我觉得我的这种思考方式很文艺,很类似于一些文人才搞的花架子,但以往的经验却告诉我,这些看着不中用的东西其实很真材实料,而且帮了我很大的忙。
身子微微向后仰,我的脑袋里开始闪过之前发生的片段,半夜突袭的警察,身份神秘的搜查队,我不知道自己遇到了怎样一群人和事,但是看眼下的情形,我确实是开始了一段逃亡的旅程。
没有明确的路线,也没有固定的终点,我甚至在自己还不清楚这是怎样一条路之前就被迫踏上了这条路。
手中的烟几乎燃尽了,我才丢到脚下,用力地踩了两下,接着扭过脸去,继续看窗外的景色。
这一路走的是高速,沿途没有过多的景致,柏油马路在朦胧的天色中像两条大蛇,蜿蜒在车的两侧,不断向前延伸着细长的身躯。我抬头看了看车的前方,那里有一个电子显示屏,上面显示着现在的时间。刚才睁眼时不太清醒,没有注意到,这会再看,时间已经快到五点了。
虽然还未到冬季,天亮的时间却是明显晚了。我盯着窗外半明半亮的晦暗,心里一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所有的一切看似在这里开始了,又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生活似乎一直都是被推动着向前,我的生命里总是时不时地出现一些阻力,这些莫名介入的阻力经常能轻而易举地打破某种看似和谐的平衡。久而久之,我也有些习惯了这种怪异的人生,毕竟哲学上讲,万物都是运动的,运动的内因是矛盾,只要生命在一天,矛盾就不会停止。
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我的生活似乎特别合适,每次旧的麻烦被解决,新的破事就会立即找上门来,生动说明了矛盾是生生不息的这一哲学道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马克思真是个犀利的人,连提出的观点都这么犀利,随便找出一句就是我人生的写照。
车子还在颠簸中向前继续行驶着,到了一处水坑,车身猛烈地晃动了几下,我一个不防,整个人险些被甩出座椅。前方的聂远伸手扶了我一把,顺带着将一个证件塞到了我的手里。
冰凉的硬质感接触到手心,我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张身份证。意外的是,身份证上面的人是我,名字却换了,证件号码也变了,明显是伪造的。我有些惊讶地看了聂远一眼,没想到他连假证件这玩意都准备了,看来还真是有预谋的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