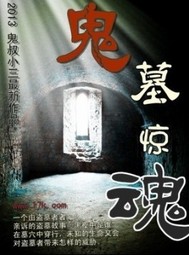聂远走后,我冲过去将沙发上的日记本收起来,锁到抽屉里。可我还是不放心,我看着抽屉上那把普通的锁头,有些神经质地担心起来,万一家里进了小偷怎么办?这种劣质锁头向来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如果有人想撬开,那岂不是轻而易举?对,我应该去买个保险柜。我想现在就去,可又怕一出门就没人留下来看着它了,我不能理解自己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想法,我的神经简直像一根绷紧的弦。
而论起导致这一切的根源,绝对就是那个姓聂的警察。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感到有种无形的压力,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含着质问的意味,他的每一个动作总能牵动我的所有神经。
我这是怎么了?
我明明没有做什么亏心事,那姓王的瞎子也说了,虽然是我给他安排了结局,却也是他命中注定,定数之事,本非人力所能为,又与我和干?我只不过答应了一个恶灵的条件,去按照他的意思写作,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写过什么危害社会的事情。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至于这么做的目的,我承认是为了私利,可谁不想为自己谋利?我写我的,对不起谁了?我何必这样担心和愧疚,即使我不写,现实中那些肮脏龌龊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么?我又不是这些事情的制造者,归根到底,罪魁祸首还不是人性自身的丑陋。
如果说最初的我还因为自己的书给别人造成的影响有过内疚和自责,那么现在的我连最后一丝纠结和怜悯之意也没有了,聂远的到来让我彻底想通了。我不是恶魔,我没有制造黑暗,一切邪恶非自我笔端生成,而是源于众生之心。
我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走到更衣镜前想好好照照现在的样子。如果此时有旁人在场,他一定觉得像极了魔鬼。可惜我自对此己还是浑然不觉,我笑得近乎扭曲地走到那面镜子前,注视着自己的脸,数日之前那种奇怪的感觉再次爬上了心头,这张脸,好像有哪里不对?
我又仔细地看了看,发现大的变化确实没有,不过脸部的形状却好像有了微妙的改变,眉眼也平添了几分陌生。与上次的疑神疑鬼不同,这一次我倒没有多想,只觉得是因为自己成名之后心态变了,容貌和气质较从前有些不同也是正常的。
只是我的神情有些过于狰狞,把我自己也着实吓了一跳。而且也许是因为这段时间躲清闲,太久没出过门,肤色也果然苍白了许多,一看就是那种病态的白。虽然我的模样不见得有多大的改变,但我这张脸,却还是有些让我无法直视的感觉。
这还是我的脸吗?
也许聂远说的对,我该出门走走了,或者是适当地运动一下。
我现在虽然也是全职作家,但我毕竟不缺钱了,花点时间去健健身还是不错的。
如果我能在人生的前二十年里就遇到这个恶灵,那我现在的境遇肯定会大不相同,我的家庭一定很美满,事业和成功,不会像如今这样单身一个人。
说实话,是男人都会寂寞,可我并不是那种随便找个女人就可以打发寂寞的男人,我现在的名气可以让很多女人愿意嫁给我,但我还是在内心渴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想跟我在一起,无论我是贫是富都不离不弃的女人。
这样的愿望恐怕每个男人都有,只是我尤其强烈。前三十年我是一个人过,成名之前的煎熬让我再也不想回到那样的日子里去,我想在我的后三十或者更多年里,能有一位知心的伴侣让我免受从前的寂寞。
可是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尚且能看出谁对你是真情谁对你是假意,一旦成了名,想要找到一个真心对自己的人就变得十分不易了。我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并不打算急着结婚,我想耐心地等,一直等到我命里那位有缘人的出现为止。
而在这之前,我显然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就算身边没有值得长久交往的女人,我至少还可以一次性消费。
说起来,这段时间忙着写稿忙应酬,我已经许久没出去放松过一回了。为了不被无聊的人认出,我戴上黑色的墨镜,特意找了一件长外衣,不顾外面的气温裹在了身上,然后悄悄下了楼。确认没人跟踪,我在拐角处打了的,上车对师傅说:“柳巷路,XX号。”
那里,有我从前常去光顾的一家夜店。
司机暧昧一笑,露出一个明了的表情,随即启动了车子,朝柳巷路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