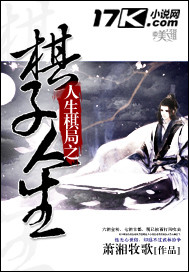入了夜的天空忽然挂起了雨云,窗外愈发地漆黑如墨。
夏侯瑾轩躺在榻上,不知为何竟是难以入睡,兴许是为了谢沧行与暮菖兰这对欢喜冤家,兴许是为了凌波刻意隐瞒的事情,为了晦暗不明的局势……思绪就这样一会儿河东一会儿河西,没有定点,更没有定论,只是睡意却是越来越无影无踪了。
方才院中看到的一幕,他与瑕当真是难以名状地既感叹又高兴,往日里被暮菖兰打趣的小怨恨,一次性“报复”了回来。
可当他们回过神来才想起要问问凌波到底看见了什么突然招呼也不打一声地追了上去,追去之后又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可惜这时已经不见了凌波的身影,连房中也找不见人。
谢沧行登时有些着急:“到底去哪儿了?刚刚告诫她不要擅自行动,竟然……”不会又冒险去探对方虚实了吧?
瑕想了想,说道:“大个儿你别急,要不问问凌音道长吧?如果也不知道,咱们再问去寻她。”
暮菖兰轻轻摇了摇头:“不用问了,我大致能猜到她的去向。”
夏侯瑾轩不由叹气:“暮姑娘也如此想?看来不中亦不远矣。”
“你们两个不要打哑谜嘛!”瑕叉腰不满道。
暮菖兰耸耸肩:“妹子,你不记得咱们前几天在哪里见着道长了?”
瑕一愣,恍然大悟:“道长去见龙溟了?”
“是谁还不一定呢。”暮菖兰忍不住说道,“人家不是拒不承认吗?”
“不管他是谁。”谢沧行皱起眉头,“凌波不是说再没见过他?”
暮菖兰以一种看白痴的目光睨着他:“不见不代表不去,也不代表不惦念。”
夏侯瑾轩叹息一声,感慨道:“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
谢沧行也跟着叹气,刚才只是关心则乱,其实他又怎会猜不到?
瑕却是狠狠瞪了他一眼:“现在是掉书袋的时候吗?”看见他搔搔头,嘿嘿一笑,这才正色问道,“那,咱们怎么办?跟去看看吗?”
夏侯瑾轩沉吟片刻,看了一眼谢沧行:“我看,还是给她留一些时间吧?”
谢沧行抿唇不语。以他的立场,又能怎么回答呢?
暮菖兰轻轻摇头,实在不想绕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问道:“那要不要多派些人手盯着点?不管怎样,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夏侯瑾轩闻言正要点头,又临时改为了摇头:“此事不宜莽撞。若鞑子尚未探明那处所在,贸然增加守卫反而容易露出马脚,中了敌人下怀。”
“这倒也是。”暮菖兰点点头,又道,“想来敌人就算能混进城中,人数也有限。以目前的守备人数,再加上周遭暗桩的数量,应付起来也绰绰有余。”
“更何况每人手中都有信号火弹,一旦有变故,总会有人来得及示警。” 夏侯瑾轩说道,“既已安排妥当,就不要自乱阵脚。”
众人对此都没有异议。他自己自然更加没有,但不知为何,总有些心神不宁。
今夜怕是很难入睡了。
而凌波与龙溟就更是如此。暗无天日的地牢里,连时间都变得没有意义。两人默然相对,连眼神的交汇都被凌波刻意地避开。
突然,厚重的铁门推开来一线,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惊醒了沉默的两人。
守卫紧握着剑柄,一脸戒备地瞄了进来,却只见牢房内两人有志一同地微蹙起眉头,询问似的朝自己看来,不由得怔了一怔,对凌波结结巴巴地说道:“这个……道长这么久没有出来……我们怕出了什么变故,不,不好交代……”
凌波有些尴尬地轻咳一声,力持镇定地回道:“无事。”幸好昏暗的光线帮她藏住了面上的一丝心虚——是否会有变故,可不就在她一念之间吗?
面对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语气,那守卫实在不知该怎么接下去,只好讪讪地退了出去,关上了沉重的铁门,心里头还是觉得莫名其妙,忍不住捅了捅身边的同伴:“喂,你说咱们该不该给盟主报个信儿?”
另外那人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报信?报什么?‘凌波道长和犯人相谈甚欢’?就为这事大晚上的把公子……盟主叫起来?”这人显然出自沈家堡,一时还不习惯沈天放新的称呼。
那守卫一愣,搔搔头,好像是有点小题大做。
那沈家弟子杵着剑席地而坐,露出一副八卦的表情:“嘿嘿,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事儿要是报到公子那里,他一准得把肺都气炸了。”语毕勾勾手,在那守卫耳边低声咬了几句耳朵,见对方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又凉凉地刺了一句:“他不能表现在明面上,一准要找人撒气。记不记得?盟主曾三令五申地命我们绝不可擅离职守,到时候他绝对会揪住这条整的你死去活来你信不信?”
那守卫彻底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