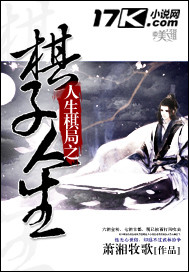对于夏侯瑾轩等人来说,擒住了龙溟,少了他跟夜叉互通有无,事情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真的只是成功了一半而已。因为他漏算了神出鬼没的铁鹞骑悄然加入了阵线。
这也怪不得他,蜀中与关中交战正酣、难分轩轾,谁能想到铁鹞骑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分兵来支援并不落下乘的夜叉王师呢?
不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正是魔翳的高明之处。关中的铁鹞骑得了汉中城,扭转了地势上的劣势,一时半会儿不易被击败。他借此时机挥军东向,一旦剿灭了盘踞河东的关陇义军,与夜叉王师合为一股,再反扑蜀中,届时哪还有不胜的道理?
暮菖兰火速将这消息传往折剑山庄,希望他们可以加紧攻势,若能抄了夜叉盘踞多时的关中,也不枉他们劳心劳力这一遭。
只可惜时间一天天过去,局势却仍不见太大改变,并没有太大突破。
不过这些和龙溟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他独自被关在不知哪里的牢里,一应家俬倒是舒适齐全,只是终日不见天日,与世隔绝一般。
龙溟的心里不是不担心夜叉目前的战况,也不是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可是他更加不愿意让对方看出来自己的担忧,于是无论独自一个还是有人在侧,都会做出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好酒好肉,不问世事,倒是逍遥自在。他时常自嘲地想到。
他至今仍不知道自己身份暴露的确切原因,不过既然无从得知,也就不必再多费心思,倒是该时常反思,自己为何会落入今天这个地步。
一是太贪心,二是太自负,三是……太轻信,尽管极为不想承认这一点。
从那天起,他只见过凌波一次,倒是凌音每天臭着脸,不情不愿地来给他换药疗伤,待伤口结了痂,扔下一瓶金创药就再没了踪迹,连一面都懒得多见。
而凌波,就是在伤好的那一天来的。
那天的龙溟身上还缠着绷带,长发披散在肩头,衣服也不复平整,可说是自从他们相遇以来最狼狈的一次,但神情却仍是一派从容,不见一丝狼狈。
两人隔着小臂粗的铁栏遥遥相对。
他屈起一膝靠坐在墙上,轻勾着唇角,似笑非笑地仰视着凌波:“怎么?他们终于忍不住派你来问话了?”
凌波微微一颤,默默无语,心中仿佛被钝器击中了一般,闷闷地疼。
当一个人对你不住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念着他的诸般不是;可一旦反过来,看着他在自己的推动下如此落魄,又总会无可抑制地记起他的好来。
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呢?如果一觉醒来,发觉这一切都是梦该有多好?
可是她知道这不可能。他们两人每一次的靠近,都有谎言的阴影;而每一次的远离,都是谎言在作祟。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相遇、相识、相知,就如同沙上的堡垒一般。
可是她仍是无法不感到难过。
“不问么?”龙溟轻轻一哂,“那你为何而来?”
干涩的眼已经流不出泪水,凌波隔着一道鸿沟的距离看着他,怔怔地问道:“你……你那时为何要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