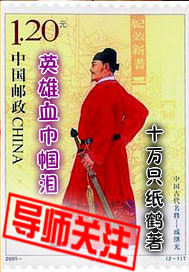“此言差矣。”一人越众而出,他一身纯白滚边的道袍,花白的头发盘得十分齐整,乃是福建泉州紫霞观的天玄道长。紫霞观正是三山五观之一。天玄不顾江北群豪的怒目而视,慢条斯理地说道:“偌大中原,雄兵百万,区区数月便尽陷敌手。以我等蜉蝣之力,贸然出击,以卵击石,实数不智之举。”
“道长莫耸人听闻。”欧阳英不悦,“胡人铁骑厉害,这我们都知道,但我汉人却也未必输了他们!朝廷虽陈兵百万,但安逸日久,一遇敌人自己先溃了,这才如此不堪一击……”
此时只听夏侯彰轻咳一声,欧阳英心中一凛,意识到失言,今日与会者甚众,鱼龙混杂,传出去落下个非议朝廷的罪名可不好,尽管是名存实亡的朝廷也一样,于是忙止住了话头,言道:“总而言之,若我等同心协力,招募乡勇,并非不可一战。”
“就算如此,”天玄道长辩道,“胡人掠夺成性,但所图不过财富而已,日久自会回返,何必劳师动众、多此一举?”
“牛鼻子说的什么鬼话!”挑山帮那个背着扁担的汉子腾地起身,怒视着天玄,“那咱们就该任他们抢吗?死去的妻儿父老,就这么算了?”
“不错,”皇甫一鸣环视众人,铿锵有力地言道,“北伐每晚一日,就要多出无数怨魂,这可是诸位所愿见?”
众人一时沉默。武夷山天心寺方丈双掌合十:“战乱不歇,中原百姓苦矣。”但当战不当战,却也没有明确表示。
眼见惹来非议,天玄一抖拂尘,躬身一礼:“贫道失言,望岂恕罪。但有些话仍是不得不说。北伐之事须当慎重,若事有不成反激怒了胡人,不但江北无法夺回,反而丢了江南。届时华夏烟消,岂非得不偿失?”
此言一出,不少人都沉默下来。
崆峒派的正平道长眼见众人心思摇摆不定,心中怒火开始燃烧,怒目圆睁,骂道:“屁话!你这鼠辈……”
眼看火药味越来越浓,夏侯彰忙开口打断,朗声道:“天玄道长过虑,长江天堑,岂是轻易可破?若胡人真敢来,管教他们有来无回。”
这时一位富商模样的中年人摇头叹了口气:“十年前若说那些只会骑马弯弓的蛮夷小民能够攻陷咱们汉人的坚城深池,有谁肯信?可如今呢?长江天堑,哼,又能有多保险?风险太大啊!”
“正是如此才不该坐守愁城!”皇甫一鸣反驳道,“方今之势,正当以攻为守。若稍加退沮,则人心涣散,长江之险又如何可恃?”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身边的世家弟子们虽然不够身份发言,但也都在悄声议论着。夏侯瑾轩的心思却是越飘越远,在他看来,愿意北伐的就去北伐,不愿意的各归其所,有何可议?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互相攻讦上。
这时眼角余光瞥见暮菖兰三人,夏侯瑾轩凑了过去,拱手道:“瑕姑娘,暮姑娘,谢公子,三位好俊的身手,瑾轩佩服。”
谢沧行嘿嘿笑着接了,暮菖兰忙道“过奖”,瑕见是他,不耐烦地抱怨道:“大少爷你告诉我,这会还要开多久才能争出个子丑寅卯?”瞟了一眼暮谢二人,心道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听得这么认真。
见还有人和自己一般不耐,夏侯瑾轩顿时生出一股亲切感,玩笑道:“也许要争到五脏庙造反吧。”
瑕扑哧一笑:“哎,还以为有什么热闹可看……暮姐姐,不如咱们先走吧?到时候小少爷把结果告诉咱们就行了。”
还未等暮菖兰说话,夏侯瑾轩先叹了口气:“我也想溜走……”
瑕促狭地看着他:“夏侯家的大少爷,这不好吧?”说着朝他身后努了努嘴,“你爹在瞪你了哦!”
夏侯瑾轩慌忙回头看去,然而夏侯彰正忙着关注场中状况,哪有心思管他,不禁松了口气。
瑕失笑,低声嘟囔道:“老鼠见了猫似的。”
夏侯瑾轩有些尴尬地搔搔头,解释道:“自小我爹便待我极严,既要习武,又要经商,甚至还要通晓国政,不然就是没出息、不长进。世人总爱墨守成规,并以此度人。然而人生在世,真的只有这华山一条路好走吗?”
“可看起来这管教没什么成果嘛!”瑕脱口道,意识到失言,连忙摆摆手,“不不,我是说……”
夏侯瑾轩不甘心地反驳:“那是因为我志不在此!”随即顿住,仿佛觉得多说无益似的摇了摇头。
“哎,我这人说话直,”瑕有些愧疚地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其实……”同情地瞟了一眼夏侯瑾轩,“总被逼着做不喜欢的事情,谁都不会开心的。”
夏侯瑾轩笑了笑,没有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