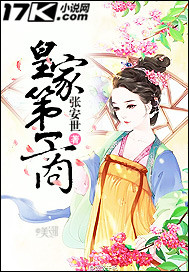求花求收藏
此章已补齐
------
张奉孝有点儿纳闷,这鬼东西无嘴无鼻的,到底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不等他想出答案,就见瘑衣僵一低头,把着火的头发拖入了池底的水中,转眼功夫火头尽灭,池底原本清辙干净的地下河水也跟着变得墨一般乌黑。
张奉孝暗道一声不好,河水由清变黑,肯定有什么古怪。刚要招呼身后诸人小心,姚四爷突然闷哼一声,抢到了他的身前:“磷火弹连水都烤得干,却奈何不了这个畜生。让你瞧瞧这是什么!”
说着,姚四爷探手入怀,取出了一把黑亮油光、细如铅笔的玄色小箭,一抖手射向池底的瘑衣僵。只听噗噗两声,七八支玄色小箭全插在了瘑衣僵胸前白花花的肥肉上,竟然如中朽,未曾见红。
瘑衣僵这下可被惹火了,双臂一震,浸在水中的长发突然甩了出来,像钢丝一般扬向空中,洒出一片墨色的雨滴。紧接着瘑衣僵双腿在池底顿了一顿,拔地跳到了半空中。
众人观之大骇,急忙向后退了几步。水池对面的张政社却等这个机会好久了,暴喝一声,一手握着黑驴蹄子一手持着唐刀,纵身一跃跳到瘑衣僵的头顶,举刀就劈。
瘑衣僵未料到身后还有人,躲闪不及,唐刀正中头顶。
张政社心中一喜,长吸一口气,握着刀柄借力一翻,想落到池底再作打算。哪知一用力,才知道唐刀竟然被瘑衣僵的脑袋给夹住了。抬头已看,瘑衣僵已经落到地上,毫无表情的白板脸面正朝着自己,心里不由格登一下。
张奉孝一见二哥遇险,飞身就要跟下去,不料被夏琳一把拉住,递过来一支亮晶晶的小手枪。这时候也顾不得问她哪里弄来的这东西,举起枪来对准瘑衣僵的后背,砰砰扣动了扳机。
跟姚四爷的小箭一样,手枪子弹也跟射入木桩中一般,瘑衣僵根本没拿它当回事儿,手臂一挥,一束粗如儿臂的头发从水中抽出来,斗然缠到了张政社身上,接着把他甩出去撞在池壁上。
张政社跌得七荤八素,好不容易爬起身来,就见瘑衣僵再次跳起身来,两米多长的千万根头发湿淋淋地在空中甩了甩,洒出一阵乌黑的水滴,淋向池边众人的身上。
张奉孝离得最近,知道众人身后就是龙吟阵的乱石,,前有追兵后有埋伏,一旦退进去当真是有死无生,一念及此,奋力抢在众人前面,抓住了瘑衣僵的一束头发。
入手之处滑腻腻的,像涂了一层护发素似的,张奉孝始料未及,差点让它脱出手去。就在这时,瘑衣僵已经跃上岸来,没有五官的白板脸面,离众人已不及三尺,更显得鬼气森森,令人触目惊心。
张奉孝一咬牙,就想扑上去抱住瘑衣僵,赤手空拳地斗个你死我活。突然间腰间一紧,低头一看,脚底下已经被头发盖得严严实实,心中一惊,回头就看到张赢川夏琳等人都被瘑衣僵缠成了一个大线团,只留脑袋在外面挣扎。
张奉孝长叹一声,难道头一回倒斗就要被粽子缠成冤鬼?
就在此时,远处突然有人厉喝一声:“张老三,铣铘刀!”
铣铘刀?张奉孝一愣神,顿时知道了身后那人就是蔡叔,他所说的铣铘刀,自然就是送给自己的那把匕首。可是,二哥手上的唐刀是祖传之物,张三链子当年就曾用过,它都不伤不了瘑衣僵分毫,这铣铘刀难道能管什么用?
蔡叔被姚四爷一掌砍晕在地,没过多长时间就醒转过来,怕被众人发觉,一直都在装死。只因为情势紧急才忍不住出言提醒,这时见张奉孝还在**,忍不住骂道:“小兔崽子,还不动手,留着给粽子当点心啊?”
张奉孝从知道蔡叔曾经害过自己的徒弟,心里就对他有了莫名的恨意。当初送自己铣铘刀,只怕是想收自己为徒,为了收买人心而已。只不过情势紧急,这时也顾不上计较太多,一弯腰,伸手去拔小腿外面绑着的匕首。
这时瘑衣僵的长发已经把他的双腿都缠住了,匕首自然也被裹在里头,张奉孝急切间拔不出来,急得出了一身大汗。
池底的张政社浑身都像散了架一样,硬撑着爬到雕着九爪青龙的玉柱上,却再也无力跳起来去抓半空中悬着的铜索了。这时见众人遇危,咬着牙关骂道:“畜生,有种下来让二爷再砍上一刀!”
瘑衣僵不知是活物还是死物,听他这么一骂,竟然扭头看了一看。张奉孝陡觉缠住自己的头发略微松了一松,哪肯放过这稍纵即逝的机会,狠命抓住刀柄往外一拔,竟连刀带鞘一起从头发里拽了出来。
情势危及万分,被头发裹在当中的众人,除了姚四爷还露着脑袋,其他人在缠成一团的乱麻堆里拼死挣扎,幅度越来越小。张奉孝抛掉刀鞘,铣铘刀在腰间一划,割掉缠着的头发,和身扑到了瘑衣僵身前。
瘑衣僵刚回过头来,没有五官的怪脸离张奉孝已不足三寸。张奉孝一闭眼,也不管这究竟是什么怪物了,反手握着铣铘刀,狠狠地插在了它原本是两个眼睛的凹窝中间。
这一刀来得凶狠,张奉孝本以为唐刀都劈不开这怪物的脑袋,脸皮定然也结实得很。没想到入手之处竟然软绵绵的,一下子贯通到底,铣铘刀近一尺长短的刀锋齐根没入。
瘑衣僵肚子里一声沉闷的惨呼,下巴上面紧绷的皮肤竟然慢慢裂开了一道口子,渗出一股红中带绿的血水,张奉孝喉头一阵抽搐,恶心地差点当场吐出来,
瘑衣僵脸上的血口越来越大,一直裂到了被头发盖住的耳根旁边,像起来整张脸就像被砍成了两半。张奉孝心中惊骇,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刚站稳身子,就见瘑衣僵突然仰头一声大叫,接着身子往后一倾,带着万千长发,又跌回了水池之中。
被黑发缠在里面的几个人,此时已是精疲力竭憋闷欲死,陡觉身上一松,再也支持不住,纷纷摔倒在地。
张奉孝暗道一声侥幸,只可惜锒铘刀插在瘑衣僵的脸上,又取不回来了。好在见众人已经脱险,心里不免有点小小的得意,回过头去,想看看瘑衣僵死透了没有。
这一看不要紧,张奉孝又惊出了一声冷汗。瘑衣僵虽然受了重创,却是百足之虫死而未僵,退到金棺之中还不死心,竟然又甩出一束头发,缠住了玉柱之上的张政社,死命地往棺材旁边拖。
张政社刚才被瘑衣僵那一摔,此刻浑身半点力道也无,不但拉扯不住,连嘴鼻都被它的头发缠得死紧,不能出声相救,眼看就要被拖进金棺之中。
张奉孝又急又怒,来不及告诉姚四爷关于蔡叔已醒的事儿,飞身而下扑到了金棺之前。瘑衣僵似乎有点忌惮这小子,断成两截的脸面疯狂的左右摇摆,往后缩了缩身子,仍不肯放弃张政社。
张奉孝强忍着恶心不去看它血淋淋的嘴脸,伸出左手抓住它脑袋上的一楼头发,右手摸到刀柄,扑的一声***,又在它脸上狠狠捅了几下。
瘑衣僵哆嗦着放开张政社,突然抬头从两截脸面的中间喷出一股又腥又臭、黄中带绿的脓血,接着全身骨骼格格乱响,缩成一团倒在棺内,算是彻底老实了。
张奉孝闭着眼,根本没防备它临死之前还来这么一手,顿时被脓血喷了一头一脸。伸手一摸,粘乎乎的腥臭难当,喉头一痒,张嘴呕了出来。
张政社喘了几口粗气,慢慢爬起身来走到张奉孝身边,拍拍他的肩膀,长叹一声:张家门里又出了一条响当当的汉子,破除血咒应该有望了。
张奉孝撩起衣角,把脸上的脓血胡乱擦了擦,站起身来扶住二哥,知道他刚才失手被瘑衣僵摔了个四脚朝天,心里肯定不舒服,刚想宽慰两句,就听池底深洞中传来一阵虎吼般的叫声。
这可就怪了,地下一百多米深处,难道还有老虎?
地下荧光棒时间久了,光线已经黯淡下来。张奉孝只好再让秦琪儿抛下一根,折亮了走到洞口边上,想扔进去瞧瞧底下有什么鬼东西。
离洞口还有两步之远,张奉孝突然浑身一抖,尾椎骨像被扎了一针,钻心地疼。张政社低头看看自己的左手,先前跟瘑衣僵死磕时抖得厉害,现在可没有什么异样,应该不会又是粽子。
这次疼起来跟长时间喝酒可没关系,张奉孝自己很清楚,在学校的时候往往三两个月才自己偷偷买上一瓶,跑到校外过过瘾,也没这么发作过。这次进金花公主墓,在借住的房东家里刚喝过半瓶,旧疾发作得不应该这么快。
池上面站着的张赢川突然脸色大变,疾声厉喝:“老二,快把他弄上来!”
秦琪儿这时突然想起,未进金花公主墓之前,在那碰到过虎蛟的溶洞中,张赢川曾经说过一句话,张奉孝身上的麻烦比自己还难缠。自己这离恨斑就够让人受得了,当时就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事情一件件接连发生,连张口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看张赢川如此紧张,应该就与这句话有关了。
张政社一愣,立即想到怎么回事,随即俯身把张奉孝拦抱起,腾身站到了洞口旁边的玉柱上。只是现在没有了悬棺,断掉的铜索吊得又高,若是一个人还可以跳起来够得到,两个人实在一点办法也没有。
张赢川天生脚力快,膺力却只平常,看了看姚四爷,希望他能出手相助。
姚四爷脸上似笑非笑,一眨不眨地盯着张奉孝看了半天,呵呵笑了几声:“好苗子,真是好苗子。除了胆子小一点儿,呵呵,若不是张三爷欺老夫在先,还真有收他为徒之心。张老大,你张家这老三,以前跟谁学的功夫?”
张赢川皱了皱眉,显然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夏琳在一旁看得清楚,伸手拉拉姚四爷的袖口,低声道:“师父,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想不开呢?张三爷纵横倒斗界的时候,你不是刚总角嘛,张三爷也料不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有将他比下去的志向。算了算了,这事儿慢慢再说,先把他救上来再做打算才是。”
姚四爷脸上看不出是喜是怒,点点头,飞虎爪摔出,在张奉孝腰间捆了几道,然后振臂一拉,竟把一百五十多斤的张奉孝直扯得飞到了井沿之上。
张政社回到金棺旁边,把插它乱糟糟一身乱发里的唐刀拔了出来,又捡起张奉孝扔在地上的铣铘刀,回身准备借助那两根玉柱跃出水池,刚走到池底中间的大洞旁边,突然从里面又传出一阵虎吼之声,不由又起了好奇心。
先前张奉孝曾经扔进洞里一根荧光棒,张政社借着它的光亮探头往里一看,脸色大变,二话不说回头就跃上了身旁的一根玉柱。
说时迟那时快,洞里虎吼声未绝,洞口突然窜出一只铁青色的大虫子,足有暖瓶粗细,一张嘴,满口的利牙撕住了张政社的裤脚。
张政社右腿猛蹬,没料到这虫子虽然个头不算大,牙口却是极好,一旦咬住了死也不松口,怎么也挣不脱。这时也顾不得许多,张政社右手唐刀一抡,疾劈而下,登时把怪虫从中斩作两截。
虫尸前后两截啪啪落在地上,黄绿相间的粘液溅得到处都是。张政社离得近了看得清楚,那虫果然怪异,像极了大号的蛆虫,头大身子小。脑袋上生有一层层的硬皮,足有狗头那么大,嘴一咧,露出一圈圈的利牙,竟然里外三四层之多。
张奉孝尾椎骨疼痛慢慢减了,站起身来走到池边往下一看,张政社正要纵身跳上玉柱,斗然间虎吼声大作,从洞中嗖嗖嗖又飞出几只怪蛆,直扑张政社后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