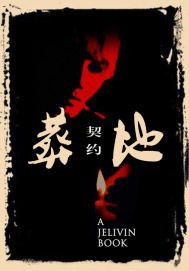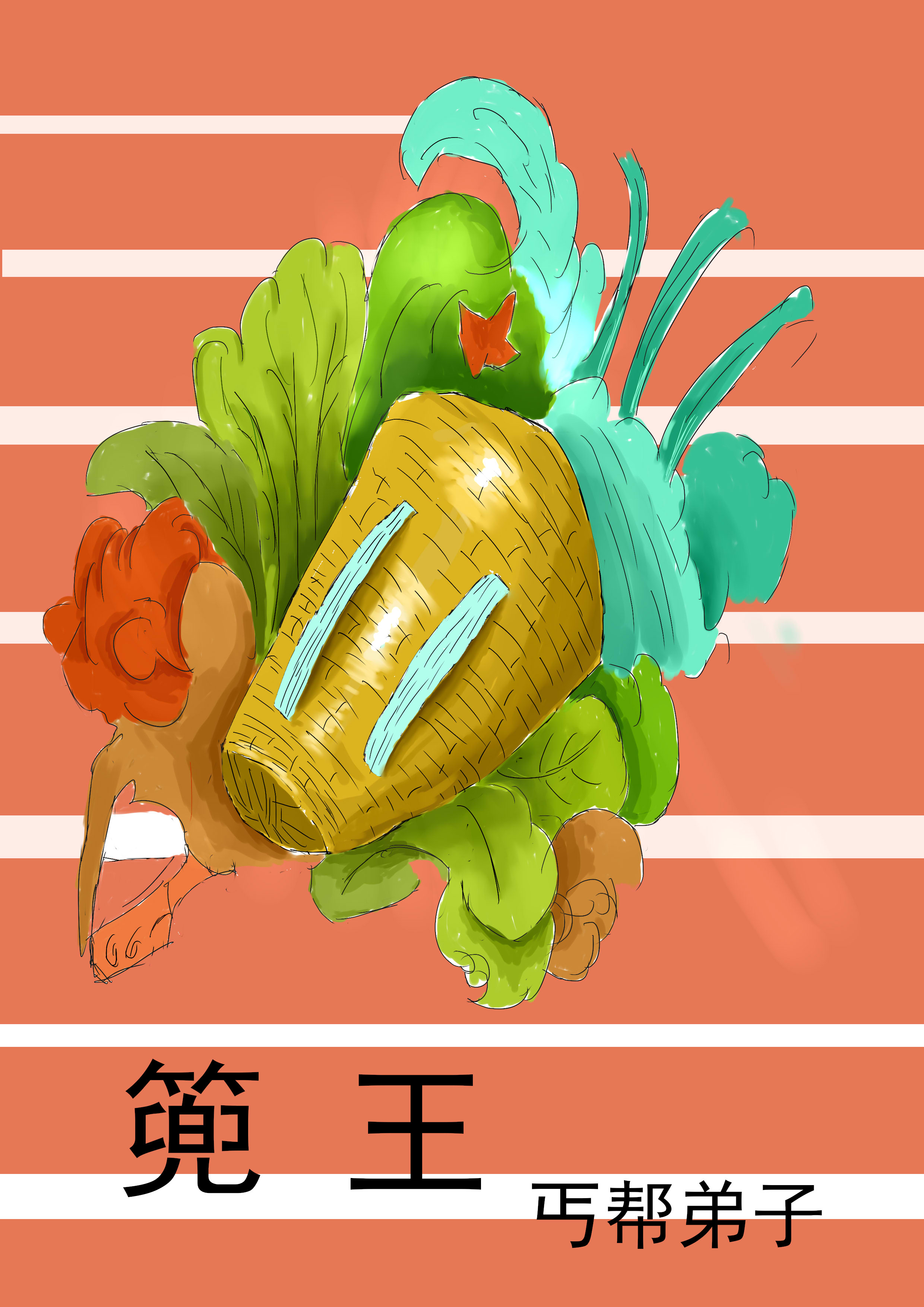张奉孝见变故陡生,抢在张赢川秦琪儿二人身前,扬手接住二哥抛过来的唐刀,接着向前一纵,一步不停地踏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块墓砖,窜到了张政社身边。
秦琪儿也想跟过去,被张赢川一把拉住,额头上急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儿:“大哥,二哥他……”
“不妨事,是旧病又发了,”张赢川轻轻叹了口气,张政社这病发作起来,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更不分场合,“这病一发作起来,神智不清。他是怕唐刀伤了自己,所以扔回来。往墙上打那一拳,也是想借着疼劲儿镇静一下,不用担心。”
秦琪儿咬着嘴唇,见张奉孝猛然把张政社扑倒在地,压在膝盖底下,吓了一大跳:“大哥,二哥这到底是什么病?我怎么从来没听奉孝说过?他……对了大哥,在溶洞中的时候,你曾说过张奉孝也有一堆麻烦,究竟怎么回事儿?”
张赢川算算时辰,眉头一皱:“现在还顾不上说这个,往后也许会出现转机,慢慢再告诉你吧。好了,先把老三那袋酒找出来,时候也差不多了。”
秦琪儿满腹狐疑,见他面色沉肃,也不好追问,依言找出羊皮酒袋,递了过去。张赢川接过酒袋,咳嗽了一下,沉声喝道:“老三!”不等他回头,手一扬,酒袋凌空越过墓道,飞向张奉孝。
当时张政社抛唐刀捶石门,张奉孝心念一转就知道他是病发了,怕他神智不清惹出麻烦,所以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哪知刚把他压在地上,就感觉自己尾椎骨突突地跳了几下,一阵钻心的疼痛顺着脊椎瞬间传遍了全身,立时浑身发抖。
张奉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两兄弟竟然同时发病,正咬着牙苦忍。听到大哥招呼,抬头一看,张奉孝心中一喜,腾出一只手接住酒袋,用牙拧开塞子,咕咚咚喝了几口。火辣辣的高梁烧刀子顺着喉管灌下去,扩展到四肢百骸,先前酸痛欲裂的感觉立即消失不见。
张政社也慢慢安静了下来,趴在地上不停喘着粗气,张奉孝慢慢抬起膝盖,把酒袋塞好挂在腰间,抬起头来看那玄黑色的石门。一看之下,立即明白了刚才二哥为何脸色铁青,心底猛然也打了一个突,忍不住回头瞧了瞧站在墓道对面的张赢川和秦琪儿。
不知是制成石门的石头本身就是黑石,还是后来在后面涂了什么东西,张奉孝一眼就看到,玄黑色的底色上,纵横各刻着一十七道白线,正是一个围棋的棋盘。棋盘上纵横线相交之处,错错落错的还凸雕着数十颗黑白分明的棋子,显然是盘没下完的弈局。
这些都还好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不论是张政社还是张奉孝,对围棋都不陌生。令两兄弟心惊肉颤的,是在棋盘左右两侧刻着的字迹,一望便知是利刃所刻。只是,左边十个字苍劲有力,从上到下布局分明——张三链子破烂柯局于此。而右边只有八个字,忽深忽浅,刀锋凌乱,显然是怒气勃发时所刻——张家无善,亦天意乎?
张赢川见他看过黑色石门之后脸色古怪,知道其上必有玄机,侧耳听听墓道之下再无异声传出,一咬牙,让秦琪儿留下,自己踩着十块地支墓砖到了石门之前,一看之下也不由脸色一沉。
张政社慢慢直起身来,伸手指着棋盘左侧一行字叹了口气:“老三猜得不错,张三爷果然是在这金花公主坟里栽了根头。左边这行字,自然是张三爷破了传闻中的烂柯名局,刻字留凭。右边,可能是吃了大亏,退出古墓时的泄愤之语。如今咱张家三兄弟,进,还是不进?”
张奉孝当然听说过什么是烂柯局。传说,晋朝时有个叫王质的人上山砍柴,来到了石室山,见到两个童子在下棋,他把砍柴的斧子垫在屁股底下,坐下观棋。一童子给王质一个像枣核的东西,王质含在口中,顿时觉得肚子不饿。王质观棋入了迷,看了很久。此时,下棋的童子对他说,你为何还不回家。王质站起一看,砍柴的斧头已经烂得不成形了。王质匆匆赶回家,村庄已完全变了样,和他同时代的认识的人一个也没有了。王质当即赶回山中,拜两位仙童为师,当神仙去了。这个传说演变为“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两个童子所下的棋局,即是传说中的烂柯局。
张赢川冷冷一笑:“张家大爷刨了三十年孤坟野冢,既然来了,不进去瞧瞧金花公主长得何等模样,岂不抱憾终身?老三,张三爷既然留字为凭,必须在棋眼上做了记号。这烂柯局就是进墓门的钥匙。”
张奉孝点点头,颗颗看去,终于发现一颗黑子之上,有一个用刀刃刻成的小小“张”字。这颗黑子周围,围了四颗白子,四口气全被堵死,显然是颗死棋。张奉孝有些纳闷,既然是一颗死棋,怎么还会摆在棋盘之上?难道这棋子并不是雕刻出来的?
一念及此,张奉孝伸手试了试,黑子果然被轻轻提了出来。张赢川看得分明,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这千古烂柯名局,必先蹈死眼,置绝地而后生,方才破解得了。那么,这黑子所在之处,定然就是机关的关键所在了。
张奉孝按着大哥的吩咐,把黑子旁边的白子也提了起来,把黑子放回原位之后,又把白子放回。白子刚一着盘,三人就听到门后扎扎之声响起,知道摸对了门路,赶紧向石门两边迈了一步,以防门后又有长刀暗箭之类的机关。
哪知等了半晌,轧轧之声渐不可闻,石门却并未打开,紧闭如故。张赢川摇摇头,又把眼光落到了棋盘之上,猛然脑海中灵光一闪,脱口而出:“张三爷看走眼了,这不是烂柯局,而是四灵二十八宿盘!”
见二人还不明白,张赢川只得把三垣二十八宿解释开来,以备张奉孝日后万一用到。原来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星或二十八舍,是古人为了比较日月金木水火土的运动而选定的二十八个星宫,东南西北各有七宿。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二十八宿解说明白,张赢川指指中间那一黑一白两颗棋子,道:“你们看这棋枰,纵横都是十七,而不是十九。按说,魏晋南北朝之后,通行对弈之盘,皆取纵横各十九,凑足三百六十一周天之数,这金代的古墓,却用这样的棋枰,实在说不过去。这一黑一白两颗,应该是辅官星和辅座星。唐代二十八宿包括辅官和辅座,金在唐之后,沿用此俗也在意料之中。”
张奉孝恍然大悟,接着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算张三爷看走眼了,以为这是传说中的烂柯残局,怎么会进得了金花公主墓?”
张赢川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思忖了半晌才缓缓说道:“我也不明白。刚才移动黑白两子,门后有机关触发之声,倒好理解,毕竟是二十八宿中非常特别的辅官和辅座星。可是墓门并没有打开。看来,墓门开启之法另有玄机。”
三人一时毫无头绪,四下里打量着墓道中的石人石马,终究想不出机关消息所在。张赢川背负双手,回到棋盘之前,默默想了想,又道:“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只不过有点玄,未必管用。”
张奉孝突然心中一动,猜到了大哥的意思,只是想了想实在太过匪夷所思,到嘴边的话又吞了下去。张赢川点点头:“你既然也猜到了,就说出来吧,看看跟我想的是不是一回事。”
张奉孝指指棋盘:“二十八宿也好,围棋对弈也罢,其实都脱不开周易的底子。二十八宿周天循环,内有不测之机。而围棋,局方而静,棋圆而动,以法天地,世无解者,这是传说围棋的发明者尧帝所言。围棋的棋枰,据说源自《洛书》,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八个方位星、周边七十二个交叉点与三百六十周天、八卦、七十二候相应。近代的围棋大师吴清源也认为围棋本不是胜负之争的游戏,而是占卜天象易理的工具。所以,墓门的开启必定着落在周易术数之上。”
话音刚落,张赢川还未置可否,就听墓道另一边的秦琪儿大声叫道:“你们三个聊得热闹,我可要跟着过去了。”说着,抬腿就往第一块雕着“子”字的墓砖上迈。
张奉孝一看到秦琪儿,再看到地支十个字,顿时如醍醐灌顶,厉喝一声:“回去!”
秦琪儿吓了一跳,以为他看到了什么危险的地方,赶紧把伸出的腿又缩了回来。张赢川和张政社也不明所以,疑惑地等他给出解释。
张奉孝搔搔脑袋,指指十块墓砖:“天干地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不用说了。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正是十个字。金花公主坟里,以地支十字刻在墓砖之上,又有十子同进十子同出的传说,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关键所在。”
张政社也终于听明白了:“老三,你是说,这十块墓砖,正对应着十个儿子的传说。若是足数,十个儿子一人站在一块墓砖之上,触发机关,墓门就会打开?这可就怪了,当年张三爷倒斗向来都是孤身一人,从不带伴当,又是怎么开的幕门?”
“不是一人占一块墓砖,”张奉孝摇摇头,皱着眉缓缓说道:“是要从这一列地支墓砖之上,按地支的顺序依次走过十个人,墓门才会开启。先前我们三个踩在上面,墓砖之下传出的扎扎之声,就是机关开始运作。现在还差七个人,才能让机簧走到尽头,开启墓门。张三爷当年,必定是想出了解决办法,才进了墓门。”
“如果墓砖旁边的石板上没有机关埋伏,从墓砖上走过来,从石板上再回去重走一遍,倒也是个办法,”张政社嘿嘿一笑,“可惜偏偏石板上就有埋伏。看来当年设局之人,果然耍的好手段。不过,既然张三爷能进得了墓门,就必定是瞧破了他手段之中的破绽,更显高明。”
三人站在墓门之前,追思当年张三爷孤胆入墓、破消息除机关之神采,不由暗叹一声。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三兄弟联手,竟然不如张三爷一人之力。再想到就连张三爷的风范,也没能在这金花公主墓里讨好了去,只怕自己四人能不能全身而退都成问题。
秦琪儿在另一边等着焦躁,忍不住又大呼小叫起来,说明明答应进了古墓绝不抛下她一个孤身女子,这倒好,还没进去呢就放自己鸽子。
张政社舔了舔嘴唇,苦笑道:“要不就让这丫头过来吧,好歹多一个人。实在不行,这石人石马虽然精巧,毕竟是个死物,拼着一死,我从石板上走回去试试,也未必就不能杀出一条血路。”
张赢川冷哼一声:“未必只是动刀动枪。这石人阵势古怪,莫说是你,数百年前的摸金校尉,哪个身手错得了?别人不说,张三爷都不敢轻迎其锋,要不然,石人石马还能如此完整?”
难道还没进古墓就寸步难行打道回府?张奉孝不信这个邪,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在墓道正上方中间的顶壁上,嵌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仔细一看,不由喜形于色:“大哥二哥,快看,张三爷留下的飞虎爪!”
“真是百密必有一疏,当年设机关的高人,什么都想到了,愣是把最简单的路疏忽了,”张奉孝嘿嘿一笑,从背包里摸出一盘登山绳:“连牛顿那样不世出的天才,小时候还犯糊涂,给一大一小两只狗开了一大一小两个洞呢。二哥,接下来看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