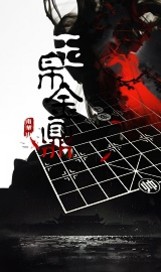张赢川脸色阴沉,摇摇头:“不知道,这死东西有点儿门道。老三不懂这个,你看着他点儿。你也别大意!”
张奉孝有点诧异,自己回家路过坟场的时候碰到过这只黑猫,听大哥这么一说,似乎它不止跟自己过不去,还缠上了大哥,怪不得大哥身上枯草烂叶,一身狼藉呢。可为什么当时黑猫朝自己一扑不中,立即就退走了呢?
这时也来不及多想,张奉孝见二哥手上血流不止,赶紧进里屋找了根布条,从酒缸里舀出点儿高梁酒蘸蘸,过来给他包扎伤口。张赢川哼了一声,快步走到跟前,瞧了瞧野猫留下的爪痕,摇摇头:“别用酒。老二,蒿叶还有,烧点灰洒上,别碰铁器。”
张政社答应了一声,突然抬起左手,掌心向上,仔细地看着。张奉孝不知就里,心想难道是二哥左手也受了伤?凝神一看,只见张政社左手多出来的那只小指突突突地跳动起来,越跳越快,二哥的脸色也越来越青。
张政社紧咬着牙关,手指并起,把跳动的小指压在下面,眼中一道青芒转瞬即逝。张奉孝刚叫了一声二哥,就见他闷声叫道“又来了”,猛地前冲一步,一脚踢开房门,右手闪电般成爪形伸出。
倏出倏退,张奉孝只听得一声惨叫,二哥已缩回胳膊,右手虎口里紧紧卡着一只黑猫。黑猫身子拼命扭动,眼睛里闪动着伸缩不定的绿光,狠狠瞪着张政社。张政社原本蜡黄的脸面已青得发绿,根根青筋暴起,胸口起伏不定,像是有一头野兽困在胸中一般。
张赢川猛然一声断喝:“杀了!”
张政社闻言身子一抖,像是刚清醒过来一般,手中加力。张奉孝只听咔的一声,黑猫颈骨折断,身子垂了下来。张政社冷冷哼了一声,扬手把猫尸抛出了门外。
这前后石火电光,张奉孝看得目瞪口呆。二哥的功夫他素来是知道的,比自己只强不弱,但万万没想到拳脚生风,一击不成,再击奏功,接着手断猫颈,脱手甩出,这速度和反应,自己是万万办不到的。
张奉孝刚想恭维二哥几句,就见他转过身来,脸色青白,豆大的汗珠不停滚下,眼球突起,几乎要破眶而出,神态甚是吓人。紧接着眼前一暗,张赢川突然拦在两个弟弟中间,一矮身,一个扫膛腿把张政社踢翻在地。
张政社趴在地上,身体强烈抽动,双手死抠着地面,嘴角白涎直流。张奉孝知道二哥的怪病又发作了,赶忙跪在地上,双手死死抱住他的脑袋,以防他神智不清,磕伤了脑袋。
整整过了一袋烟功夫,张政社才慢慢平静下来,身子不再抽动,眼神也逐渐正常。张奉孝自从进门,一系列怪事接连发生,连张口询问的机会都没有,早装了一肚子问号。这时抬起头来,向张赢川投去询问的目光。
张赢川脸色铁青,并不理会,把张政社扶了起来,转身回到椅子上,想了半天,才轻轻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两个弟弟:“这病发作越来越频繁,再这么下去,就怕破咒无望啊……”
张奉孝再也忍不住了,见二哥已恢复平静,便半拖半拽地扶他到椅子上坐下,然后一字一顿地沉声发问:“大哥,我好歹也算是张家的子孙,如今也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别再瞒我了,有什么事,说出来,咱们三兄弟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张政社佝偻着身子,略微扬了扬手,语气疲惫:“大哥,告诉老三吧。大嫂走了,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你既然写信叫他回来,宜早不宜迟,明天去给嫂子烧刀纸,也该动手了。”
张赢川点点头,将先前放在八仙桌上的包袱解开,露出里面的物事,沉声道:“这次去北京白云山,就是为了取回这几件东西。**的时候,到处破四旧,咱爹怕祖上传下来的这些东西毁在手里,幸亏当年一个同行帮忙,给收了几年。如今老三也大了,张家子孙谁也脱不掉,有些事你该知道了。”
看来秦琪儿猜得果然不错,大哥有事儿瞒着自己。张奉孝点点头,从裤兜里掏出大哥写的那封信,放到了桌子上:“我也有一堆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大哥,有什么难处说出来,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张赢川苦笑了一下,想了想才道:“老三,你也知道,咱爹是一脉单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了三兄弟。你二哥不用说了,这病情打小你就见过。我左腿腿骨天生扭曲,右肋下一个大洞,能活到现在也是不易。只有老三你,除了尾巴骨有点问题,基本算是个正常人……”
一听“正常人”三个字,张奉孝脸色一白:“原来大哥小时候逼我喝酒,就是因为尾椎骨有毛病。可是大哥,这究竟是什么病,怎么喝酒就能压制住?”
张赢川摇了摇头,叹口气:“酒能缓解疼痛,这只是其一,还有另外的原因,慢慢我会告诉你的。还有我那两个孩子,老三,你也知道,一个天聋一个地哑。咱张家门里,其实不止咱们三兄弟和两个孩子,就是咱爹和咱爷爷,也都天生残疾。既然生为张家子孙,就免不了了。”
张奉孝心里格登一下:“这是为什么?就算是家族遗传病,也该是同样的症状啊。对了,玉山和稷玺呢?打回来我就没看到。”
张政社伸手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接过话头:“大嫂过世没几天,大哥要去白云山,我又时不时犯病,两个孩子就送到姥爷那边去了。明天,老三你去接回来见个面,万一以后见不到了,总是件憾事。”
以后可能见不到了?这句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样。张奉孝一激灵,顿时想了起来,回家前带秦琪儿去黑屋子,蔡叔好像隐约说过同样的话。难道蔡叔以前跟自己家里真有什么瓜葛?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张赢川点点头,盯着张奉孝:“老三,你可知道咱爹为什么给你取这么个名字?”
名字?张奉孝?这个名字怎么了?张奉孝头皮一阵阵发麻,看来真让秦琪儿说着了,名字绝不是个符号,真有可能暗藏玄机。
张赢川自顾自地说了下去:“爹熟读三国,最佩服的人就是曹操的一个谋士,郭嘉郭奉孝。老三,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存了希望你料敌先机,克敌制胜之意。”话未说完,见张奉孝神色有异,便停住不再往下说,“老三,怎么了?”
张奉孝深吸了一口气:“回家之前,有一个女同学,也跟我说过跟大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她说一个人的名字不仅仅是个记号,我的名字,必定是跟郭奉孝有关,现在看来,没说错。”
张赢川跟张政社对望了一眼,大为惊异,朝张奉孝一挥手:“老三,你这同学叫什么名字?怎么会无缘无故跟你说起这些?”
张奉孝知道其中关系重大,便将与秦琪儿进黑屋子探访蔡叔,坐论玄机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二哥倒没怎么样,张赢川听了,却是大为感兴趣,低头想了好一段时间,才缓缓说道:“若说是巧合,也未免太巧了。据我看,这蔡叔当年应该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至于那个女娃子,虽猜不透底细,也大有问题。老三,你刚才说她是哪里人?”
张奉孝回忆了一下,把秦琪儿所说的祖上原是北方人,后来兵败退到海南等事说了。张赢川听完,扭头问张政社:“老二,这几天那些笔记你也该看完了,可记得有这么个人吗?”
张政社昂起头,瞅着顶梁认真想了想,一挥手:“没有。本来记录的东西就不多,就算当年有这么一号人物,也未必会提到。大哥,听老三说来,姓蔡的好像懂一些奇门遁甲之术,会不会是当年崔猴子那边儿的人?”
张赢川思忖了半晌,才皱着眉头道:“未必,奇门遁甲也不是只有崔猴子一派才懂,终归脱不了易理神数,有不少干单帮的也熟知一二。奇怪的是姓秦的这个女娃子,还有她父亲大金牙,很不简单。要说起北京,我这次回来的路上,在白云山碰到了一个北京人,姓胡名八一,也是个同行,说起来跟咱上一辈好像有不浅的渊源……”
张奉孝听两位兄长云遮雾罩说了一堆,自己一句也听不懂,忍不住抬手打断了张赢川的话:“大哥二哥,话说得明白一些,难道真让她说着了,咱张家祖上真是倒斗的手艺人?”
“除了倒斗,还能是什么?”张政社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要不是当年张三爷触犯阴灵,张家门里也不至于有如此大祸。你看看大哥的两个孩子,天聋地哑,要不是这样,大嫂能愁出病来?”
张奉孝心头一暗,话说到现在,真是无一件不在秦琪儿意料之中。蔡叔是盗墓的,自己祖上也干过这号营生。都说人鬼殊途,倒斗人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去刨坟,晚上黑灯瞎火地打通墓道,连拱带爬地进古墓转悠,遇到点麻烦事儿不稀奇。搞不好自己祖上那什么张三爷招了什么脏东西回来,所以张家后代个个受累。
张赢川双眉紧锁,旋即舒展开来:“要说张三爷,也就是咱爷爷的爹,当年可是响当当的摸金校尉,也就是倒斗人。老三,当初我硬逼你报考历史系,也是有原因的,你可知道摸金校尉是什么意思?”
这个张奉孝自然知道。汉末黄巾军起兵造反,曹操率兵征讨,军饷吃紧,便在军中设立了两个官职,一是摸金校尉,一是发丘中郎将。这两派人马堂而皇之的盗墓,把墓中得来的金银珠宝都充作了军饷。后世很多盗墓贼借其虚名,自称摸金校尉,干的自然也是倒斗的勾当。
张赢川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很是欣慰:“看来老三书没白读。张三爷,原来叫张三链子,因为身手不凡盗过几个同行不敢进的大墓,人人都尊称他张三爷。张三爷后来金盆洗手,行内人都以为他是钱捞够了厌烦了盗墓的营生。其实,个中原因,除了我们张家子孙,外人又哪里知道?”
张奉孝点点头,知道大哥就要说到关键所在了,催促道:“那么,张三爷金盆洗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与张家后代受累这事儿,有莫大的关系?”
张赢川眼中泪光闪动,显然是又想到了几代人所受的无名苦楚。张政社已完全恢复,叹口气,伸手抹了把脸,替大哥说了下去:“当年张三爷何等了得,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事,他怎么会正当壮年就金盆洗手?这两天大哥去了白云山,我翻了翻爹留下来的笔记,上面有记载。当年张三爷摸进了一座古墓,中了邪,所以金盆洗了手。”
张赢川回过神来,叹了口气道:“不是中邪,是中了血咒。”当下原原本本把张三爷当年发生过的一些事告诉了两个兄弟。
原来当年摸金校尉张三链子,因一身倒斗的好本事,行内人不直呼其名,皆以张三爷代称。张三爷精研易术,有神鬼莫测之机。古墓地宫,不论是隐埋高山大岭,还是潜藏水中地下,只要张三爷出马,紫金罗盘一到,上观天象三垣,下踩地理七星,剑指到处,便是坟冢所在,毫厘不爽。
世人都说,张三爷倒斗倒出了名堂,家财巨万,因而金盆洗手,成就了倒斗行内的一段佳话。不过这可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世上可没有嫌钱多的,张三爷进出古墓无数,深知地宫中珍宝无数,又正当壮年,怎么会舍得就此罢手?
张三爷金盆洗手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张家门里不可对人言的秘密了。按张奉孝的话说,这与张家子孙所背负的血咒,有莫大的关连。话说张三爷某日挖进一座金国古冢,无意中得到了一幅十六字天象全卦。正所谓乐极生悲,这古冢大有门道,张三爷纵有惊天神通,终于还是中了血咒,张家子孙世世代代皆受其累。
张赢川把话说完,长出了一口气,又道:“要破除张家所受的血咒,不那么容易。张三爷过世的时候,曾留下话来,要张家子弟找到破咒之物。从爷爷那辈儿起,加上爹,还有我,不知翻过了多少古墓,也未曾找到什么线索。”
张奉孝吓了一跳:“怎么,大哥,你也进过古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