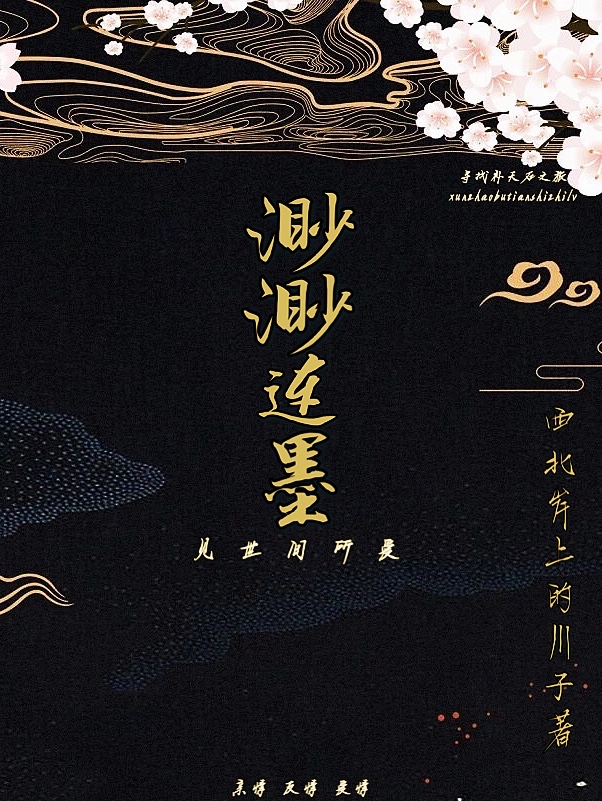我和王路是三年同学,却在数年后以网络朋友的方式重新认识了。之后的时间里,我们通过网聊基本知道了彼此想要知道的对方的大部分信息。聊天的句子随着聊天次数的增加简直就是在谈情说爱了。大概十多天之后我们互留了电话。
互留电话的第二天早晨,上完课后,我和舍友从教学区回至生活区,生活区的院子里,有好几棵年近百岁的大柳树,柳树旁是水库,水库的三面墙体上都接有水龙头,供住宿教师生活用水。我一手提着塑料水桶,一手端着菜盆朝着水龙头的方向走去。天空蓝的耀眼,阳光温热的 洒下来,柳树上,鸟儿们“啾啾啾”的雀跃鸣叫。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花飞溅着碧绿的油菜,软和的风缓缓的吹过来,我想唱歌,于是我轻轻的哼起歌,”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里,在不知不觉得一瞬间又想起你......"
站在水花四溅的洗菜盆儿旁,我想王路会不会在今天给我打电话,他何时给我发讯息。照片中自信飞扬的那张脸庞又浮现眼前。于是我继续哼着歌,开始往塑料水桶里接水,水未满,我的电话铃声响了,我急忙拿出电话,陌生电话,但我已知是谁,立马,我的心跳似乎就在嗓子眼儿上,我镇定一下接通电话说“哈喽”,与此同时,那边说“你在干啥呢?”我说我在水龙头边上洗菜呢你干啥呢?“一个同事搬家,我早晨去帮忙了现在刚回来”声音有些沙沙的烟嗓。我们聊得时间并不长,他说他要去单位出工了,他很期待和我见面,如果单位没有临时工作安排的话,两周后的周五他就回来和我见面。临挂电话时他又说一句:”想想你一个女孩子还要提水,我其实挺心疼的,以后这些活儿就交给我吧“。我的心内充满了甜蜜,但同时,也不安着,两个熟悉的陌生人,在网络世界里浓情蜜意,虽美好,但虚幻而令人不踏实。
无数次,我看着立镜中的自己,身材矮小,皮肤粗糙,就女生而言,大部分人从外貌来说随着年岁的增加而蜕变的越好看,而我属于反其道而行之的极少类。社会更好更开阔了,更多的女孩子借以读大学的机会从农村进入各个城市,在环境的影响中逐渐习得衣着得体、妆容精致的本领,大学毕业后衣锦还乡精神抖擞的走上各个工作岗位,一个更比一个俏丽,一个更比一个有韵味。而我,用我妈的话说,压根儿不会打扮,邋里邋遢。我妈劝我不要老是穿运动鞋,女孩子要买高跟鞋的,你看邻居家虹,她工作不及你好工资不及你高,但人家穿的干散的呀,一天一套衣服的换。在我周围众多女人的忠言逆耳下,我买了一身很女人的行头,从七厘米的高跟鞋开始,那时流行小脚紧身裤和风衣,我一一购进,另有各类军师参考建议的上衣下裤,总之,一段时间下来,各类衣物能够保障较为丰富的搭配,但坚持不到三个月,我就累了,我只想做自己,只想穿着运动鞋健步如飞,针织衫和休闲服才是我的最爱。一个既然已经成型的人,服饰的装饰作用其实很有限,装饰也是基于天赋的,如果身材五短,皮肤粗糙,过多的装饰非但适得其反,而且徒增疲惫。
所以我想让自己简约舒适。做自己,不太好看也没有关系。
但随着和王路熟识程度的与日俱增,我开始有了外貌焦虑,我从衣柜里拿出我所有的衣服乱搭着试图找寻出最适合的搭配,也想要和闺蜜在周六周末的时候逛逛服装店更新一下自己,但同时我觉得自己太过重视第一次见面了,心说既然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何必造作,就这样干净简单的见面好了,是怎样就怎样,顺其自然,但同时心有戚戚,略微的担忧着。
两周后的周四的晚上,王路打电话说他明天会如约回来。我们约好在县城见面,约好去一家我常吃的火锅店吃火锅,还约好一起去爬山。他也会顺便回家看看他的妈妈。
王路的家就在我上班学校的河对岸的村庄里,与学校所在的镇隔河相望,有水泥桥相通,离我很近,我想,我有可能和他的妈妈擦肩而过吧。
周五放学之后,我坐车回县城,我先回了趟家,交代妈妈今晚同学聚会我可能来的晚一点。我家原本在离王路家大概20分钟车程的一个村子里,几年前爸爸在县城买了院子盖了房屋,就搬至县城居住,原来村子里的老房子还在,但也只是在逢节过令时回去一下。我换了一身衣服,红色的卫衣、蓝色的牛仔裤、藏青色运动鞋,衣物普通,但我觉得挺好的。出门前我洗了把脸,薄薄的涂了一层bb霜,这样气色看起来稍好一些。提一只白色条纹帆布包,我出门了,傍晚时分风有些紧,稍冷,看了看表,差不多应该到了,我没有打车,我家离车站不远,我想走过去,这时电话响了,接通电话他说路上有些堵车,可能会晚个一小时左右,也说不定,看堵车时间长不长了。我说没关系,不用着急,反正明天周六,大不了周六见喽。他笑着说没那么夸张并问我有没有离开家,没有的话就迟出来一会儿,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我想先回家,但想着回家也呆不了多长时间还得出来,算了,索性去车站等着吧,我着意慢悠悠的走着,想象着等会儿见面的情况,我告诉自己要大方得体。
由于是傍晚,车站人已稀少,我进入站内后院,大巴车到达之后会停在后院,后院在河道旁边,风呼啸而来,很是冷冽。我缩着身子侧风而站,有点后悔刚才没有回家等稍后再出来,我将包放在地上,空手跳绳试图通过运动让自己暖和一点,但风太大了。候车厅因下班而关门了,我无处可躲,我希望他能够快点到达,好让我结束这寒冷空气里的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的走过,我冷的直打颤,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还需20分钟左右就可到达,我又在冰凉的空气里跳动起来。
不及20分钟,他打电话说你从后院出来沿着马路往前走,师傅说大巴车不进车站了要停在桥的这一边,我们都向前走就会碰面的。挂了电话,我提起包出了后院沿着车站前的公路往前走,走了几分钟后,我看见对面的远处走来一个人,我想应该是他吧,逐渐的,我看见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果然挺高的,皮肤白皙,相貌英俊,但两只胳膊随着走路的节奏夸张的甩动着,走姿甚是难看。我的脸开始从皮肤深处燃烧,眼睛不知道该不该看他,所以我边走边东张西望。当我们从两个方向走到一起站住时,他笑着对我说,好久不见啊,你还和以前一样。我有些难为情,呵呵呵的笑了几声,随之我说,你长的挺高,变化挺大。他说没有吧。之后我们朝着他走来的方向走去吃饭,我们说话前行,走着走着,他的左手拉住了我的右手,我心跳的厉害,同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他神态自若,谈笑风生。他的手很暖和。
火锅店所有的位置都满了,由于不确定他几点到达所以我们没有事先预定位置,排了号之后,我们站在店门口的灯光里等待叫号,他掏出烟抽了起来,我们仍然说着话,但某个时刻也觉得无话可说,空气略有尴尬,我不看他看周围时觉得他在暗暗的从上到下打量我,但或许是错觉。终于叫到我们了,我点了菜,他点了一份儿面筋,他说吃火锅他除了面筋其他菜品都无所谓,餐桌上,我们更多地聊了各自的工作。开始时他象征性的给我夹菜,我有些不习惯,我说我们各自吃吧不用彼此夹菜,他好像也很认同,埋头就吃他的了,中间他频繁而熟练的抽烟,夹着烟的手指骨节分明、葱白干净,非常好看。
饭前我便想由我结账,毕竟他远道而来,但他抢先一步,我说AA吧,他哈哈大笑着说哪能那样。走出火锅店他问我们再去哪儿,我说再过一会儿我要回家了,他说那我们逛逛夜市吧,我说那好吧,他拉着我的手我们在夜市上漫无目的的乱逛着,琳琅满目的小物件面前是年轻的男男女女,他问我有没有想要的东西,我说没有,他便不再说什么了。在街道走着,我觉得时间渐晚,我说我要回家了,他说那我送你吧,我说好啊,我们开始朝着我家的方向走,一会儿他说要不你先陪我去定一间酒店不然时间太晚怕满客了,我说那好吧,于是我们朝原来方向的左边的道路上走,前面有一家酒店,我们进去定了一间房,拿到房卡之后,我说你上去放随身物品吧我在下面等着,王路说我俩一块上去吧放完东西很快就下来,我说我就不上去了要不我自己回家吧,他看着我说你陪我上去放完东西我送你回家呀。我看着地面沉默了一会儿,任他拉着我的手进了电梯。那一晚,我没有回家。
整个晚上我一眼儿没扎,失眠让我头昏脑涨,王路在我旁边鼾声此起彼伏,我心犹如蚂蚁咬噬,又如被塑料袋包裹,疼痛而窒息。网聊时罩着我的幸福和安全被撕破,我重新置于黑暗中荒无人烟的原野,想大声喊却发不出声,只有嗓子眼儿在干涸中蠢蠢欲动着。我觉得自己愚蠢、混乱,我胡思乱直到天亮,彻夜未眠。王路醒来点了一根烟,他微笑着看着我,一会儿他说“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我看着他的眼睛问“你觉得我们合适吧?”他说那谁知道呢毕竟好多年没见了,抽一口烟继续说,工作也不再一块儿也没有办法相互了解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看了看窗外。过了一会儿,他抽一口烟又说,即便我俩合适,两地分居怎么解决,结婚之后你我都会很辛苦。我没有说话,我坐在窗户旁的沙发上沉默很久,之后我说,我们各自回家吧,如果你没有看上我请不必抱歉,请不要再联系我,打电话或者信息都不要。王路笑着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走过来轻轻拥抱了我。
中午我们一块儿吃了饭,我们沿着河坝的那条路走着,他尽力的讲着笑话,我心内觉得挺可笑,是我们可笑,河水哗哗的流淌着在太阳下泛起亮光,邻居家的几个小孩子在河道旁放风筝,但由于风小怎么也飞不起来,我心想千万不要遇见熟悉的大人,我说我家到了再见吧,他说那你回吧我也要坐车回家了。我从河坝下来转进我家的深巷子,他在后面喊“打电话噢”。
回家之后心乱如麻,两岁多的侄女缠着我要我陪她玩,和侄女摆弄着她的玩具,小孩咿咿呀呀的把摆好的玩具搬来搬去,我手里拿一只玩具呆若木鸡,她过来拉着我的大拇指比划着,看着她,我眼圈儿里打转的眼泪忽然决堤奔涌而下,我大声哭了起来,侄女惊了一秒,也嚎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