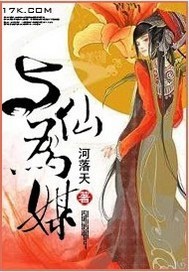山洞里更是温暖如春,初进去是一条仅可容纳两人并肩的狭长通道,石壁似乎是经过了人工的打磨,异常光滑,即使碰到了也绝不会擦伤。大约走了五十米,洞内便豁然开朗。
见到眼前的景象秋木白和梅素心惊讶极了,这个大概仅有两间房大小的山洞,竟是把一个小江南搬了进来。山洞正中是一架拔步床,高大轩昂,床身雕了九十九只羊,或憨萌或悍勇,或柔美或朗健,形态各异,意趣盎然。如此看来,雪大娘应该是属羊的,秋木白心中默算了一下,以雪大娘的样貌推断,她应该是康熙三十年生人。拔步床挂着的茜纱帐,既柔且垂,似静似动,一看就是出自江南织造最好的工匠之手。床内廊中所陈设的几案圆凳,博古小架,陈设着雅致的器皿,晶莹剔透的青白瓷器、雕工繁复的金银碗盏、造型独特的各式木器,东西虽不多却应有尽有;再恰到好处地点缀着精美的苏绣屏风,古拙的玉质折扇,跃然的紫砂羊雕,让人完全忘记了这是置身在长白山绝处的山洞里。
梅素心看了良久方感叹一句:“雪大娘真的好喜欢羊啊。”
雪姑笑道:“我师父属羊的。”
梅素心恍然:“我应该早想到的。”
雪姑扶着雪大娘进了拔步床,在床上躺下,从被子里抽出的靠枕竟然是金陵绝技之一的云锦,这是宫里御用之物,平常人根本连接触的机会都没有,织就一匹就要十年八载的时间,就算再有钱也买不到。那靠枕的图样竟然还是一只玫粉色的凤凰,周围配以蓝色卷云,这是只有后宫的妃嫔才可以使用的图案,连公主格格们都没有资格,这就更加不寻常了。
秋梅二人对雪大娘的身份满心好奇,但并没有出言相问。
只见雪姑从床下取出一个两尺见方的玉箱子,里面装满了晶莹剔透的白色药丸,雪姑取出一丸,又从架上取下一套玉壶玉杯,玉壶中有水,倒进杯里,把药丸花开,再送给雪大娘服用。
雪大娘用药之后缓了一会儿,表情也舒适起来,她看了一眼拔步床廊外站着的秋梅二人。
雪大娘:“你们进来坐吧。”
秋木白这才扶着梅素心进到拔步床里面,在圆凳上坐下。
雪大娘:“这位姑娘和我的病症一样,给姑娘也服一丸。”
雪姑说道:“可是玉杯只有一个,用别的杯子会影响药力的。”
雪大娘看了看秋木白,狡黠一笑:“他可以用我的玉杯,你可以让他先饮到嘴里,再送至姑娘口中。”
秋木白和梅素心大囧,雪姑也一脸茫然地看着师父。
雪大娘无视他们,慢悠悠说道:“此药名为冷香丸,是用长白山的千年人参炼制而成。把冷香丸存放于玉匣之中,需要时以玉壶玉杯服用,是因为我和这位姑娘一样,都是五脏受了不可逆的重伤,既需要千年人参来续命,又不堪承受千年人参强大的药性,经过玉器的长久滋润,冷香丸的药性被封住,变得温和内敛,入体后能够慢慢流入五脏,服用的时候再配以长白山三分热泉水七分冷雪水,如此冷香丸形成的药力刚好能够为我所用,不能有一丝差错,否则都会致命。所以这姑娘想要服用冷香丸不能用其他材质的杯子。”
秋木白不解地看着雪大娘:“可我是男人,浊气冲天,你如何许我用你的杯子,却不许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使用?”
雪大娘斜倚着床榻,盯着秋木白看了片刻:“你应该是叫秋木白吧?你父亲是秋远山。”
秋木白:“秋远山正是家父。”
雪大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自小与你父亲同寝一榻,同食一碗,同饮一杯,你既然是他的儿子,自然可以用我的杯子。”
秋木白浑身一震:“敢问前辈可是我三师叔周紫菱?”
雪大娘:“周紫菱早已经死了,现在只有雪大娘。不过你爹走的时候你应该还不到两岁,我被逐出师门,师父他老人家不准门内人再说我的名字,我又在长白山隐居也有十五年了,世人都以为我死了,你怎么会知道我?”
秋木白忙跪到在雪大娘面前,拜了三拜,然后从贴身的衣襟里取出一张羊皮卷,恭恭敬敬递给雪大娘:“这是家父留给我的。家母临终前再三嘱托于我,整个江南武林只有三师叔可以相信,只有三师叔可以看此卷。”
雪大娘难免有些诧异:“你母亲知道我还活着?”
秋木白:“家母说三师叔最喜欢的东西都不见了,肯定还活着,把平时的心爱之物都带走了。”
雪大娘打量着她那些陈设,都是她少年时代各处搜罗来的宝贝,不禁哑然失笑:“你母亲真是个玲珑剔透的人。”
秋木白把羊皮卷交给雪大娘,他们谈话的时候,雪姑已经把冷香丸化开,只是有些不知该交给谁。
雪大娘表情冷漠地看了她一眼:“给你秋师兄,让他给自己的女人喂药。”
雪姑便顺从地把玉杯递给了秋木白。
秋木白接过杯子,看了梅素心一眼,也不多说,站起身来走到梅素心身边,慢慢含了一口。
雪大娘看着羊皮卷,眼睛也不抬,似乎漫不经心说了一句:“用你一分的功力炼化一下。”
秋木白依言运气,用一分功力把冷香丸炼化,口中的药性果然变得更为温润,他明白了三师叔的真正用意,梅素心的伤是新伤,身体承受能力更差,所以需要他助一臂之力。
秋木白把炼好的药送入梅素心口中,两人双唇微碰,宛若多年相濡以沫的夫妻,没有一丝忸怩和兴奋。
在一旁一直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的雪姑,忽然意识到这是男女的肌肤相亲,连忙转头避开。
雪大娘却展开羊皮卷细细看来,只见上面是一幅江南反清复明联盟的组织架构图,上面详细标明了各大门派的掌门以及主要人物。秋木白给梅素心喂好了药,她也适时地抬起了头。
雪大娘:“二师兄竟然留下这种东西,要是落到朝廷手中,江南各大门派肯定会被连根拔起。二师兄这是把整个江南武林都恨上了吗?”
秋木白:“三师叔误会了,我爹只是想从这些人物关系中找到真正的奸细。”
雪大娘把羊皮卷还给秋木白:“我也不相信是二师兄做的。这个你收好,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份名单。”雪大娘深深地叹了口气,“它早晚会害了你,不光是朝廷,就连江南各大门派只要得到一点儿讯息,都不会放过你。你真的是你爹亲生的吗?”
秋木白深深看着这份名单,好像要把这张羊皮卷看破一样:“就是因为我是我爹的亲儿子,才有责任替我爹洗清冤屈,那个人就在这份名单里,不管他藏得多深,我都要把他挖出来。”
雪大娘:“难道你要一个一个地去查吗?”
秋木白:“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雪大娘:“自从师父他老人家过世以后,江南反清复明联盟几乎成了一盘散沙,快二十年了,很多门派都归顺了朝廷,但日子也都不好过,究竟是谁得了真正的好处呢?”
雪大娘把思绪拉回到了十八年前。
自古以来,中原地区是武林门派兴盛之地,可满清入关,曾在江南大肆屠杀汉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人民血海深仇不能忘,抗清义军纷纷崛起,不到二十年间就形成了九大门派,数十个小门派,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誓把满清鞑子驱逐出中原。为了壮大力量,以九大门派为首建立了江南反清复明联盟,并共同推举德高望重、武艺超群的秋叶山庄庄主秋连峰为盟主,就是秋远山的父亲,秋木白的祖父。
听到这里梅素心和雪姑都很惊讶。
“我竟然不知道师祖就是二师叔的父亲。那么大家对他的指控不仅仅是杀害师父背叛师门,还有弑父的罪名?”吃了冷香丸的梅素心明显精气神好了很多,忍不住问道。
从他们进了山洞,雪大娘一直盯着秋木白看,完全没把梅素心放在眼里,这时候才问:“怎么,你也是师门中人吗?”
梅素心:“梅红蕊正是家父。”
雪大娘有些意外:“哦?你是大师兄的女儿?”
梅素心欠身行礼:“见过三师叔。”
雪大娘:“不必多礼。我记得你小时候一直跟你娘住在乡下,你们什么时候回到秋叶山庄的?”
梅素心:“我六岁时母亲病逝,父亲把我接到了秋叶山庄。”
雪大娘:“你母亲也亡故了?”
梅素心有些悲戚:“已经十二年了。”
雪大娘:“没想到身子比我硬朗的人,竟都已经不在了。我这身残躯,活着也是靠一口气。”
雪姑从未听师父提起过师门之事,不禁好奇,眼巴巴看着师父,希望她能多讲一些。
雪大娘:“其实当年师父遇害的前因后果我并不知道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也如她一般的年纪,被一个男人迷住了,整天往外跑,几乎不在山庄里。”
雪大娘深望着梅素心,她是第一次认真地看着眼前这位姑娘,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她收回眼神,低头流露出难当的愧疚,这是秋木白见到三师叔这半天来第一次见她情绪如此波动:“到今天我还觉得愧对师父。”伴随着这句难以出口的话,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雪姑忙替师父顺气按穴:“师父不要难过,您的身子不能太激动,刚刚用了药,您还是歇息吧,明天再聊。”
雪大娘摆摆手:“无妨。我这把身子也快到头了,临死前能有人说说当年的旧事也好。”
秋木白心中道可明兄说的一点都不错,内腑受伤果然不能有情志的波动,他担忧地看了一眼梅素心,只见梅素心神态淡然。
雪大娘恢复了平静:“那天师父正好五十岁的寿辰,那个让我着迷的男人……”雪大娘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决定把真相告诉后辈,“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现今在位的狗皇帝。师父要是活着,见到我爱上了满清的四皇子,就不可能是逐出师门这么简单了,他老人家一定会废了我的武功。大师兄接任庄主后见管不住我,只能去查那个人的底细,我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满人相恋是咱们师门第一等大罪,甚至比灭师弑父还严重,只是把我逐出师门,大师兄对我还是仁慈的。”
这一席话惊呆了三个晚辈,他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半晌没人搭话,雪大娘也暂停讲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
梅素心终于忍不住说道:“可是三师叔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是被骗的,俗话说不知者无罪,父亲这样做也说不通。”
雪大娘叹了口气:“我罪不可恕之处就在于知道了他的身份,我还执迷不悟,一心跟他走,甚至帮他做一些对付政敌的龌龊事。那时候我太年轻,只知道我从未见过如此风度翩翩、文才武功都一等一的贵公子,只要能跟他在一起,什么背叛师门、反清复明都抛在了我的脑后,他是我的一切,只要他一句话,我什么都肯为他做。”
对,那时候她还不是雪大娘,她是周紫菱,是那个江南最大门派秋叶山庄唯一的女弟子,是江南武林之首、不轻易收徒的秋连峰的关门弟子,是江湖赫赫有名的紫剑女侠周紫菱。她年轻气盛,风华正茂,一心完成反清复明的伟大梦想,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抵过那个男人忽然回头对她的一眼深眸。
雪大娘忽然想起来:“木白,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
秋木白愣住:“哪句话?”
雪大娘:“就是什么男人浊气冲天、女人冰清玉洁的那句。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听说过这种言论。”
秋木白:“这也不是我说的话,是我一个朋友说的。他经常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他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周紫菱叹道:“这世上还有男子这般看待女子,我真想见见你这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