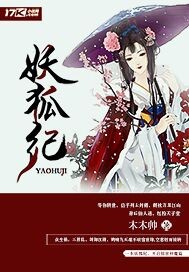出门沿回廊走不远我便不敢再往前走,四下看了看,确定无人后才放心启用手链招来几只小飞鸟。
“听着,帮我找宝宝来这儿,要快!对了,让它小心被人发现了。”遣走那几只飞鸟,又对留下的那只叽叽喳喳的鸟儿说道:“你先去盯着他,随时回来报告我,知道吗?”
回到穆苏的住处时,祁昰还在他房里,两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声音都压得极低。宿寒守在外面,我刚走近了两步便听他出声阻止。
“雪婴姑娘请留步。”
“他们还在说么?这么久了,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我疑惑不解,既然不能让旁人听了,我也只好等在外面。隐隐的听着祁昰好像在里面在说什么,在回宋国的途中便收到讯息,于是匆匆赶了回来,又说什么不便插手的,总之后来的我也听不清。
又过了一阵子,房内传出祁昰爽朗的笑声。
“这件事,我还未跟祖母提及,祖母只听说府上来了位我的客人,还不知是谁呢。等过些日子,你的伤好了些,我再作安排让你跟祖母见面,如何?”
穆苏谦逊有礼回道:“无妨,我的伤并无大碍,原是应该我去拜见尊祖母的,怎好让尊祖母此番久等。不如就安排明日吧,明日我亲自去向尊祖母赔罪。”
我心间疑惑更深,以前跟穆苏在一起的时候,虽总共听他所说的话并不多,可这样的语气跟声音,却实在跟我以前听到的有些不同,可到底不同在哪里,我一时想不清。
便又听祁昰说道:“好,便依你所言。”紧接着不久便从房里出来了。
见门开,我便凑上前去。
祁昰见了我,朝我意味深长的笑了笑,看得我直冒鸡皮疙瘩。
我怪异的觑了他一眼,转身向房门走去。
“怎么,有了你穆苏哥哥,便忘了你大恩人啦?如此心急去看他,我又不会吃了他。”说罢又是一笑。
我瞬时红了脸。
“哪有,我担心穆苏哥哥伤势,所以才·······”
不等我把话说完,祁昰便顾自摇扇扬长而去。
及至屋内,烛火摇曳,烛光拖着衣衫单薄倚靠在床上的穆苏的影子投在桌前的绢画屏上,闪烁不定。画屏上高低重迭的山峦间,逶迤碧水流淌,行云流水的描着幅野水青山的山水图。穆苏青丝如瀑披肩,凹凸有致的五官有些许迷蒙的映在屏上,静静的就像隐在那山水间的仙人跳脱而出,放大在我眼前。
望着屏风上投映的影子,恍然幻梦,我竟有些痴了。但听他轻微咳嗽,说道:“怎么不进来?”
被一语惊醒,我这才如梦初醒应了他一声。走至桌前,见适才端给他的药汤尚未动分毫,里面的汤药都已经冷了,便捧着想拿去重新热热给他。
便听他道: “不用麻烦了,给我吧。”
“药凉了,我去给你热热。”
“无妨,拿来吧。”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应声端了进去。
及至床前,但见他手里拿着那块铁质的面具,静静的不动,似乎并不打算再戴上去。我抬头望他,见他白衣玉冠,肩头披了件白色的外衫,眉眼温润,清朗的眼带笑意。手里的药碗瞬间脱离了掌心,我怔然盯着眼前之人,迟疑道:“你······不是穆苏哥哥。”
他神色微怔,眉间隐见一缕清愁,又脩忽飘散不见。
“我原本也无意欺瞒你什么,我的确不是穆苏,雪婴。”他轻声说着,精神好似好了许多。
“那你是谁?你怎么会认识我的?”即便我告诉过他我的名字的,可为什么他看起来还知道我与穆苏的事。
“我叫乐凌轩,是穆苏的朋友,也是他告诉我关于你的事的。”
听他将穆苏在千日谷的事娓娓道来,又问起我穆苏的笛子,我心知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是穆苏的朋友。听说穆苏的伤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也便放心了。
药汤洒了一地,我弯腰拣地上的碎瓷片,却不小心被一片锋利的碎瓷割破了手,鲜血直流,连忙将手指送进嘴里吮吸。
“不小心割到手了么?”乐凌轩轻声问道。
我瞟了眼他,不再说话。
又听他道:“以后要小心不要弄伤自己,你的血很特别,你也很特别。”
我心下大惊,背脊生出一阵恶寒。心想难道是宿寒告诉他的?
“大哥哥,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我笑说道,埋着头小心翼翼的呼吸着,等着他的下文。
他也轻笑,突然又岔开话题说道:“这十几年来,你在千日谷里过得还好么,陆吾可有好好照顾你?”
我惊惶不定,他怎么知道阿翁的名字?骤然抽离手指,问道:“你怎么知道我阿翁?”
这个人竟然将我的秘密一语点破,以这样风轻云淡的方式,他究竟是何人,怎么第一次见我便知道我这么多事。这绝不可能是穆苏告诉他的,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些。
但见他眉目具笑,温润如玉。“你不要害怕,我只知道这些,是你刚刚睡着了梦呓时,我不小心听到的。”
随即又歉意的说着:“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闻此,我这才松了口气,原来我刚才又说梦话了,幸好他只听了这些。忙赧然笑道:“我大概是又胡说了吧,我小时候总是爱乱想些奇奇怪怪的事,其实我的血和别人都一样,所以阿翁以前总是骂我说胡话呢。我是不是很像个疯子一样?呵呵,你可别把我的话当真了呀。”
他目光温柔,就像阿翁以前那样温暖,却又有些不同,我猜不透。
他笑了笑。“好。”
乐凌轩原本便打算拜见祁家家主祁姬的,于是第二日在祁昰的安排下便同辛九一道去见了祁姬。
祁家现任家主祁姬,祁昰的祖母,原是燕国之女,后嫁入祁家为妇。祁姬一把年纪还坚持操持着祁家庞大的家业,打理整个家族内外事务,这并不是她有多么强势,而是别有他因。祁家世代铸剑为生,据说许多旷古奇剑大都出自这里,且不仅如此,祁家还做帝王家的生意,这便奠定了祁家在宋国数一数二的世族大家的地位。
祁姬膝下共两子,大儿子祁正也就是祁昰的父亲,原本是这一代的祁家家主,倒是年轻有为,可谁也没料到他会英年早逝,如今只留下了祁昰这一条唯一的血脉。也便是因此,祁姬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儿可谓是疼爱甚佳,初初念其尚小,加之其母早早背离,抚养之担便全落在她这个祖母的肩上。十几年来,本该坐享儿孙福的祁姬不得不与二儿子祁越一同扛起祁家庞大的家业,坚持打理家族事业,这便成了外人口中的女强人。
十年成一英雄,渐渐地,祁昰在祁姬的管教下长大成人了,眼看着该是她祁姬卸下担子的时侯,却不料这个宝贝孙子偏爱吟吟诗篇,描描山水人家,酿酿小酒的,对继承家业一事极为抵触。任凭祁姬软硬兼施,那祁昰就是想方设法的摆脱,可把祁姬急得头疼。于是就有人对祁姬说了,说祁昰该是年少心浮,他弱冠已过,也是该成亲的年纪了,应该给他定了亲事,安了家,人就该沉下来了。俗话说,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小家先成,方谈齐大家。祁姬思及这是个两全其美的事儿,便开始为祁昰四处张罗起婚事来,谁知祁昰不但没沉下来成个家,反倒更加猖狂了起来,动不动就以逃婚为前提溜出府去,前阵子更是一跑跑去了燕国。
祁昰在外面的那段日子倒也过得舒坦,而如今回到祁府,却如同那霜打了的茄子一般蔫了,躲躲藏藏的不愿与祁姬正面交锋。
如今祁姬要接见客人,祁昰自然也被叫了去。大厅里大家都客客气气的交谈着,也不知是谁,说着说着便将话题引到了祁昰身上,无非还是他的婚事问题。紧接着毫无悬念的,当着我们的面祁昰又被训诫了一番。
被训了的祁昰灰溜溜的摸了摸鼻子,却恭敬如命听着。
等到我们都告辞后,祁姬屏退了所有人,却独独将辛九留了下来。也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晚上遇见辛九时,他正在屋顶喝着闷酒。
夜风渐起,吹散了笼罩在月亮周围的云层,却不见那清辉减了半分清寒,寒透人心。高高的屋顶上,辛九斜靠在屋顶尖角上坐着,似乎在赏月,却抱了坛酒,时不时地灌上几口。只道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祁昰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呵,伯九可真是好雅兴,难道晚宴上还没喝够吗?躲到这儿来独自一人饮酒赏月作潇洒,很惬意嘛。”
“哪有祁少君好兴致,上来一起喝吧。”
祁昰一个飞身便轻松上了屋顶,找了处屋檐边坐了下来,接过辛九的酒痛快灌了几口,道:“这酒虽好,可不比我酿的共白首醇香,改明儿个我去取来,咱俩再喝一道如何?”
“共白首?好风雅的名字!不过,不知那是什么好酒,我倒愿意一尝。”辛九淡淡地说道。
“原是我自己酿的,可如今仅有两坛了,不过无妨,喝着痛快才最重要。”祁昰接过酒,又是闷头一口。
两人似乎都只是在找痛快,却不是在品酒了。
“既是你自己酿的,那大可再酿啊,何苦守着仅有的两坛舍不得起来。”
辛九说起话来毫不留情面。
祁昰摊了摊手,作出副无奈的样子。 “不会,祖母说是我酿的,可倒怪了,我竟不会再酿。”
“是吗?”辛九的语气中带着淡淡的忧伤,携着夜风消失在空旷的夜空。
辛九忽而枕臂躺下,却侧头默默看着祁昰,良久,直到祁昰感受到那炽热的目光转过头来,恰对上辛九淡淡忧伤的目光。
祁昰嗤笑一声。“伯九这是怎么了?为何如此看着昰,昰自知自己风度翩翩,仪表不凡,可魅力也不至于这么大吧……”
正说着,却见辛九起身慢慢挪向祁昰。一步,两步,直至贴到了祁昰跟前,辛九突然弯下腰,将脸一点点凑到祁昰面前,眼睛却直勾勾的盯着那被酒水润湿的薄唇。一点一点,彼此之间呼吸骤然停止了交换。
辛九冰凉的唇轻启,对着祁昰吐气道:“我喜欢你……”
祁昰闻此被惊的一跳,霎时犹如大白天撞见鬼了一般,手忙脚乱,一把将辛九推开,吓得脚下一软,便胡乱就地打了通滚,险些悠不住身子跌下房去,霎时踩落几片瓦石簌簌砸了下来。
辛九及时出手将祁昰拉住。刚稳住身子,祁昰像只青蛙一般立马弹跳开去,隔着辛九远远站定,犹如惊弓之鸟忌惮地望着悠悠哉起身的辛九。
心神未定的祁昰说起话来也结结巴巴。“你……你该不会是断……断袖吧?”
辛九楞了楞。
月光悄然流泻,映着两人的影子犹如刻画。
辛九忽而笑道:“我若点头,那么你可愿从了我?我会很好,很好地待你。”
说完脉脉含情地望了眼祁昰,直吓得祁昰脚跟儿再软,忙不迭滚下房去。
檐上辛九一人独立在月下,意犹未尽悻悻沉吟道:“我本有心随流水,奈何流水系秋风。”却闻头顶上方又是一阵吸气声,辛九才悠悠道:“放心吧,我没那嗜好,即便断也不会断与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