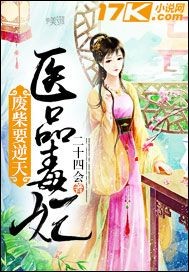苏家是漪水的大户人家,她还记得苏梓涵说她喜欢木兰,所以许多人附庸风雅,漪水到处可见木兰树。苏家庭院更甚,不过每棵木兰下还种着含笑花,只因为含笑喜阴,植株矮小一些,木兰可遮阳。而喜欢木兰的那个一直是云歌。
当年苏梓涵年少时,曾拉着云歌的手撒娇道:“云姐姐你喜欢木兰啊?那我让爹爹把院子里都种上木兰。”
果然,不仅苏家,整个漪水都爱上了种木兰。
她们,也曾情似姐妹过。可是事态发展,促使亲情中也会渐渐滋生出些别的东西来。
不久,木兰树下又开始多出了许多含笑。
说到底,云歌从未恨过苏梓涵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富足生活和父亲疼爱,因为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没有得到过的东西又遑论失去呢,所以也便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落感。可是她较于苏梓涵于父亲来说,始终还是梓涵更重要一些吧。她在这份缺失的情感上,看起来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这压抑了十几年的对生父的控诉,也渐渐变成了一种深不可测的执念。
王室大公子要迎娶苏梓涵,只因为苏梓涵不愿意,所以苏岳在即使知道云歌是自己女儿后,也还是毫不犹豫的将她给推出去挡箭,让她代替苏梓涵嫁入王室。这大概才是让云歌真正绝望的原因,那竟是她的亲身父亲的选择,若不是她出于私欲截下书信,也不知苏家竟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云歌行事冷静,她心里也清楚有些事注定如此,知道有些东西是她强求不来的。可她心里总归是怨怼的,她不禁恨她的父亲,因为他,在这世上唯一疼她的母亲才无药可治无路活命,也是他让她来到这世上却只能让她受苦,他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该尽的责任,也不配她云歌承认他。可是公子御夷不一样,即使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她,她却爱着他。他不属于任何人。他爱苏梓涵不愿违背誓言,可他至少也并未休了她,她想通过自己努力让他看到她,有朝一日他的心里自会有她的,哪怕只是一点点位置。
云歌倚在护栏上,手中拿着当年的那方素书,已然泛黄。当初不若是她一己私欲藏了这封信,为了求一个结果,或许现在她们三人也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她望着满树的木兰,若有所思。
“卑职无能,未能保护好殿下······”
她派出去寻找公子御夷下落的人回来了,带着他的噩耗。
云歌目光微闪,瞥向跪在地上的护卫。她派出去那么多人,终于有了他的消息,可等来的却是他最不想听到的结果。
“殿下,殿下身负重伤跌落水中,生死未卜!”
云歌怔然起身,身体因重心不稳,险些跌倒。她一手支栏,手无力的垂落下去,手中信纸飘落在地。
风吹过,带走一帘的雪白花瓣。
公子御夷在去会见楚国来客那次,为侍候污蔑勾结楚人谋反,宫内侍人芮与左师联合陷害,使得公子御夷谋反罪名坐实。云歌闻此猝不及防,受公子御夷之命前去请公子佐相助,无奈左师从中阻挠,不得。于是只得施一金蝉脱壳之计,将公子御夷暗中救出,再思策平反罪名。不料公子御夷性情秉直有过,委屈不能,中途折返,却于途中遇伏。
闻知公子御夷遇难,云歌便暗地里发了疯似的派人四处寻找。一面则立马进宫觐见君上,请罪自己私救世子出狱之事,申诉世子之案的冤情。一面,则又让公子御夷的贴身随侍假扮他,对外则宣称世子遇刺,闭门养伤不见外客,制造出御夷重伤命危的假象,诱敌入瓮。
不日后,果有一拨刺客潜入府邸欲再次行刺。而另一方面,云歌早已暗里找公子佐达成了协议。公子御夷不在了,那么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便是他。云歌请见公子佐陈明实情,请佐务必助她寻查真凶,还公子御夷一个交代。
她绝不会怜悯谁,即便是自己。所以她要做的便是以仇报仇,以怨抱怨。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她心尖尖上人的人,即便她在意的那个人一点也不在意她,甚至是恨她入骨,她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不利于他。她便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人,极端的又叫人心疼。
刀光剑影一刹那,不知是幻觉,还是公子御夷真的回来了,云歌竟突然扑向那侍者身前,拼死替他挡下了那致命一剑。
她明明晓得世上已经没有御夷了,或许他还活着,却不会再来见她。她大约是真累了,努力了两年,他却再不会看她一眼了,那样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与公子御夷争吵那日,她已着手请人相助。苏家这些年借势发展得顺风顺水,财力跻身整个宋国前列,渐渐不容小觑,如今突然栽了这么大个跟头,表面之下定不简单。可云歌万万没想到的是,此事还牵扯出了命案,她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明面出手挽救,更害怕因此拖累世子府,于是只能借助外力暗箱操作。然一方面苏岳的一无所有也让她私心渐升,这一刻她迟疑了,她想让他尝尝自己和母亲曾经是怎样的活着,苏家欠她母亲的,她永远不会忘。而正是这一刻的迟疑,促使整件事陷入了不可挽回的颓境之中。
没有什么武器比愧疚更能报复一个人,可是苏岳到底又会不会因此难过一点点呢?对于苏梓涵,她很清醒她只是在嫉妒,嫉妒苏梓涵那样容易就得到了公子御夷的爱,让他至今也放不下她。她这一注输了,输的还很彻底,亲情亦或是爱情终只有心凉,所以不需要再怨恨什么。她那些曾经的努力在他面前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她还是得不到他的心。既然公子御夷甘心为了苏梓涵放弃王位,那她为他挡下一剑又有何不可,如果那个人是他。或许她也该就此放手了,放过他,也放过她自己,可惜如今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云歌跌跌撞撞拖着步子来到那颗木兰树下,洁白如雪的花铺了满地。她颤巍巍靠在树上,被血染红的双手抚过树身,留下道道模糊血迹。她捂着不断涌流的伤口,凄苦无力笑道:“我这一生,为了生存算计,为了仇恨算计,却唯独想为你单纯一次,可是······我再守不住······”
仿佛又见细雨绵绵时节,木兰花开,他一身玄服蹁跹而至,嘴角轻扬,是在跟她说着“实在抱歉,惊扰到姑娘”。她躺在树下,衣裙上尽染鲜血,触目惊心。白色的木兰花瓣随风飘落,铺在她的身上,她眸光中深情又绝望,望着远方的眼终于轻轻合上。
不辞歌里断人肠,只怕有肠无处断。
府里本无木兰,什么时候开了这么好的一树,却原来是他移栽的。
可惜她再也等不到与他一同看木兰开满枝桠的那日。
三月,云歌不治而亡,以王室之礼厚葬。世子遇刺身亡消息公诸于世,谋反一案也沉冤昭雪,君上赐死了侍候,公子佐立为世子。不日后,公子御夷死里逃生回到国都,却逢世子夫人逝世,悲痛欲绝。
时值十月,天高云淡;及目之处,尽显萧索。偶尔的一阵风刮过,也带着一丝肃杀之气。王室的陵园里,一名身着灰衣的中年男子正手握扫帚动作悠缓的扫着地上的枯叶,身影单薄。金黄的银杏叶簌簌飘落,铺满一地又一地。
男子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望了望旁边的一棵木兰树,枝桠已是光秃秃。他轻叹了口气,似是自言自语,带着一丝饱经沧桑后的孤寂:“今年的木兰看来会晚些开了,你一定很想看吧······”说罢顾自轻笑了一声,唇角渐勾起一个浅浅的弧度。
身后传来枯叶被踏碎的声音,男子顿了顿,却未回头。
“卑职见过大公子。”沙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却仍铿锵。
男子未理,自顾自地继续说着:“我还记得,你曾说过,你喜欢木兰。”
一切仿佛又回到多年前。那个坚毅不露声色的女子,脸上带着明媚的忧伤,轻轻叹道:“我喜欢木兰,可却不是因为它洁白高雅,而是怜惜它······花颜易逝,命运堪折。”
男子自言自语道:“如果第一眼看见的不是她,我们会不会······呵,我还是没能让自己走进你的心里,是我。”他缓缓低头握起扫帚,一声不吭的向前走去,步履有些颠簸。
风吹过,金色的叶帘中,灰衣萧瑟。
云歌轻皱眉头,严肃说:“这是荨麻草,周身都是细刺,而且有毒,就算轻轻碰一下也不要。”
谁都知道,荨麻刺人,却并无毒,可谁人又知她心非木石。
她自比荨麻,将周身都长满细刺,不让别人靠近,同时也提醒着自己。她喜欢公子御夷,她用生命在爱着他,却从来不敢轻言所爱。他为她的身世悲怜,却又被她的坚强所震撼,他欣赏她的聪慧过人,却也忌于她的手段,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喜欢上了这女子。他们都是那样骄傲,又偏偏那样倔强,其实又何尝不是种怯懦呢。分明向往着对方却又止步于对方,最终被自己一遍遍欺骗了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