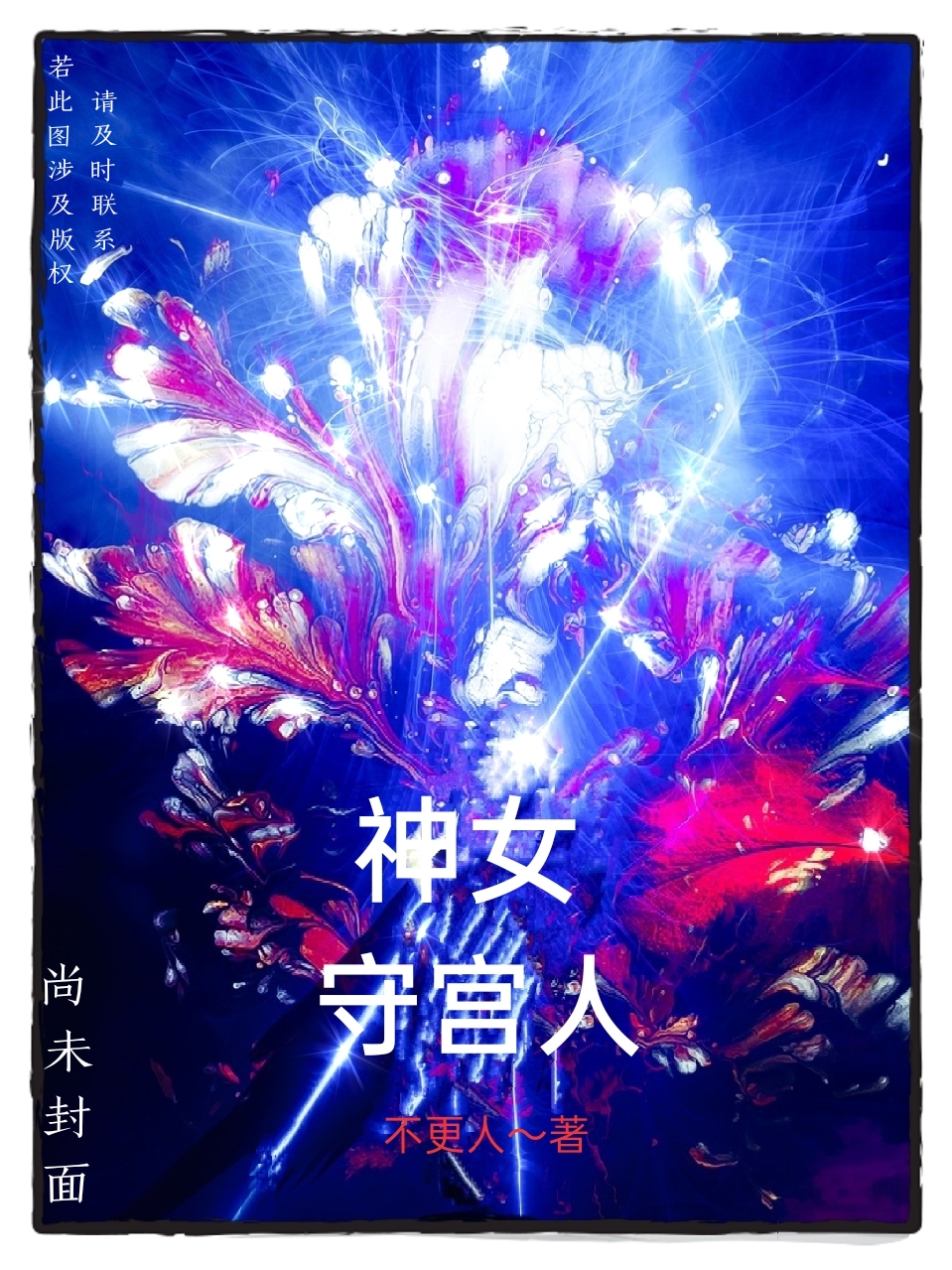沈然取来钥匙时,王毅也找到了自己的那串。
原来汽车小储藏柜上有条缝,装钥匙的小信封掉到金属线架里了。他弄出钥匙,开了门,让搬运工往房子里搬东西。
沈然把另一串钥匙也给了他。
王毅谢了沈然,漫不经心地把钥匙放进口袋里,看着搬运工搬运着那些箱子、梳妆台和衣柜等等他们结婚十年来积攒的东西。看着这些东西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有的还要丢掉,他想,不过是箱子里的一堆破烂,突然,他心头一阵忧伤和沮丧——他想也许是人们所说的想家的感觉吧。
“有点像被拔了根,被移植了的感觉吧。”沈然突然在他身边说,王毅有点吓了一跳。
“好像小然体验过这种感觉似的。”王毅说。
“是的。”沈然说,
“那你——”
沈然耸耸肩膀说:“反正,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搬运工们在遮阳棚入口处停了下来,抓着绑着王毅和林琪的大双人床的盒子上的绳子问:“王先生,我们把这个放在哪儿?”
“放楼上……等一下,我带你们上去。”王毅向他们走去,接着停下来回头看着沈然。
“你上去吧,”沈然微笑着说,“我回去看看你的家人们怎么样了,然后送他们回来。我不打扰你了,不过搬家真是件令人口渴的工作。一起去买点汽水、然后来我家做客吗”
“好吧,也许我会去的。不过,别专门来找我,也别熬夜等我——我们今天真是乱透了。”王毅说,他倒是很喜欢王毅。是个好人,王毅想。只是,医生们对人总是好猜疑。
“只要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请柬就行了。”沈然说,在他那狡黠的笑里,王毅觉得有种东西使他感到克兰道尔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沈然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步子轻快。路易斯第一次对年轻人有种淡淡爱的感觉了。他看了沈然一会儿,然后和搬运工一起上楼。
---------------
沈然来到f镇已经有两个月了,这两个月来他几乎一无所获。有时候他甚至怀疑他是被人用折合人民币两亿元的材料来给做了个恶作剧,不过可能性不大。
多亏了那些材料,他制作出了一个中级傀儡。而高级的,还是遥遥无期。毕竟高级傀儡所需要的材料可是中级傀儡的一千倍。
不过,由于他把傀儡做得实在太漂亮了点,为此给他惹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不是对方给的材料已经用完了,他都打算重新再做一个了。
不过他也不算一无所获,至少他知道,如果镇有灵异的话,那么最有可能是在宠物公墓。
到晚上9点时,搬运工们走了。筋疲力尽的儿女都在自己的新房间里睡着了。小儿子睡在他的儿童床上,女儿睡在一张床垫上。
下午刚开始搬东西时,林琪抱着盖小儿子不停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打量着王毅让搬运工放家具的地方,不满意的地方就让他们重摆。最后大货车终于卸完了,路易斯从胸前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支票和20元一张的一些小费,给了他们,签了收据,站在门廊里,目送他们向大卡车走去。此时喝点汽水正合适,可惜没有酒。这使他又想起了沈然。
后来,夫妻俩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他看到妻子的眼眶周围的黑晕,说:“你,去睡吧。”
林琪笑着说:“是医生的命令吗?”
“对。”
“好吧。”她站起来,说:“我累坏了。小基晚上很可能会醒了不睡。你也来睡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还不想睡,街对面的那个年轻人——”
“不是街,是路。在乡下,人们叫路。
“好吧,‘乐’对面的年轻人。他请我去喝杯啤酒。我想我该接受这邀请。我也累了,可太激动了,睡不着。”
林琪笑了:“那你就快点去吧。”
王毅大笑起来,一边想,多可笑,多可怕,妻子们总能看出丈夫们在想什么。
路易斯耸耸肩膀,问
“他家里怎么样?”
瑞琪儿说:“看样子他是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她的女朋友非常漂亮,而且性情很温和。儿子竟坐在她的膝头。我很惊讶,你知道,今天儿子不舒服,而且他一般很难短期内喜欢上个生人。她还给了小雪一个洋娃娃玩儿。”
瑞琪儿举起自己纤细的手指,弯曲起来模仿成爪子模样。“不管怎样,路易斯,你别在那几待得太晚了,我在陌生的房子里总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王毅点点头,亲了她一下,说:“这房子不久就不陌生了。”
他走出家门,穿过马路去沈然家时,傀儡正在卧室补充能量,没办法见客。沈然则坐在摇椅上,他身边的音箱里传出二十年前的经典歌曲的声音。这一切使王毅感觉像到了家一样。他敲了敲门廊的门。
“进来,是王医生吧。”沈然说。
“希望您说的关于喝汽水的事是真的。”王毅边回答边走了进来。
“噢,关于喝可乐我从不撒谎。请人喝可乐撒谎会树敌的。请坐吧,大夫。我再多加点冰块。”
狭长的门廊里安置了几张藤椅和藤条做的沙发。王毅坐下来,惊奇地发现非常舒服。在他的左侧有一个锡桶,里面装着冰块和几罐可乐。他拿了一罐,边打开边说:“谢谢。”
他喝了两口,觉得沁人心脾。
“多喝点儿,”沈然说,“希望你们在这儿生活愉快,大夫。”
“但愿如此。”
“对了,要是你想来点饼干什么的,我可以给你拿些来。我有一大块准备好了的奶酪。”
“一大块什么?”
“奶酪。”克兰道尔的话听起来有些暗自好笑的味道。
“谢谢了,不过有可乐就行了。”
“好吧,那我们就只喝可乐。”沈然满意地打着嗝说。
“你女朋友去睡了?”王毅问,一边纳闷为什么沈然还开着门。
“是的。她有时熬夜,有时睡得早。”对于别人总是把傀儡误认为自己女朋友这件事,他遇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15号公路上一辆水槽大卡车隆隆地开过,车那么大,那么长,王毅都看不见路对面自己家的房子了。夜色中可以看到大卡车侧面写着奥灵科。
“这么大一辆卡车。”路易斯说。
“奥灵科是个化肥工厂,就在h市附近。这些车天天来来往往,这没关系。还有油罐卡车,装垃圾的卡车,那些白天去g市或z市上班,晚上开车回家的人,这是我对f镇不喜欢的一个原因。那条破公路,一刻也不让人安宁。”在万事屋里社里,他可从未在晚上感受过喧嚣。
而王毅经历过了s市那一刻不停的喧嚣,觉得f市这块土地出奇的宁静,所以他只点了点头。
“迟早有一天欧罗巴人会挑起争端,就在那公路上引发f洲似的暴乱。”沈然说。
“您也许是对的。”王毅举起可乐罐,惊奇地发现已经空了。
沈然大笑着说:“你再来一听,医生。”
王毅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只能再来一听,我得回去了。”
“当然了。你从没搬过家?”
“对。”王毅答道。接下来是一阵沉默。这沉默让人觉得舒适,好像两人相识已久。这种感觉王毅曾在书中读到过,但直到此时才体验到。
公路上又一辆车咆哮而过,闪烁的车灯像星星。
“这是条邪恶的公路。”沈然沉思着轻声说。他扭头看着王毅,嘴角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然后问,“你还记得你女儿说起的那条小路吗?”
王毅刚开始没想起来,小雪一天里说了一大堆的事。不过后来他的确想起来了。那条被修剪了杂草,穿过树林,蜿蜒伸向山边的小路。
“噢,记得。您答应以后要给她讲讲这条路呢。”
“是的,我会给她讲的。”沈然说,“那条小路在林中延伸约一公里半。这儿附近的本地孩子们打扫那路,因为他们总在这条路上来来去去……知道宠物公墓吗”
“知道什么?”
“宠物公墓。”
“宠物公墓?”王毅迷惑不解地重复说。
“其实不像听起来那么怪。”沈然边晃动摇椅,边抽着烟说,“就是因为那条公路。那公路上压死了很多动物。大多是狗和猫,不过不全是狗和猫。一辆奥灵科工厂的大卡车还压死了来家孩子们养的一只宠物洗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为什么要禁止养这些动物呢?”
“因为狂犬病,”沈然说,“现在h市总发生狂犬病。几年前有只狗疯了,咬死了四个人。真可怕。那时那只狗没打防疫苗。要是那些愚蠢的人给狗打了防疫苗的话,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
但是人们也可给烷熊和臭黝打免疫针,一年两次,而且它们一般不会得狂犬病的。然而来家的孩子们养的那只烷熊就打疫苗。它长得胖乎乎的,人们都叫它可爱的熊。
孩子们的父亲甚至花钱请了位兽医给烷熊作结扎和剪爪子,可花了他不少钱呢!我想洗熊的死一定使他们很伤心。来家小儿子哭了好久,把他妈妈吓坏了,都要带他看医生去了。这件事他们永远也不会忘掉的。一只宝贝宠物在路上被车压死了,孩子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王毅想起刚才看到女儿熟睡的样子,小猫丘吉趴在床垫边打呼噜的样子,于是说:“我女儿有只小猫,我们叫它丘吉。”
“它跟别的猫打闹吗?”
“什么?”
“它没被阉割过吗?”
“还没有。”
实际上还在芝加哥时,他们就考虑过这件事。林琪想给小猫作结扎,已经跟兽医约好了。路易斯给取消了,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不是因为怕小猫会给原来隔壁的胖女人惹麻烦,也不是因为他和小猫都是雄性。
主要是因为他不想毁掉小猫身上那种他欣赏的东西,那种在猫的绿眼睛里闪亮的无所畏惧的神色。因此他向林琪解释说,他们搬到乡下就没事了。而现在沈然跟他说乡下的生活要注意公路,问他小猫是否阉割了。真有些像命运的嘲弄。
“要是我,就把它阉割了。”沈然说,“小猫阉割后就不会乱跑了。要是它老是来回乱跑,就该倒霉了。就像来家的烷熊。”
“谢谢你的建议。”王毅说。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为何自己会在沈然面前表现的像一个后辈一样,明明自己比他大二十多岁。
“应该那么做,不过具体的要问问李老爷子,我知道的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沈然站起来说,“来瓶雪碧怎么样?或者我进去来块奶酪了。”
王毅也站起来说:“可乐都下肚了,我也该走了,明天见。”
“明天你就去学校开始上班?”
王毅点头回答说:“学生还有两周才开学,不过我应该早点知道我要做的工作,你说呢?”
“对,”沈然说,“随时欢迎你来,不过也请你去帮帮李老爷子的妻子,她有关节炎。”
“我会的。”王毅与沈然握手告别,“小然,认识你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你很快就会安定下来,可能会住很久呢。”
“但愿如此吧。”
王毅沿着随意铺就的小路走到公路边,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又有一辆卡车,后面跟着5辆小汽车向同样的方向开过去。王毅举手示意,穿过公路,走进自己的新家。
大家都睡了,一片沉寂。女儿好像一直没动,儿子仍在自己的儿童床里,仰面朝天,四肢摊开,床上不远处有只奶瓶。
王毅停下来看着儿子,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爱。他想主要是因为离开了熟悉的城市和那儿熟知的面孔。现在人们这么搬来搬去的,过去人们选中一个地方,就固定下来。这句话还真有些对。
他走近儿子,没人看见他,就是林琪也不在。他亲了亲儿子的手指,又透过儿童床栏杆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面颊。儿子笑了一声,转过身去。
“好好睡吧,宝贝。”王毅说。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悄悄地躺在床上,那床不过是两张单人床垫拼在一起罢了。林琪没动,王毅觉得一天的紧张开始消除了。
睡前他支起胳膊向窗外望,看到路对面沈然家的灯还亮着。王毅想,沈然还没睡,他可能要熬会夜,年轻人就爱这样。
他一边想着,一边睡着了。他梦到自己在s市,开着一辆印有红十字的白色篷车,儿子坐在他的身旁,梦中的儿子至少有10岁了。名叫丘吉的那只猫在篷车的挡泥板上,瞪着绿眼睛看着他。在19世纪90年代的火车站外的大街上,米老鼠被孩子们围着,它正用那带着白色卡通大手套的手握着孩子们信任的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