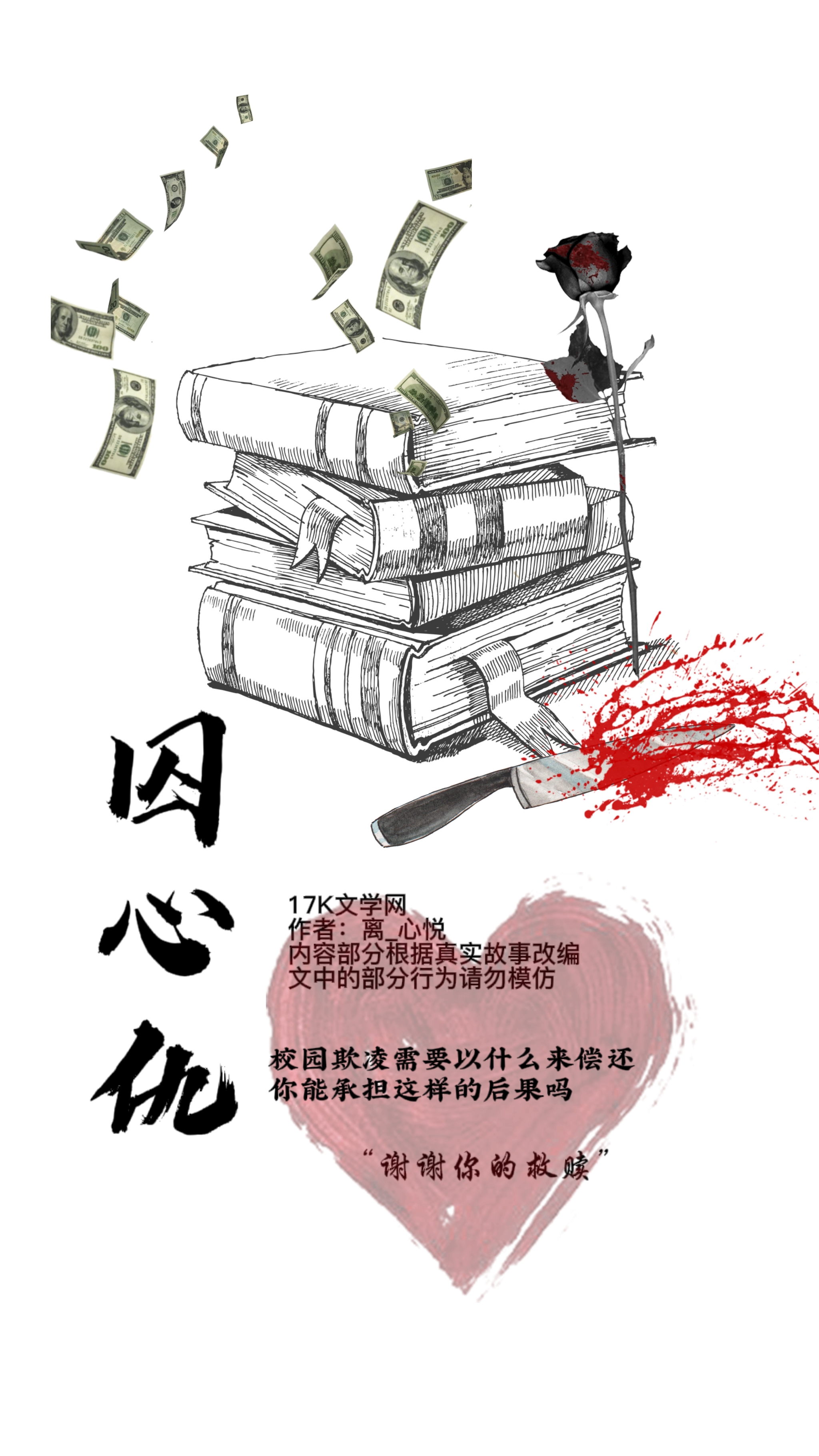安子鱼不得已撒了个谎,要是让王桂兰知道这个星期她在学校都干了什么,王桂兰怕是会更加担心。
“你们也快月考了吧,之前生病落下了些功课,你也别太拼,搞到一二两点都不睡,身体重要啊。”王桂兰握住了安子鱼的手,冰凉的皮肤让她暗暗心惊。她轻轻把安子鱼的手包了起来,让自己手心的温度传到安子鱼手上。
“嗯,知道了。”
安子鱼身体有些紧绷,但是没把手抽回来。手心手背都传来源源不断的热量,烫得她有些慌乱。
陌生,但是温暖得让人眷恋。
姨妈王桂梅住在镇上,和丈夫一起经营一家肥料店,现在已经在镇上盖起了两层的小楼房。王桂兰和王桂梅感情一直不错,逢年过节或者没事儿干的时候,两姐妹经常约着坐一坐,聊聊天。
安子鱼人好看,嘴也甜,王桂梅很是喜欢。听王桂兰说安子鱼生了场大病,她也忍不住担心起来。这下亲眼看到安子鱼,就更加担心了。
人还是那个人,就是不会笑了,也不没有甜甜地喊她姨妈,看着蔫蔫的。是不是身体还没好?王桂梅如此想到,一时间对安子鱼就更加关心了。
王桂梅嘘寒问暖,这摸摸那看看,从头看到脚,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似乎一定要搞清楚她的乖乖外甥女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安子鱼无奈,只得谎称自己只是发烧还没完全好,提不起劲儿。
王桂梅一听心想果然如此,亲手给安子鱼削了个苹果。
安子鱼和王桂兰在王桂梅家呆了大概三个小时,才开始动身去逛逛集市。或许是念着安子鱼还没有好利索的身体,也没走太远,但却把附近的女装、女鞋和精品店都逛了个遍。
王桂梅本来想生一男一女,但是却生了两个儿子。本来还想再生一胎,要一个女儿,但是夫妻俩眼看年纪也大了,安桂梅丈夫怕她身体吃不消,也就没答应。这大概也是姨妈为什么会那么喜爱安子鱼的原因吧。所以一进店,王桂梅和王桂兰两人就拉着安子鱼把店里还看得过去的衣服都试了个遍。从脚上的鞋到裤子衣服,还有头上带的帽子,一件不落。等逛完回家,安子鱼和王桂兰手里已经提了满满的购物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要过年了呢。
安子鱼大概这辈子都不擅长应付热情的人。全程下来基本上都是两个女人在说话,安子鱼也没有拒绝的机会。
中午在王桂梅家简单吃了个饭,两人就动身回家了。安子鱼看着王桂梅一步三挽留的架势,嘴巴像是被缝了线似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张口说话了。最后只得干巴巴地说了句“下次再来。”
告别王桂梅,安子鱼和王桂兰坐上了回家的大巴。王桂兰脸上都是满意的神色,笑得太多太欢,眼角的皱纹貌似都深了几分。
“下次我们再来的时候摘一点菜园里的豌豆尖来给你姨妈吧,她最喜欢吃那个。”
“嗯,好。”安子鱼轻声回答。
她上辈子的时间全都花在了怎么取得敌人脑袋上。无论是被王桂梅拉着聊家常,还是和两个长辈一起疯狂购物,都是极为新鲜的事儿。安子鱼虽然嘴上想着拒绝,但打心里喜欢这样的新鲜事儿,甚至开始享受了。
想到今天经历的,余光又看到脚边的购物袋,一根甜丝丝的藤,慢慢爬上心头,但没多久,这根藤便慢慢发黑,枯萎。
安子鱼想起了那些训练营里的孩子们。
那些年幼,却已经开始挥刀,学着杀人的孩子们。
而她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前世的安子鱼是个孤儿,是教官从废墟里捡来的孩子。她从小在训练营里长大,记事起就已经开始接受训练和培养。训练营里没有性别之分,无论男女,只有足够强大才能活下来,被军部接收,再依据各自的特长被收编进入不同的军种。所以在安子鱼短暂又漫长的17年里,别说是购物,连走出军营都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可以主导帝国发展方向的,从来都是有权有势的统治阶级。贫穷弱小的平民,连逃跑和反抗都做不到。帝国的未来是好是坏并不可知,至少安子鱼活着的时候不可能。
如果帝国能够解决内乱,完成统一,帝国的孩子们是否也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呢?他们或许再也不用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走进训练营,进行一年又一年残酷的训练,只为成为上位者手里听话的工具。他们或许能活着再次见到亲人,或许能活得久一点,体会一下普通人家的生活,也或许,永远留在了训练营的新兵冢。
安子鱼曾有多少战友,永远留在了那里。有的甚至没活过第一年。
安子鱼见过太多过早夭折的,他们的名字和相貌早已模糊,但是他们曾许下的愿望却深深刻在安子鱼的记忆里。
他们想再被母亲抱一抱。
想尝一尝除了营养剂以外的味道。
想穿一穿五彩斑斓的裙子。
想看一看爱莲娜歌姬演唱战歌的样子……
但几乎,都被埋在了新兵冢和不知名的战场上……
于是乎,现在手里拿的,身上穿的,甚至精神寄居的身体,都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背叛者。
她背叛了自己应该承受的黑暗,用手接住了一点点光明。
“小鱼。”王桂兰叫了叫安子鱼,却没见她答应,转头看去,安子鱼正安静地端坐着。
她身体坐得笔直,但王桂兰却在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她被压弯到地上脊背。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安子鱼,平静的脸,却让人无比清晰地感受到绝望、悲凉和无助。那双眼睛,背着车窗散落的光,像死寂的沼泽,黑得让人害怕。
陌生。
王桂兰心头一跳,这一瞬间,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可是她的女儿不就在眼前吗?眼睛看得到,手摸得到。一样的脸,一样的身材,一样的头发。
安桂兰应该很清楚自己女儿是什么样子。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他们血脉相连,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她的女儿会哭,会笑,会抱着她喊妈妈,会摸着她手上的老茧,也会调皮地给她涂口红……
这个不会哭,不会笑,不会喊妈妈,沉默寡言,不会和她亲近的人。
是她女儿吗?
那一刻,王桂兰只觉得身体发着虚汗,眼前发白,脑子嗡嗡响,心也在快速跳动着。她似乎啥也想不明白,但又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你是谁?”
此后的数年里,王桂兰多希望这句话永远不要问出口。
一句话把安子鱼从思绪中猛地拽了出来,她差异地看向王桂兰,心里惊了一下。
王桂兰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惊觉自己问了个多么荒谬的问题。她慌乱地抚了抚额角垂下来的碎发,用手遮掩住自己干涩发红的眼睛,嘴角不自然地抽动着。
“哎呀,刚刚,刚刚好像听见有人叫我呢,咋一仔细听又没了呢……”王桂兰手忙脚乱地挪了挪脚边的袋子,试图掩饰。
但这样的掩饰,实在是漏洞百出。
安子鱼也是一个不会演戏的人,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欺瞒王桂兰多久。
他们迟早会知道真相,只不过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安子鱼的默不作声让王桂兰莫名的心头绞痛,眼角已经在不知觉中湿润。
一路无言,到家的事后,已经是下午将近下午三点钟。
他们也没又打电话让安正康出来接,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提着大袋小袋,慢慢走在草木枯黄的小路上。安子鱼几次想要上前接过王桂兰手里的袋子,但是又不敢往安桂兰面前凑,只能安静地跟在她身后。
安正康在妻子一进门的时候就察觉到了异样。但是在安子鱼面前也不好问,于是把王桂兰拉到了房间里。
“这是怎么了?不顺利啊?”
王桂兰不知道该怎么和安正康说,也不愿意说,她自己心里也是一团乱。只是想到车上的情景,鼻子又开始泛起了酸意。
“我……我不知道,顺利是挺顺利的,但是……”
“但是啥呀?”安正康有些焦急,“哎呀你说呀。”
王桂兰被问得冒了点火气,“我现在不想说,晚点再说吧。”
“晚点”的意思可能是今天晚些时候,也可能是几天之后。安正康看现在也问不出什么,也就没再追问,转身出去了。
安正康回到菜园子里除没除完的草,见安子鱼蹲在鱼塘边上看鱼,也没去打扰她。女人们的心事他不过多追问,他们想明白了自然会说。
很快,该吃席的时间也到了。一家三口出了门,往王家方向走去。
虽是嫁女儿,但是来吃席的人并不多,加起来也不过五六桌席。
安子鱼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身穿一身红色的女人,不,叫女孩儿可能更合适些。昨天听王桂兰说,她也只有15岁。
女孩儿身材瘦小,皮肤偏黄黑,脸上的妆容却过白,和脖子形成鲜明对比。艳丽的口红涂在她的嘴上,像是浮在表面,并没有达到增加气色的目的,反而在白色的脸上红得有些异常。黝黑的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餐桌里的鸡肉出神。她穿的红色嫁衣貌似也不合身,肩膀处明显宽出了一大截,和她小巧的脸以及纤细的脖子组合在一起,既别扭又违和。
她安静地坐在一片灰黑色的人群中。明明身着热烈的红色,却透露着的孤独和冷漠。
安子鱼坐的地方和新娘离得比较近。她不留痕迹地观察着这个女孩儿,却被她衣领下露出的伤疤吸引住了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