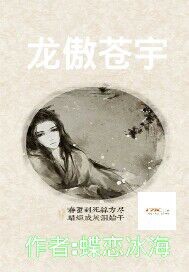魏母下葬完后,钱星簇兀自跪在母亲坟前,何阳燧送走帮忙的邻里,也陪在一旁,日渐高照,忽觉腹中饥饿,想起两人已许久滴米未进,怕钱星簇饿坏了肠胃,正打算出去寻些吃食,却见钱星簇忽的站起身来,提了铁枪一言不发朝外面走去。何阳燧心知他的用意,上前拦住,道:“他们虽骑了马,但带着一个病人,走不远的,你一夜未眠,还是身体要紧,待歇息片刻养好精神以后再议复仇之事。”钱星簇冷冷回道:“不杀了那几个贼人,母亲在黄泉之下始终受屈,我又如何能坦然入睡?”何阳燧见他复仇心切,心里对那几个人也是恨之入骨,当即说道:“好,既然你这么想报仇,我便随你一起上路就是。”钱星簇惨然一笑,点了点头。
钱,何二人当初在窗外听到那络腮胡说到,他们口中的扶大人着急回京复命,相必一行人也是奔了北方而去,两人在家中简单收拾了些衣物干粮,又拿了家里剩下的几钱碎银,收拾妥当之后当即出发,那络腮胡一行人均是士卒装扮,又带着一个病人,走在路上甚是醒目。钱,何二人打听起来也非难事,两人一路北上,且行且寻,如此走了四五天。
这一日两人正行进间,远远瞧见前面一座县城,何阳燧向路人一打听,原来已走到了临澧县,眼见天色渐晚,二人一商议,决定先进城里找个客栈住下来。
钱星簇离家的时候只带了家里仅剩的几钱银子,何阳燧长在道观,与师父同吃同住,平日里没有花钱的地方,此时更是身无分文,两人一路省吃俭用,饿了就打些野兔田鼠充饥,渴了便就地生火烧些雪水喝,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临澧,待付完房费,身上银子早已所剩无几。
钱星簇将身上所有的钱摊在桌上,只剩下几十个铜板,叹了口气说道:“咱们只剩下这些钱了,只怕付了房钱后,下一顿饭也吃不上了,今晚就先挨饿忍忍吧,明日一早我去城外再打些野物回来。”
何阳燧见他忧心忡忡,摆摆手道:“要弄些钱财有什么难的。”钱星簇奇道:“怎么,你有办法?”何阳燧微微一笑,道:“今晚我便去当地县衙府库里盗些银钱,以供咱们赶路使用,反正那些官府平日里鱼肉百姓,压榨来那些钱财也是为了自己享乐,我们盗取一些,也算得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钱星簇恍然大悟,当即赞同。
明朝严行夜禁制度,待到半夜,街上早已无一行人,何阳燧起床洗了把脸,振奋精神后从窗户翻了出去,直奔衙门而去,本来钱星簇是想一同前往,只是轻功较何阳燧稍逊,又怕两人目标过大,被人发现,为了免生事端,便留守在了客栈中。
行了约莫一顿饭的功夫,何阳燧已到了县衙门外,只见衙门大门紧闭,又绕到后墙下,那里种着几棵槐树,何阳燧心下寻好路径,双足运劲,一跃而起,右足在槐树上微一借力,一丈来高的围墙便轻轻跃了上去。
因为生平从未来过衙门,何阳燧不知里面是何布局,只想着从后墙翻进去准没错,岂知这后堂是县令平日睡觉歇息的地方,往往等到晚上,大部分衙役下班回到自己家里,而县令则睡在县衙后堂,只两三名衙役留守陪伴,以便遇到突发事件当即处理。何阳燧从后墙翻进,此时正好面对着县衙后堂,瞧见屋里烛影晃动,映出几条人影,似在商议什么事情。何阳燧正自纳闷,心想:“这县令大半夜不睡觉干什么,定是在商量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且让我也听上一听。”想毕从墙头轻轻跃下,悄无声息,转到门前,又见有两名衙役把守,心里疑心更起。当下悄悄绕了回去,施展轻功翻上屋顶,轻轻揭起屋顶上一片青瓦,眯起眼睛朝里张望。
只见屋内一人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何阳燧瞧着那人身着朴素,戴着一顶破毡帽,身形魁梧,面貌丑陋,脸上挂着一条大刀疤,下巴还长着一个大脓包,甚是骇人,何阳燧新生厌恶,又见在他下面站着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府内衙役,另一半则穿着平常,跟那刀疤脸倒像是一伙。几名衙役面前又站着一位老者,身着官服,满面皱纹,留着一撮山羊胡须,想来便是当地的县令了。何阳燧心下却好奇:“为何那县令让一个寻常百姓居主座,偏偏自己站在下面,想必那刀疤脸是有些来头了。”
那刀疤脸忽的猛一拍桌子,愤然道:“李大人,怎么临澧城内进了这帮流氓土匪你也不知道,幸好老子福大命大,及早发现,否则我们几个已经变成几具死尸了。”何阳燧听着这声音有些耳熟,觉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却一时想不起来。
那县令年老力衰,颤巍巍上前一步,拱起手来,道:“都怪下官治理无方,才让那帮恶匪流窜到本县肆意妄为,还望常大人恕罪。”方才何阳燧就觉得那刀疤脸的声音熟悉异常,此时“常大人”三个字一说出口,何阳燧蓦的一愣,立刻想起自己兄弟二人追的那个络腮胡也姓常,两人声音竟也是如此相似,只是样貌大相径庭,何阳燧满腹疑窦,一时不敢确认。只见刀疤脸摆摆手道:“罢了罢了,既然没发生什么意外,你这条命先记在我这,不过你须得护我们几人周全,否则扶大人怪罪下来,你可知道后果?”那县令冷汗直冒,连连称是。
这刀疤脸又一提“扶大人”,何阳燧心里已有了七八分答案,料想这人便是那个络腮胡,只是为了躲避他们二人追杀,在逃亡路上剃了满脸的胡须,又粘上一条偌大的假伤疤,至于那几个脓包,八成也是什么乔装易容的把戏了。如此一算定,何阳燧便有了十分把握,正想下去生擒了刀疤脸送到义兄面前,好了了他的杀母之仇,心下却犯了难,这屋里少说也有十七八人,多多少少都会些武功,自己又手无寸铁,任凭本事再高也难以生擒了他。
正踌躇间,忽闻门口传来两声闷响,接着又是两人扑倒在地的声音,屋内十余人听到异响,纷纷受惊,抄起身边的长刀短剑向屋外奔去,何阳燧也是一惊,悄悄从屋顶上爬了过去,只见把守在门外的两名衙役倒在地上全无声息,不知死活。
何阳燧看到此时院里除了刀疤脸和李县令的人,又多出了六人,其中五男一女,手中均拿着怪异兵刃,门口的衙役想必也是被他们打倒的了。何阳燧注意到那六人中有一人高鼻蓝目,身形高瘦,明显是异域人士。只见他站了出来,冲着刀疤脸道:“常交氏,快让我杀了你。”何阳燧心下好笑,心说这络腮胡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
原来络腮胡原名叫常乔时,这蓝目人生在欧洲,虽会说中原话却口音难改,发音怪异,硬生生将“常乔时”叫成了“常交氏”,说起话来也带着欧洲人的特点,全不似中原人,在场余人不禁暗笑,却不敢表露出来。
蓝目人的一名同伴见他与人交谈甚是困难,自己还浑然不觉,当下微叹一口气,转而一脸怪笑道:“姓常的,今日侥幸让你在客栈里跑了,本以为你去找了什么厉害人物护你周全,原来是个不中用的老头子,现下看你还有命能活到几时。”说话这名同伴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个子不高,脸上留着一副八字胡,却是一脸的不正经,看上去十分猥琐。
此言一出,只见常乔时满脸怒气,一言不发,似乎早就知道这些人要来。原来络腮胡一行人当日带了公子一路北上,行进甚是缓慢,过了两日,常乔时心里一琢磨,反正身边带着扶公子,骑马也走不快,跟走路没什么差别,那两人武艺高强,随时会追上来,于是当机立断,命一行人放掉马匹,换了一辆破旧马车,让扶庄龄和那名大夫坐在里面,余下几人均换掉衣服,乔装打扮,一路徐行,竟与钱,何二人同一日抵达临澧县,只是较他们早了几个时辰。
等一行人进了城便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栈住了进去,常乔时安置好扶庄龄后带着手下去楼下吃饭,几个人点了一桌大鱼大肉正在吃喝,忽然从门外跑进一个孩童,在店里环视一周,看见了常乔时,径直走到他面前,却是一言不发,在桌上扔下一张纸条便匆匆跑了出去,常乔时奇怪,拿起纸条一瞧,瞬间冷汗涔涔,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限一个时辰内交出扶庄龄,否则你等狗命不保。
常乔时正自纳闷:“按理说那二人要杀的是我,何以又要我交出扶庄龄?难道写这纸条的另有他人?”当下收起纸条,急忙起身去追那孩童,那孩童见他凶神恶煞来追,吓得拔腿就跑,可一个六七岁的孩童又怎能跑得过一个大人,刚出了客栈没多远就被常乔时一把抓住。
常乔时抓着那孩童的衣领怒道:“是谁派你来的!”那孩童哪经得住这般惊吓,当下嚎啕大哭,颤声道:“我…我不知道,那个姐姐给了我一两银子,让我把纸条交给你,别的什么也没说”说罢将右手手掌摊开,果然是一锭银子。
常乔时见这小孩不像说假话,只好将他放开。那小孩连忙一溜烟跑进人群里,一会儿便没了身影。常乔时定定的看着那孩童的身影渐渐消失,内心绝望之极。正消沉间,猛然瞧见前方不远处的街角有五六人正盯着自己,装扮怪异,与周围百姓格格不入,常乔时吓了一跳,再一看,忽的那几人又不见了踪影,片刻之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轻功之高恐怕连何阳燧也比之不及。常乔时长叹一声,只道是天要绝人之路,回到客栈里派手下去找当地县令求救,正是当日烤兔肉的那个矮子,那矮子虽说平日里好吃懒做,但好在没皮没脸,善与人打交道,是以常乔时派了他去衙门交涉。等那矮子到了衙门门口说明来由,衙役一通报,说是扶熙品扶大人的手下,李县令哪敢怠慢,赶忙派了人去客栈接常乔时一等人,又是一路殷勤招待,哪里还用得着交涉,那几人不便在白日闹市中动手,盘算着待到晚上再动手,是以一直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他们进了当地县衙。
等到了县衙里,李县令派了十几名衙役保护常乔时一行人,但常乔时始终不知那几人底细,竟是连觉也不敢睡,一直守到了半夜,直到此时那几人追上门来。
常乔时暗压怒火,拱手道:“扶公子整日里与属下待在一起,未曾离开半步,又不知因何事得罪了几位英雄,特地前来为难。”
八字胡嘻嘻一笑,道:“我们与扶公子未生矛盾,只是想借他一用,向扶熙品扶大人换一样东西,待事成之后,定将扶公子完好无损的送回府上。”
常乔时心说不知哪里来的这帮无理取闹的家伙,却偏偏武功高深莫测,打又打不过,当下回道:“在下受命保护扶公子,若是有什么差池,就算回去了也是难逃一死,还望几位高抬贵手,饶了扶公子,也放了我们兄弟几人一命”
八字胡回道:“这好办,只要你将星弧符交出来,倒是可以饶你一命。”说罢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尤为尖锐,摄人心魄,听得众人心情烦躁郁闷之极。
常乔时沉吟片刻,道:“星弧符这么重要的东西,扶大人又怎会交给我,他早已带着回京了。”那八字胡微一愣,喃喃自语道:“扶熙品那老家伙为了这东西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接着又冲着屋里喊道:“看来只能先让请扶公子跟我们走一趟了,等你爹爹取了东西再把你换回去。”这话明显是冲着常乔时说的,言外之意就是若常乔时再不交出扶庄龄,便要动用武力了。
常乔时到了县衙之后便将扶庄龄藏在屋内,原想着若运气好便能逃过一劫,此刻却进退两难,交也不是不交也不是。正踌躇间,八字胡身后一位年轻女子站了出来,淡淡说道:“原来常大人另请了高手助阵,也不必躲躲藏藏的了,还请现身吧。”这女子眉清目秀,外表文静,肤色白皙,俨然一副小家碧玉的样子,心思却缜密,怕常乔时暗中设了高手助阵,是以方才一直站在同伴中不言不语,留神四周,此刻突然发话,在场李县令和常乔时及二人手下皆是一惊,面面相觑,心道自己哪有请什么高手助阵,却不知只有在屋顶上偷窥的何阳燧听出了那女子的用意。
眼见行踪已露,再躲着也不是办法,何阳燧从屋顶上轻轻跃下,显出一身高明轻功,常乔时一瞧心下大骇,这不正是当日那位使用暗器功夫的青年吗,心底只是暗暗叫苦,怎的他在屋顶上偷听了这么久都没人发现,恐怕早已知晓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低下头去,不敢看他。
何阳燧冲着众人环顾一周,目光落在常乔时身上,道:“诸位误会了,在下并不是这奸贼请来的帮手,实不相瞒,我义兄与这奸贼有杀母之仇,此行正是为了生擒他替义兄报仇。”
没想到那八字胡根本不担心他是什么帮手,却哈哈大笑起来,道:“年轻人,我看你功夫甚好,怎的江湖阅历如此浅薄,让我师妹诈一诈你就当场泄了底?”何阳燧一愕,当下明白过来,原来那女子并未发现自己的行踪,只是夸口虚说一句,没想到自己偏就上了当,正中其下怀。何阳燧当即冲她瞪了一眼,那女子见他面貌俊朗,又想他不惧生死为义兄报仇,只道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儿,当下莞尔一笑,脸泛潮红,默不作声。若放在寻常男人,有女子对自己如此羞涩而笑,对其心意早已明朗了七八分,只是何阳燧自幼与师父长在山上道观,于男女之情一窍不通,此时自然未得领会,只觉得她是个狡诈又不讨喜的女子。
那八字胡见何阳燧面含怒色,本想开个玩笑,却落了个无趣,便岔开话题,冲常乔时道:“姓常的,你的仇家还真是多啊。”说罢转向何阳燧,道:“这样吧小兄弟,我叫刘景和,咱们今日交个朋友,和气相处,我抓我的扶庄龄,你抓你的常乔时,各取所需嘛。”何阳燧心想办正事要紧,微微一笑,报了自己姓名,接着道:“如你所说那再好不过。”说罢两人上前一步,当即就要对常乔时等人动手。
此时忽闻木门响动,吱呀一声,从里屋走出来一位青年,脸色苍白,面容憔悴,看见院内站着众人大惊失色。常乔时见他出来,连忙喊道:“扶公子,你怎么醒了,快回屋去……”话还未讲完,那八字胡手疾眼快,几个箭步冲上,一把将那青年抓住,施展轻功,片刻间又回到了同伴身边,行动迅速,中途竟没一个人能拦下,几名衙役片刻才恍然回神,立即就要冲上去救下扶公子。
常乔时连连摆手,大声喝令几名衙役退下,生怕将那八字胡激怒,下毒手对扶公子不利。
八字胡一行人见人已擒到,冲何阳燧大笑两声:“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兄弟我要走啦,这姓常的可就交给你了,替我多砍两刀啊。”说罢扬长一笑,一行人就要离开。何阳燧听闻连忙拦下,道:“刘兄弟,我仅凭一人,可没法敌得过他们十几人,还请刘兄弟留下助阵,刘兄弟武艺高强,只需片刻就能制服他们,也不会耽误了你们的事。”
那八字胡天生喜交朋友,却鲜少真心与人相交,只要不是敌人便以兄弟相称,又偏爱看人难堪,常常叫身边朋友当众下不来台,平日里同伴都对他心有不满,但念他天性如此,如无造成严重后果,也都是能忍且忍。他听到何阳燧这一番话,当即生了兴致,嬉皮笑脸道:“何兄弟武艺比我高出不知多少倍,此刻就别谦虚了,杀了这几个小贼还不是易如反掌,我相信兄弟的本事。”说罢提了人质就往县衙外走去,走到一半忽的想起一事,扭头又道:“对了何兄弟,你可别杀光了啊,还得留一条狗命回去给他们主子报信呢。”说完又向常乔时一干人等喊道:“老子就在北京城里等他。”常乔时众手下一听,均是面露怒色,却不敢发作,只能默默站在一边,期盼这几人早点离开。
何阳燧凄然一笑,回道:“既是如此,还请兄弟赐一兵刃,总不能让我空着手跟他们打吧?”那八字胡微微一愣,低下头默不作声,随身保命的武器又怎能轻易赠人?沉寂片刻,只见事前那女子又走了出来,将手中一件亮闪闪的物什抛了过去,何阳燧抬手一接,原来是一柄短剑,雕刻精美,剑柄上镶一颗蓝宝石,不似一把杀人的利器,倒像是一件富贵人家的装饰品。只听那女子淡淡说道:“这把短剑跟了我八年,甚是喜爱,还望公子好好妥善保管,若是日后有缘相见,再将它交还与我。”何阳燧虽对她无甚好感,但毕竟受人恩惠,当下一拱手,道:“多谢姑娘赐贵兵刃,在下定当好好珍惜。”那女子点点头,不再答话,跟着同伴走了。
见那一行人消失在夜幕中,常乔时心下一宽,心道:“少了几个棘手的,剩下这一个虽也厉害,却也勉强敌得过,今日这一条命算是有希望保住了。”何阳燧却犯了难,不知该走还是该留,正犹豫间,转念又想到义兄这几日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当下心一狠,决定留下以死相搏,只见他突然上前几步,施展擒拿手,抓向面前一名衙役咽喉,那衙役闪避不及,立即被擒住,由于咽喉被扼,气血不畅,何阳燧又使得一手巧劲,那人当即满面通红,白眼上翻,何阳燧手上微一用力,那人喉骨竟被活生生掐断,当场气绝。事发突然,其余衙役都是一惊,纷纷拔刀冲了上去,李县令和常乔时则远远躲在一边,生怕自己像那衙役一般下场。
眼见十几人手举长刀朝着自己扑来,何阳燧面无惧色,拔出那女子所赠短剑,只觉得剑刃锋锐,寒光逼人,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暗道一声好宝剑!挺起剑锋,向一人心口刺去,只听噗的一声,那人胸口当即血流如注,一命呜呼,何阳燧不待余人扑上,立稳重心,反手用剑格挡开几柄落下的长刀,在人群中左躲右闪,身法微妙,有时眼见右脚就要踏出,却瞬间伸出了左脚,身子要往前倾又突然倒向朝后,这是师父传授他的云杪棍法中的身法,云杪意为虚无缥缈,似云似雾,要求练习者身法灵动,半真半假,叫敌人猜不出自己招数,防无可防,攻又不敢攻,只是此时他变棍为剑,使将起来倒也不失威力。只听得一群人中连连传来惨叫,顷刻间又有五六人倒地,或是心口中剑,或是咽喉受创,均是致命伤口,鲜血似一张红毯铺了满地。剩下十几人见此情景,慌忙退散开来,一时竟不敢再靠近,围成一个圈将何阳燧远远包围起来。
身边十余人对自己或是怒目而视,或是惊恐万分,均是想将他置于死地,何阳燧望着那些人的眼睛,恍然间想起师父平日教导自己不可轻易杀生,又想起这些人也都是爹生娘养,有妻子家室,如今杀了他们,不知又有多少如义兄那般的家庭惨剧发生,心神一恍惚,背后一人突然冲上,抬手一刀,直直砍在何阳燧肩上,何阳燧只感肩膀一阵剧痛,心下大怒,心道这些人也只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最大的恶人还是躲在一旁的常,李二人,想罢飞起几脚,踢开挡在他二人前面的衙役,提剑刺去,常乔时反应迅速,连忙拉过身边的李县令挡在自己前面,那李县令年老体弱,间何阳燧杀的性起,两眼通红,剑锋还没指到面前早已吓得昏了过了,躺在地上已然气绝。
何阳燧轻哼一声,饶过了他,转而瞪着面前的常乔时,正欲上前动手,常乔时见再无可逃,心下大骇,连忙喊道:“英雄且慢动手,我有一事要说。”何阳燧只道他是人之将死,想尽办法求饶而已,停下脚步说道:“你我素无交往,要说什么事又与我有何干系?”常乔时见他并不上当,颤声回道:“其实…其实我昨日在那片梅树林里就已见过你们,那时我正路过哪里,看见两人在树林里交谈,其中一人正是那跟你一起的那位英雄,另一人想来便是你了,于是悄悄摸过去想偷听,结果发现他对面那人是一陌生男子,你猜他向那人说了什么?”何阳燧听到常乔时提及义兄,心里犹豫一下,只怕是什么阴谋诡计,又听他提到梅树林,想想自己昨日确是经过那片梅树林,便又相信了几分。其实这几天常乔时与何阳燧两人赶的都是同一条路,常乔时在路上见过那片梅树林,何阳燧自然也见过,只是常乔时随口拿来圆谎,让他相信而已,加之何阳燧江湖阅历甚浅,不知人心叵测,于是放下戒备,道:“那你说罢,我听着便是。”
常乔时嘿嘿一笑,走上前去,做欲说话状,手里向身旁手下使一手势,那手下是常乔时的亲信,两人心照不宣,当即领会,从怀中悄悄掏出一个小纸包解了开来,不由分说便朝何阳燧脸上洒去。
何阳燧并未察觉身后异动,只觉眼前忽然白茫茫一片,急忙后退几步,接着感到一股强烈的灼烧感在双目升腾,原来那手下洒的是一包生石灰粉,是常乔时日间派人买好,以便偷袭所备。何阳燧小时候听师父讲授药理,知道生石灰入了眼剧痛无比,不可手揉,亦不可用水冲洗,只能让旁人用干布擦拭干净。只是此时身陷险境,孤身一人,却不知如何应对。
常乔时大笑几声,看准时机拔出腰间短刀向何阳燧砍去,何阳燧视觉模糊,见有一团黑影向自己扑了过来,只是分辨不清那人动作,无法招架,只得施展轻功,躲向一边,在院子里乱跑乱撞,常乔时大怒,举刀又追,何阳燧正跑间,冷不丁感觉到脚下一软,原来是踩到了地上衙役的尸体,当即绊倒在地,常乔时见时机正好,抬手一刀,正砍在何阳燧后背,只听“嗤”的一声,划出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汩汩流下,片刻间满背殷红。
何阳燧身负剧痛,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心中只叹自己本事低微,不能替义兄圆了心愿,也不能替世间除掉这恶人,又道上天无眼,只叫好人枉死,却让恶人长活,心中绝望至极,只等那贼人最后一刀落下,了结了自己性命。
常乔时见他心灰意冷,决意受死,心中暗喜,举刀向他心口砍去,忽听“铮”的一声,刀身转向飞去,“哐啷”一声落在地上。何阳燧知是有人相救,勉强睁大双眼一瞧,只见一细长之物横在眼前,长物一端闪闪发光,心下大喜:这正是义兄钱星簇所使的长枪。
原来钱星簇独自留守在客栈里,等来等去久久不见义弟归来,心里着急,便提了长枪,一路上小心翼翼的摸到了县衙,刚到门口二里有余,远远瞧见几个黑影闪动,一晃便没了踪影,以为是义弟惊扰了官府里的人,心说糟糕,赶忙冲了进去,这才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何阳燧一命。
钱星簇见院内横躺着几具尸体,又见义弟身上两处偌大的伤口,双目红肿,甚是奇怪,心道义弟只是来盗些银两,怎的无端端又闹出几条人命来?当下俯身查看他的伤势,又扯去身上一条衣衫,替何阳燧简单包了伤口,拭去眼里的石灰粉。
钱星簇不认得此时的常乔时,以为他是衙门里的人,那常乔时却认得他,心想若是被何阳燧点破自己的身份,定是在劫难逃,于是趁着他为义弟包扎伤口的时候,带着手下悄悄朝着县衙后门奔去,那里候着几匹李县令事先备好的良驹。何阳燧视力尚未恢复,但能朦朦胧胧的瞧见五六人朝着后门奔去,料定是常乔时等人,只是背上的伤口疼的他说不出话来,只能一手抓着钱星簇的衣袖,一手指着常乔时一行人。
钱星簇还以为是何阳燧让他去替自己报仇,说道:“义弟,你且在这好好休息,我这就去追赶他们,那几个贼兵跑不了的。”说罢提起长枪上前几步,一招“游龙出海”,分别刺中两名跑在最后的随从的小腿。那两名随从腿部吃痛,双双扑倒在地,见逃跑无望,跪在地下连连求饶。钱星簇瞧着那两人怒然喝道:“我义弟只为求些银钱,何以如此痛下杀手?”那两名随从不知如何回答,只是一味求饶,还有一人冲着身后喊道:“常大人!常大人!救命啊!”常乔时此时哪管得了手下性命,只自顾自的翻身上马,死命扬鞭,听得马儿一阵悲嘶,几骑马扬长而去。
何阳燧满心焦急,忍着剧痛叫道:“常大人…杀母凶手…快追!”此言一出,钱星簇满心奇怪,思索片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人就是自己苦苦寻了几日的仇人,现下却被自己眼睁睁的放走,顿时勃然大怒,反手两枪刺死了跪在地上的两名随从,施展轻功追了上去。
何阳燧身负重伤,无力再追,在县衙内待了这许久,眼见天空星光渐暗,过不到一个时辰就要转夜为昼,将手中的短剑收入怀中,又在几名衙役身上搜出几两银子,趁着天未亮一路摸索着回到了客栈里。
经此一役,何阳燧深受重伤,临澧县衙官兵死伤大半,有七八人侥幸逃生,其中一半人是常乔时的手下,当晚跟着常乔时一起骑马逃走,另一半是李县令手底下的衙役,这些人不敢再回县衙,有的在临澧城中躲了起来,有的干脆跑回了老家,将此事烂在肚里,绝不对外人说一个字。衙门平时鲜有百姓上访,这几日又大门紧闭,是以周围居民虽觉得有些奇怪,却也没发现衙内惨案。何阳燧在客栈里直等到天明才见到钱星簇灰心丧气的回来,想来也是两条腿跑不过那四条腿,眼睁睁的让那常乔时捡回一条命,心中苦道下一次再碰到他不知还要等上多久。
这几日,钱,何二人一直藏在客栈里,白天不敢出门,也不敢去药铺买药,所幸身上还有搜来的十余两银子,便委托店小二帮忙买些简单治外伤的药膏,又付了房钱,二人在房里每隔两个时辰换一次药,加之何阳燧自己运气疗伤,幸得他年轻气盛,筋骨健壮,过了几天,已能下地走动了。
两人在客栈中待了几日,时时想起当晚县衙中发生的惨状,虽二人武功高强,此下又是为了报亲死之仇,但二人初出江湖,以前从未杀过人,回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尤其是何阳燧,常常在半夜被噩梦惊醒,又怕再多待上几日县衙里东窗事发,于是相互一商议,决定另谋去处。
那常乔时认得钱,何二人是廖子坪村人,此次放虎归山,待他回了京城,禀报扶大人,定会领着大批高手回去寻仇,眼下廖子坪村是不能回去的了,如今杀母之仇还未得报,却惹上一身命案,两人只道自己阅历太浅,应付不过久混江湖庙堂的常乔时,商量了许久,二人决定一路北上,无论如何也要豁出性命去,将血海深仇报了再说。
这一日清晨,二人用毕早饭,钱星簇出了客栈去镇上集市,准备买两匹马以便赶路所用,何阳燧伤势尚未痊愈,便留在客栈里等他。到了集市,钱星簇一打听马匹价格,询得随便一匹普普通通的马都要六七两银子,更别提那些强壮力盛的良驹。这下心里犯了难,手里只有十余两银子,若都拿来买了坐骑,日后那些吃喝用度琐事支出又该如何应对?旁边的灰驴倒是便宜,二两银子一头,不过骑着游山玩水倒还够用,长途赶路又是不足。那牲口贩子与他议价半天,见他仍是犹豫不决,心里有些不满,生气道:“你这人真奇怪得紧,从早上与我一直谈价谈到晌午,到底还买不买了,要是没钱买快别挡着我做生意!”钱星簇见他已无耐性,知道这价钱是再也砍不下去了,一狠心,决定买两匹马,至于以后的用度,等上了路再想办法吧,当下从怀里掏出十几两银子,正欲交到那牲口贩子手里,此时身旁一人忽道:“小兄弟若要赶长路,这等品相的坐骑可是不妥。”钱星簇听闻此人言,刚伸出的手又收了回来,朝身旁一瞧,只见是个中年男子,穿一身青布长衣,留着少许短髯,目有精光,容貌甚伟,全不似寻常百姓。那牲口贩子见即将到手的银子又没了,怒冲冲朝那人瞪一眼,也不说话。
钱星簇凄然一笑,回道:“晚辈亦想购得两匹良驹,实在是囊中羞涩,现下买了这两匹马,日后的吃穿用度还不知从何处谋。”那中年男子哈哈一笑,拱手道:“小兄弟可是姓何,名阳燧?”钱星簇见此人陌生,却知道义弟的姓名,心里顿时生了戒备,怕是有人来找义弟的麻烦,索性自己先探探虚实再说,当下回了礼,道:“不错,晚辈正是何字姓,名阳燧,不知前辈有何指教?”
此言一出,中年男子顿时心花怒放,喜形于色,也不回答他的问题,从怀里掏出一锭金子,交给了那牲口贩子,嘱咐他挑两匹最好的马给钱星簇。那牲口贩子一看见金子,又见那人样貌不凡,只道是财神爷下凡,瞬间转怒为喜,连连称是,挑了两匹最好的骏马交予钱星簇手中。
钱星簇从未受人如此大的恩惠,此时云里雾里,不知此人是何用意,问道:“在下与前辈素不相识,不知为何前辈慷慨相助?”那人却不回答,一抬头见日头高照,已是午时,便道:“如今已到饭时,还请何兄弟到饭馆用些酒菜,我自当将其中原委一一道来。”钱星簇见他并无恶意,便应允了下来,当即牵了马与他同行,一路上钱星簇又问了几次,那中年男子只是笑而不答,钱星簇也只好作罢。
直等到午后,两人在一家饭铺吃完了饭,那中年男子见桌上碗盘大半皆空,这才心满意足,微笑道:“咱们二人可以说素未相识,却又在几日前已成了朋友,那天晚上,我麖教六名兄弟已与何兄弟在县衙里见过面,师妹黄景仪还将随身宝剑赠予何兄弟,此事可还记得?”原来这中年男子名叫西景昌,与那晚劫持扶庄龄的八字胡一行人同属一个门派,是他们六人的师兄。这几日西景昌正在临澧附近办事,带办完事后回去的路上偶遇六人,见他们毫发无伤劫来了扶庄龄,甚感欣慰,问及详情,刘景和便将当晚发生的事连同遇见何阳燧的事一齐说了,还笑道找了个傻小子替自己挡了那些黑皮衙役,黄景仪在一旁听得颇为不满,但他们几人中自己辈分最低,心中有怨言也不好发作,只得暗自生闷气。
西景昌为人谦和,深谋远虑,听完刘景和一番话只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又身负不凡武艺,当下爱惜贤才之情顿起,数落了刘景和几句便匆匆与六人分手,进了临澧城中寻找何阳燧,想将其纳入自己门下。
西景昌进了临澧城中先是去了趟县衙,见满地尸首兀自未动,又找不到何阳燧的尸体,心里一宽,知道他还没死,便四处打听,却一无所获,正自失落。前一日碰巧在钱,何二人所住客栈中吃饭,偶然听见店小二与旁人闲聊,说店里住了两个怪人,平日里窝在房中极少出门,一出门不是要些酒菜就是让自己帮忙去药店买药,虽是奇怪,却也能按时交了房钱,店小二讲的兴致勃勃,却没发现西景昌在一旁也听得清清楚楚。西景昌当下起了疑心,在这家客栈中住了下来,果不其然找到一间奇怪的房间,听见里面虽有动静,却终日不见有人出来,想来八成何阳燧是住在这里了,当下就要敲门拜访,随即转念一想,先让他无故受些自己的恩惠,到那时再提出自己的想法,岂不半功倍?于是先瞧瞧住了下来,直到今日早晨,西景昌看见钱星簇出门,当下退了房一路跟随,这才有了集市上买马一事。
这几日钱,何二人一直藏在房里,闲聊间便将遇见那六人的事说了,现下西景昌突然发问,钱星簇被问得满脸通红,只道是自己冒用义弟之名骗了朋友的情谊,当下起身赔罪,表明自己是何阳燧的义兄钱星簇,而非其本人。
出现这等情况是西景昌事先没想到的,他听完微微一愕,低头沉思片刻,转而问道:“那何兄弟现下在哪里?”钱星簇道:“在客栈里等我。”西景昌回道:“那等咱们吃完了饭,去拜访一下他罢……” 话未说完,又细细思索起当日刘景和所说的话,刘景和平日碎言碎语,说起话来毫不避讳,将钱星簇杀母之仇也没落下一并说了,此时西景昌忽的记起,一想到钱星簇是何阳燧义兄,想来功夫肯定比义弟更好,母亲又是朝廷官员所害,定万分痛恨朝廷,若能收入麾下比其义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心生一计,道:“钱兄弟,你想不想报了家仇?”
钱星簇一听此话,立即愤然道:“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在下无一日不想手刃仇人。”西景昌听完心里踏实不少,道:“如今那扶熙品同其手下不日便要回到京城,到时候他身边高手如云,凭你一己之力又如何报仇?”钱星簇愕然,不知如何回答。西景昌见他心里犯难,当即起身拱手道:“若钱兄弟不嫌弃本门,大可同何兄弟一起投身我麖教门下,我麖教与朝廷不共戴天,定能帮助钱兄弟一臂之力,报了心中大仇。”钱星簇心下大喜,前几日兄弟二人还正愁如何报仇,如今有人肯相助,自是求之不得,当下连连应允,感激戴德。
西景昌微微一笑,从怀中又掏出一些银两交给钱星簇,让他回去劝何阳燧与自己一同投身麖教,待商量就好了到临澧城外那一处树林中。西景昌深谙与人相处之道,明白此事让他们兄弟二人私下商议最为合适,外人若中途插嘴,反而会让人起疑心,况且英雄本就不可强求,就算相劝不成,再不济也能落得个钱星簇,自己也就不与他一起回到客栈中,只在那片树林中静候消息。
西,钱二人在饭店门口分手,分道而去,钱星簇满心欢喜的牵了马回到客栈,将今日之事与何阳燧说了,又劝义弟与自己一同前往麖教,何阳燧当晚虽得那女子相助,却对那八字胡无甚好感,觉得他为人轻薄,不值得深交,当下皱了皱眉,道:“义兄大仇有望得报,义弟自然欣喜,只是改投其他门派,须得我师父同意,义兄与他无师徒之情,自然无妨。”说罢微一停顿,又道:“说来也有许久没见到师父他老人家,心里甚是想念,我还是回去看看吧,义兄在外,须得处处小心,莫让自己吃了亏。”
钱星簇一想这话也不错,当即两眼含泪,道:“义弟且先回去与道长作伴,待我报了大仇再与义弟相聚!”何阳燧点点头,也是眼泛星光,两人相拥而泣,洒泪惜别。临别前何阳燧想让义兄代为转交那姑娘的短剑,钱星簇看着那把短剑,也是心下暗夸一句,随即摆摆手笑道:“那姑娘让你亲手交换与她,肯定是有自己的用意了,我不方便掺和,你有时间还是自己交给她吧。”何阳燧不明白义兄这番话的意味,钱星簇心下明白那姑娘的用意,只道义弟太过天真不懂男女之情,也只笑笑不明说,让他兀自猜测去了。
到当日下午时分,两人在客栈门口分别,一南一北而去,何阳燧南下回道观陪伴师父,钱星簇则跟着西景昌一路北上,投身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