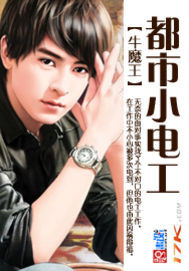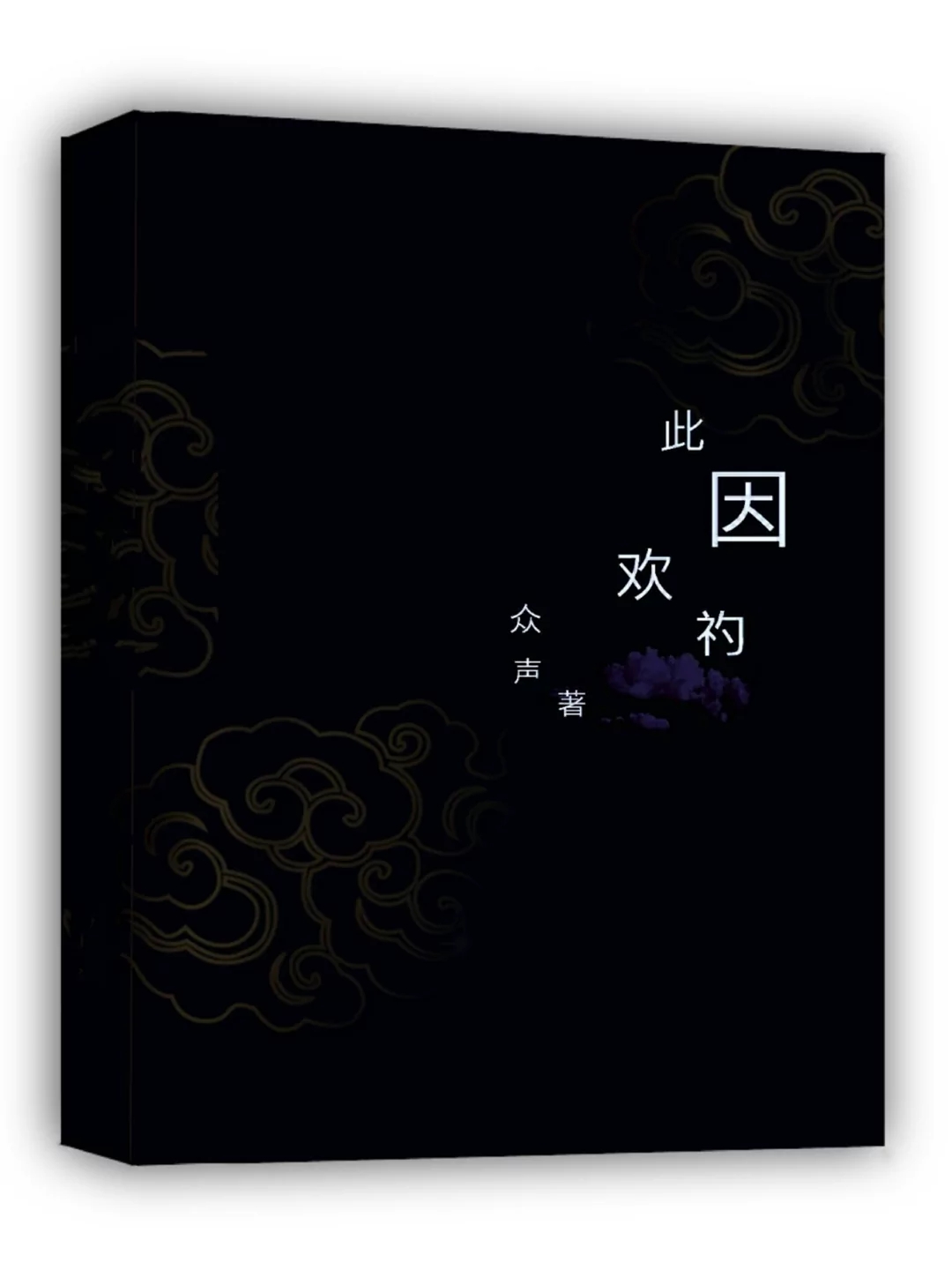夜幕降临了,四周都是漆黑的一片,顾双双晕眩了才找出了手机,可是又发现手机竟然已经关机了,早上出门没有充电。她的嘴角只留下了一抹苦涩,并不知道该去哪里,门外的蚊子很多,她一向讨厌蚊子,于是一直跺着脚,那些蚊子将她咬得到处都是包,痒痒的。该死的,她竟然不知道将钥匙丢到了哪里,现在的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缩头乌龟,头很痛,哪儿也不用想去,直想进屋去睡一个觉,可是又发现偏偏不能够。
隔了一会儿,她听到了车子引擎的声音。又有脚步声,踏得石板咯咯的响,是高跟鞋的声音,她以为是伍碧君来了,抬起了头,才发现不是。眼前的女子身材高挑,全身都透着一种高贵之气。但是,看上去,又觉得很眼熟,她绝对认识的。
“顾双双,你怎么还是和从前一个样子,丢三落四的。我还以为见鬼了,瞧瞧你现在的这个模样。”傅时歌出口就骂了几句,完全和她的高贵形象不符合。她从包里找出了钥匙,帮顾双双打开了门。顾双双看着她的一系列的动作,也不说什么。她的脑袋还是晕晕的,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被傅时歌拖了进去,丢在沙发上。顾双双条件反射的抓起旁边的被褥子盖在身上,实在是觉得有些冷。
“你怎么来了?”顾双双躺好以后,才慢吞吞地问。几年不见了,她真的差一点就认不出她来了。
傅时歌坐了下来,给了她一杯水,张牙舞爪的说:“说好了要缠你一辈子的,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放弃啊。别以为你逃到日本,我就没有法子了。现在还不是照样要回来。告诉你啊,别想甩掉我。”她话刚落音,手掌就已经落到了顾双双的脸上,虽然不是很用力,但是还是有一种疼痛的感觉。
“歌儿,你越来越暴力了。”顾双双扯开她的手,瞪着她。
傅时歌笑了一下,说:“论暴力,有人比得上你吗?我这几招,还不是你教的啊。”
“唔,师门不幸啊。”顾双双悲叹。
两人咯咯地笑起来。
顾双双有些发烧,吃了一些药,很快睡下了,等她睡了,傅时歌才缓缓地离开。她走到路口,发现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吉普车,便上去敲了一下门。里面的人似乎睡着了,根本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气愤地踢了一脚。车窗才缓缓地被摇下来,傅时欧冰块一样的脸出现在她的面前。
“怎么?谁惹着你了?”傅时欧看了过去。傅时歌不说话,从旁边绕开了,她打开自己的红色跑车的车门,呼啸而去。她开得很快,心中的怒气就是不能平复,渐渐的,她觉得自己已经不认识这个哥哥了。他暴戾,冷血,对身边的一切似乎都不关心。曾经被他视若珍宝的女人,现在对于他却是陌生人。
她想起发现顾双双的那一串钥匙的时候,它正乖乖地躺在垃圾桶里,她的钥匙扣还是和当年一样,桃木依旧挂在上面,只不过,那一个“双”字微微有些褪了色了。如果不是那一个字,傅时歌根本就不会知道那是顾双双的钥匙。毕竟七年都没有见过了,也七年没有人提起过了,在哥哥的面前,没有人敢提起这一个名字。以往的一切就像薄薄的烟雾,风一吹,就散了,什么也不剩,仿佛这一个女人从来都没有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她拿着钥匙去问他的时候,他冷冷的看着她,说:“不知道是谁的,留着干什么?”
她将钥匙紧紧地握着,手搁得很生痛,一个巴掌就要甩上去,他竟然跟自己说不记得了,不知道那是谁的东西。她知道,他是记得的,只是他已经变了,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哥哥了,从前,不惜一切代价他也会护着双双,后来一切与双双有关的事情他都会自动频闭,他已经硬生生地将她从心上割开了。
风很大,傅时歌将窗子也开得很大。头发丝在风中乱窜着,挡住了眼睛,她觉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忽然觉得自己被骗了。
高中的时候,她想,要是哥哥和双双都不能厮守,她就一辈子不谈恋爱。她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像他们那样,才是幸福的。
可是,不久以后,他们竟然分开了。她想不明白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也一直没有想明白。她将车速放慢了,身边的车子一辆又一辆的超过了她,她觉得自己正在渐渐地被吞噬。中途,她去酒吧喝了几杯酒,和那些老同学聊了几句,才慢悠悠地回大名。她停好了车子,见一人已经走了出来,见是陈叔,她叫了一声,正要进去。
陈叔忽然问:“傅小姐,傅先生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傅时歌回头,看着他,“有什么事?”
“老爷和太太已经到了,老爷正在书房发脾气呢,傅先生的那个宝贝墨砚都被老爷一气之下砸掉了。”陈叔叹着气,摇头。傅时欧的那个砚台从来都不让人碰,可是老爷子的脾气又急又硬,哪里管这些。
傅时歌问:“老爷子来了多久了?怎么不通知我们?”父亲的脾气她是知道的,每次过来总是免不了和哥哥吵上一架,谁也不会让谁。父亲急了还会摔东西,打人。小时候,她就见过他常常拿杖子打哥哥。哥哥不低头,他就往死里打,有时候好几天都下不了床。
“打了,可是傅先生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哪里会管老爷子来不来啊,就算他正好在家里,也是不会有好脸色的,别说他在外面了。估计今晚都不会回来了。”陈叔脸上的皱纹皱成一团,沟壑深深的,灯光下看得格外的清楚。
傅时歌说:“陈叔,你先别管这事,我跟他说一声,你去休息吧,老爷子那边有我呢。”她拿出手机来,可是他的电话哪里打得通,总是不在服务区的。她上了楼,看到站在窗前的父亲,他已经老了许多,这次回来,她直接来了大名,并没有绕道去看他,现在看着这背影竟然一下子觉得不认识了。
“爸,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她站在门口问。
傅正风回过头来,目光定在女儿的身上,声音幽冷地说:“怎么提前,不提前都见不到人了,提前,他还不躲到美国去!”硬生生的语言,让人无法辩驳。傅时歌低了低头,说不出话来,她都不知道父亲和哥哥现在的关系竟然僵成了这样。这种关系常常让人无法理解。
楼下突然有了动静,傅时歌突然听到陈叔的声音,“傅先生,你可回来了。老爷子正在楼上。”之后就没有了什么声音,连脚步声都听不到。傅正风背着手,表情阴冷,对傅时歌说:“去叫你哥过来。”
傅时歌刚要退出去,就见傅时欧正在走过来,他没有理她,越过她走进了书房,在沙发上坐下来,冷冷地问:“有什么事?”
傅正风幽冷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歌儿,你先下去,陪陪你妈妈。”
“哼,那个女人……”傅时欧冷笑了一声,狠狠地看傅时歌。又对傅正风说:“下次来见我,记得不要带闲杂人等过来,父亲大人,你知道我讨厌在这里见到别的女人。”
“你那是什么话!”傅正风大怒,“她是你的母亲!”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母亲?”傅时欧站了起来,“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母亲,不像您,您可以有两个妻子。”
傅时歌吃了一惊,来不及叫哥哥,父亲的手杖已经打了下来,一杖打在脸上,一杖打在背脊上,他根本就来不及躲,似乎也没有想过要躲。额头上的一道伤痕渗出了血丝,鲜艳的颜色,让傅时歌觉得很刺眼。“哥。”她拉住他的手臂。他却笑着甩开她的手,盈盈地看上父亲那张盛怒的脸:“您可别一直这样气着,气坏了身子,得不偿失。”
傅正风放下了手杖,板着一张脸说:“我要你从公司转两个亿出来,让时政去西面做西平广告的投资。”
“公司的股票刚刚抛出去,其他的资金也都砸在迎春的建设上,腾不出来。”傅时欧淡淡地望着父亲。现在公司的财政大权已经基本掌握在他的手上,他并不畏惧眼前的这个男人。别说挤不出钱来,就是拿得出来,他也不会交出一分钱。他巴不得傅时政跌倒了就再也起不来。
“那就从你自己的账上转!”傅正风说,“我不信你连区区两个亿都拿不出来。”
傅时欧看着地上的砚台的碎片,缓缓地说:“如果您真要我转,也不是没有办法。”他顿了一下,“其实很简单,伊顿的地盘归我,什么都好说。”
“好嚣张的口气!”傅正风大喝一声,儿子咄咄逼人的口气,让他怒不可遏。这个儿子从来就不听他的话,常常他会有一种冲动,就是一掌打死他。
“据我所知,你手里的资金都是冻结的吧,至少近两年是提不出来的吧?”傅时欧干笑了一声,若是他手里有流动的资金,他才不会来找自己。他死咬着不放,就不怕他不妥协。他倒要看看是那个儿子重要,还是伊顿重要。
傅正风气得拂袖而去,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儿子的心肠这么硬,没有了伊顿,不是将他往死路上逼吗?可是,傅时欧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这性子像极了他,令人懊恼。
等傅正风走远了,傅时歌缓缓开口:“哥,父亲的身体也不太好,你就不要再这样和他扛着呢,都是一家人,这又是何必?”
“歌儿!”傅时欧打断她,“你不懂,就像你会叫那个女人母亲一样,而我,永远也不会。”他不是狠吗?偏偏,他要比他更绝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