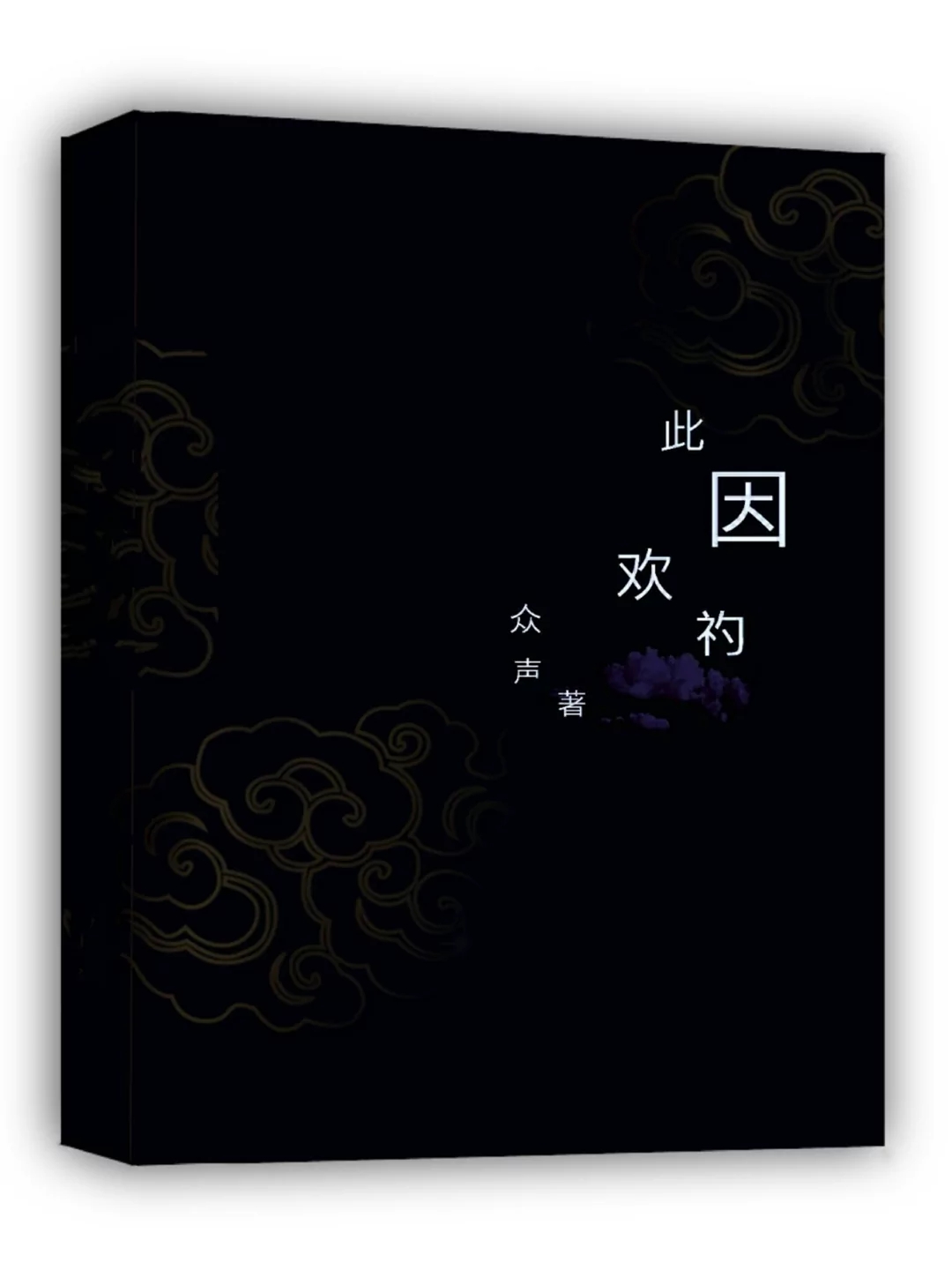巍峨耸立的山峰横在青龙窟前,两人跋山涉水多日,再越过这座山,就能直奔青龙窟。古往今来肖想圣器的人不在少数,但真正能越过这座山的人却不多。世人皆以为青龙窟是最为险恶之地,却忽略了青龙山也是一道艰险的屏障,抢夺圣器是人大多是还没进青龙窟一睹真容,就或逃命、或丧命在了青龙山。
远看这山绵延高耸,层层叠叠的雾气弥漫山腰,朦胧危险,近看则是来到山脚下,抬头仰望时难以穷极山峰。问觞将大聪留在山脚下,与风泽杳徒步上山。
越往深处走,能见度越低。走到半山腰已是白茫茫一片,问觞已经看不清风泽杳的身形了。风泽杳从怀里掏出一根细绳,一头将问觞的手腕捆住,一头牵在自己手上。雾气朦胧,问觞只知道自己捆了一边的绳,不知道风泽杳是牵着那边绳的,乐呵呵道:“这个法子好。”
风泽杳道:“嗯。”
若是叫她知道自己牵着绳儿,定是要骂上一顿。
问觞丝毫不觉:“我说话你要应声,不然万一走散了我也察觉不了。”
风泽杳紧了紧绳:“好。”
问觞感到手腕上的细绳被拉得更紧了,好像这绳子一牵,她心里安定多了。
两人互相拉扯着往上走着,越走雾气越浓,霜华越重。按理说这个季节根本不该如此寒凉,可周遭的气温已经如同寒冬。一阵又一阵的寒风呼啸而来,问觞手脚已经冻得发麻,竟还笑叹了一句:“真实在,该不会这青龙山的绝技就是冻人吧。”
风泽杳撑起胳膊,一阵寒风吹来,宽大的袖摆鼓鼓地挡在问觞跟前,风泽杳把她拉近了些:“不止。”
四处皆是白雾,两人迷失了方向,晕头转向得不知该往何处走。问觞蹲下摸索到一根树枝,拾起来用来探路。周遭寂寥,唯有呼呼的北风咆哮充斥着耳膜,她冻得手麻脚麻,探了好一会儿路才感到手腕上的绳松弛了下来,当即心里一凉,试探地喊了声:“风泽杳?”
身旁传来一个低沉又清冷的嗓音:“我在。”
问觞松了口气:“这绳子松了,我以为走散了。”
风泽杳道:“不会。”
问觞感到绳子又绷直了,那一头被紧紧牵着,风泽杳道:“怕把你勒疼了,就松了些。”
问觞吸了吸鼻子,感动道:“没关系,你走近一点,安全些。”
“好。”
问觞还没反应过来,身旁的人就挨了过来,一把把她圈进了怀里,轻声在她耳边道:“你身子怎么这般凉。”
问觞全身冰凉,身形瑟瑟。非常时机,他怀抱又那么温暖,为了不让自己还没到青龙窟就半路冻死,她就顺从地接受了这份温度。开口时鼻音颤颤,已然是冻得不轻:“这个气候,不凉才怪。我们现在往哪儿走?”
身前那人低下头,温热的鼻息在她敏感的耳畔游走,嗓音蛊惑动人:“……不走了。”
问觞头皮发麻,想推开他:“不走等死么?”
风泽杳不容她逃避,贴身上来将她狠狠拥紧,一只手掀下她黑袍帽檐,一只手勒住她的腰身,低头将脸埋在了她脖颈间,低低道:“不走……我想要你,我要你在我身边。”
他的唇齿在她裸露的脖颈间游走,问觞惊觉不妙时,意识已经开始模糊。她被他勒得透不过气,拼命想推开他,可身体被狠狠压制,一点力都使不出来。熟悉的困意猛烈地袭来,她双眼不堪重负,沉沉地倒在眼前人的怀中。
方才俊美无双的男人转瞬间化作一团黑气,将问觞包裹其中。随即传来一阵阵凄厉的笑声,乐此不疲地回荡山间。
问觞再睁眼时,是在一个茫茫雪天。
她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时间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隐隐约约记得自己刚刚好像是在山上。在山上……在山上做什么呢?
她懵懵懂懂地望着四周。白雪皑皑,万径人踪灭,偶尔有一只鸟儿在光秃秃的枝头扑棱一下,连个能问路的人都没有。她低头发现自己手里提着两壶烧酒,好像被什么支配了一样,本能地朝一个方向走去。
穿过了街巷,穿过了枝桠,穿过了木门,掀开屏障一看,一个俊美如画的男人懒卧榻上,眉眼生笑地看着她。
男人慵懒而温柔,只是脸色过于苍白,像是久病未愈。她听他温柔地唤她:“南渊,过来。”
她稀里糊涂地就提着酒过去了。
不仅过去了,她还自己开口道:“大夫都说了你现在不能喝酒,拗不过你,喏。”她扬了扬手中的烧酒,“只许你喝一口。”
“好。”男人温柔地笑了,缓缓伸出苍白修长的手将她发丝的新雪拂去,“下雪了。出去一趟可冻着了?”
问觞顺着这具身体的主人答道:“为你这一口酒,跑趟长白山都不在话下。”
男人将她拥入怀中,她靠在他坚硬又单薄的胸膛上,听着他炽热的心跳,看着窗外的雪景,觉得岁月安好,盛世无双。
她轻轻开口道:“过两天就是年三十了。阿杳,这年复一年的,过得可真快。”
风泽杳将下巴搁在她的头上,轻轻抚着她微湿的发丝。
“你身体太虚弱,不然我们能在屋外小亭里烧个火炉边看雪边吃酒。不过无妨,从窗户里看也一样。”她起身,移了个小桌来,跪在榻边热酒,“说好了,只许喝一小口。”
窗外万千风景,皆浓缩于窗上尺幅之间。
小屋里了了人气,微微星火,便成人间。
问觞没来由地心痛起来。
年三十那晚,她借着窗外透进的微烁星光仔细地注视着男人温润的睡颜,熟练又虔诚地在他的唇上轻轻烙下一吻。
阿杳,烧酒太烈,饮酒入肠的时候满心热烈,可终究是伤人的。
我不要胆战心惊地活着,我要与你安安稳稳,要与这世间的魑魅魍魉做个了断。
她背负一身的月光与仇恨,那一夜策马驶向远方。
问觞抹了把脸,没抹到眼泪。
她心想这好像是从前的江南渊,又好像不是。
脑子乱作一团。
不知不觉的已经分不清现实和幻想,她能真实地感受到与自己共用一个身体的人的喜怒哀乐,她悲伤,眷恋,不甘,绝望……她与她一同拉着缰绳驾着马儿奔驰,与她一同感受深夜呼啸而过的烈风,与她一同披荆斩棘,在杀局中千回百转……她成了她。
多少个日日夜夜后,问觞满身伤痕地坐在深夜的篝火旁,一壶烈酒穿肠肚,烧得人四遭冒火。霜露重的季节,天上的云像拨不开的黑布笼罩在穹苍之上,月黑风高的夜里,她一人一火一酒壶,却拥抱了满腔的热忱。
魔火被她亲手摧毁,她虽也受了严重的伤,但好在从小摸爬滚打,四处行义,受过的伤已将她层层包裹成一个不会觉得痛的人。她亲手斩杀魔火,将他的魂魄撕得稀碎,没有给他再次造乱的任何可能。天下人对她感恩戴德,将她供奉为神,为她开窟立像,修建庙宇。她承受万民朝拜,万流景仰,溢美之词在在她耳旁充斥数日,皆是子民的狂欢。
那日她回到观苍山时,师父与师叔师伯们喝得醉醺醺的,一见到她就笑呵呵道:“好孩子,真是好孩子!嗝!”
问觞扶住他,小心地问道:“师父,我想带阿杳回来看看,可以吗?”
“行,行!”师父举着酒壶,含糊不清道,“赖着不走都行!”
她一高兴,酒宴都没来得及参加,跋山涉水地朝临淮城出发。心里有一团热烈要撑破胸膛破土而出,她思之如狂的那张面容日日夜夜折磨着她,她想念极了那汪浅淡温柔的紫色,想念极了那人温柔坚实的胸膛。
那日夜里的不辞而别还是让她在门前胆怯滞步,她不确定他还在不在,不确定他是否能原谅她。他们曾经说好要一起面对,可她还是一意孤行地失了约。
一路上的热情与期待在离家一步之遥的地方慢慢被消耗,她颤抖着手缓缓推开了木门。
养在院落里的树木花草还如当初一般鲜艳,门旁的扫帚也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石桌石凳一点灰也没落,一看就是有人时常照料花草,清理桌椅。
问觞心里有团火被重新点燃了起来。
她拂开眼前的垂下的柳叶,看到一个穿着懒散黑袍的男人正提着小壶给花儿浇水,步子迈得悠闲惬意,转过头来的时候眉目一如既往得柔情似水。
她屏息,见眼前这个俊美绝尘的男子朝她缓缓伸出了手,嗓音温柔蛊人:“南渊。”
她着了魔一般走过去。男人将她轻轻拥入怀里,下巴摩挲着她的头发,低声道:“瘦了。”
问觞伸手抱住他,摸到他背上的坚硬挺拔的脊骨,顺毛一般地摸了两下:“你不生气?”
风泽杳道:“生气。但看到你之后,那些狠话一点都说不出口了。”
问觞埋在他怀里,闷闷地笑了好一阵,道:“我回来以前去了一趟观苍山,师父允许我们回去了。”
“好,”风泽杳道,“等你休养几日,我们就回去好好拜访他老人家。”
问觞点点头,静静地靠着他好一会儿,突然喃喃自语道:“好像……好像还有一件事。”
风泽杳问道:“何事?”
问觞苦恼道:“不知。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我忘了。我忘了……忘了……”一阵剧烈地头疼袭来,她痛苦地捂住了脑袋,缓缓地蜷缩下来。
她这一路上经历了太多,太多她记不清的事,可就偏偏这一件,她觉得是至关重要的,是不能忘的。可是她叮嘱自己千遍百遍的事如今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她感到头痛欲裂,胸闷难挡,一口腥甜硬生生卡在嗓子里。
风泽杳焦急地蹲下身来,努力安抚着她:“忘了就不要想了,南渊,不要想了。”
有些记忆懵懵懂懂地就被遗忘了。她和风泽杳回到观苍山,回到旭华峰,见过了师父,兑现了要陪他喝观苍山最烈的酒的诺言,将她不眠峰的东西搬了个七七八八到听雨峰,时常这儿住几天,那儿再逍遥几时,日子过得潇洒恣意,极尽安乐。
渐渐地,她好像真的忘了那个要做的重要的事。
风泽杳踽踽独行在青龙山的迷雾之中,牵了半天的绳儿都没听见问觞说话,拉扯线绳的时候才猛然惊觉与她走散了。
眼前白茫茫的雾里突然出现一股浓烈的黑色气旋,一个眨眼间就势不可挡地朝他狂啸而来。风泽杳拔剑抵御,转瞬间几道剑波就如横劈的刀刃一般朝黑气冲去。两者势均力敌,寸步不让,一时间叫人分不清究竟是黑色压制了金波,还是金波吞噬了黑气。风泽杳脚尖借力,箭步朝黑色巨剑狠狠劈去。
一团的黑气被他从中劈开,他隐隐约约看到问觞双眸紧闭半卧黑气之间,急忙大喊一声:“南渊!”
问觞不应,而汩汩黑气倾泻而出,怒吼着幻化成一只面目可憎的黑龙直朝他径直冲来!
风泽杳蹙紧了眉,已没有耐心与它纠缠。握紧了手中的剑,转眼间就舞了三十六式,与黑龙激烈相斗起来!黑龙由气而化,劈不死,斩不灭,风泽杳提剑半空直下,一剑从龙头劈到龙尾,干净利落,杀意十足。黑龙嘶吼一声,被齐齐割裂的身体化雾竟又重新拼接起来!
龙啸爆发,整个青龙山为之一颤。风泽杳丝毫不惧,反掌结印,一跃而起直击黑龙面门!
黑龙甩尾想将这个狂妄的人类拍飞,风泽杳却直接抱住龙头,一声怒喝之下,硬生生将一整条黑龙甩飞出去!
他不常动手,一旦动起手来,一定是拼命狠绝的。
半空中的黑龙猝不及防,没料到敌手的实力竟远在它之上,风泽杳不给它反应的时间,借助虚空之气飞跃而上,收剑入鞘,一拳狠狠砸在龙头上,黑龙席卷着狂风被狠狠拍回地上,整个青龙山灰尘弥漫,大抖三抖!
黑龙不可置信地瘫倒在地,近乎畏惧地瞧着眼前深不可测的紫眸男人。它守护青龙山数百年,不是没有遇见过强手,但打得这么狠、这么猛的还是第一次见。
风泽杳踏步而来,一把抓住龙须,怒喝道:“人呢!?”
黑龙缩了缩,委委屈屈地化了黑气,问觞被团团黑气簇拥着送到他的面前。风泽杳伸手接住,看她沉沉昏睡,黑袍半敞,白嫩的脖颈间竟有泛红的咬痕。
黑龙见他的面容猛得冷鸷下来,禁不住打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哆嗦。
“这是怎么了?”风泽杳缓缓开口,嗓音冷得吓人。
黑龙在他身边来回逡巡,用尾巴在空中拟了一个阵。
迷雾阵。
此阵法并不难实施,威力只看施咒者的法力强弱。迷雾阵是一种让入阵者沉迷幻境的阵法,在幻境里他们可以看到此生最美妙的东西,可以填补所有的遗憾,可以过最想过的生活。这阵法只有入阵者自己可以破,若是外力强行干预,双方都会陷入其中无法逃离。然而,大部分人是沉迷其中不愿醒来的,他们迷失心智,把幻境当成了现实,享受幻境,沉浸美好,早已不贪恋现实人世。
风泽杳低头低声又急促地呼唤道:“南渊!醒醒!”
问觞眼皮都不动一下,睡得沉极了。
风泽杳紧抿着唇,双指覆上她眉间。一到白光闪烁,风泽杳在闭眼前凭空握了一把黑气。黑龙绝望地呼啸一声,被一齐带入了幻觉。
落点处就是问觞梦境所在处。此时一人一龙在仙气缥缈,灵气充沛的一座灵山上落脚,眼前是一片茂密的树林。风泽杳微微一怔,觉得场景分外熟悉,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最高处耸立着“旭华峰”三字。
没想到竟回到了观苍山。
他携黑龙一起往前方茂密的丛林里探去。从问觞的梦境里进去,那么落脚点一定是梦主的所在地,风泽杳顺着指引往前寻找,不多时就在一片丰盛的草药地里看见一个素色身影。
这个身影背对着他,脚边搁了一只竹筐,正蹲在地里自行辨别着药材。头顶上是入云的葱翠,此刻阳光正通过这层层叠叠的遮蔽稀碎地散落在她的身上、乌黑的发丝上。此番静谧安宁,任谁看了都不忍打扰。
风泽杳踩着落在地上干枯了的树叶,缓步朝她走进。
女子的筐里已经装了近乎半框的药材,她低头拿了把小铲正割着一株八青草的茎。八青草不好采摘,用手揪不出,用铲又容易飞汁,女子染了一手的绿液,终于如释重负地把八青草扔进了竹筐。她提起竹筐,正转身往另一片药地里走,转头就看见风泽杳站在离她堪堪几尺远处。
身形修长的男人一席黑衣,脚蹬黑靴,腰间以血红腰带系一垂穗,别了一把通体雪亮的银剑。再往上瞧,那面容自然是一等一的好,只说个面胜美玉,姿色无双,怕是远远不够的。他一双特别的紫眸认真地注视着他,见她回望,神色微微一动。
女子回眸笑道:“阿杳,今日怎么穿成这样?”
风泽杳一愣。
他张了张嘴,半晌道:“你唤我什么?”
“阿杳啊。”女子道,“回观苍山这么久,还第一次见你穿成这样。怎么,是道袍穿腻了吗?”女子提着竹筐款款走到她身边,风泽杳想伸手接筐,女子却避开了,“你身子不好,不是说了不让你来吗?”
风泽杳不知何意,但只好顺从道:“我已经好多了。你要去哪儿?”
女子牵起他的手,朝林外走去:“回听雨峰吧。你好好歇着,我给你熬药。”
她的手温温软软,凉凉地贴上来的时候,他几乎是猛地一颤,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坍塌了。
风泽杳嗓音微颤:“南渊。”
江南渊转头,见他眉头紧锁,伸手轻轻抚平他眉间的紧迫,温声道:“怎么?”
风泽杳半晌没说话,只静静地看着她。江南渊抬头望着他紫色如漩涡搬迷人的双眼,像是一潭千尺深泉,将她紧紧缠绕进其中。渐渐的,她心里没来由得觉得不对劲,觉得他的眼神竟带上了攻击性,说不上来是认真,还是锐利。
江南渊缓缓松开了手,无措道:“你怎么这副神情?”
风泽杳注视着她,唇齿间缓缓吐出两个字:“问觞。”
女子猛地撒了手,一筐的草药撒了一地,她往后退了几步,瞳孔里满是惊慌。
风泽杳道:“你不要害怕。你仔细想一想,你是谁,你身在哪里,你该在哪里?”
女子恐惧地望着他,风泽杳不知自己为何会有这么吓人,便顺着她看往的方向朝自己身后看了一眼。身后早已不是仙气缭绕的各大灵峰,而是一团打开的空间,里面充溢着满天的黑气,狂狂地呼啸着。
风泽杳知道,这是梦境与现实的交点。只要她朝前一步,进了黑气深渊,他们就能得救。
若她不进,这看似桃源的仙境,实则就是深渊。
江南渊往后退着,咬着牙道:“你不是阿杳。”
风泽杳站在黑气前,没动:“我是。也许你看到的那个,才是假的。”他顿了一顿,后面两个字吐得格外清楚,“你好好想清楚,究竟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觉。你告诉我,你想去哪里,问觞?”
听到这个名字,江南渊痛苦地捂住了头,挣扎着蹲下缩成一团。
风泽杳缓缓朝她走进。一步、两步,她听得格外真切,她能感受到这个男人朝她走进的身影,能感受到他腰间鲜红穗子随他走路的一起一伏。他停在她面前,朝她伸出一只手。
江南渊露出一双眼,抬头看了一眼,除此之外没有回应。
风泽杳也不急,只伸出一只手,久久地立在她面前。
这意思无非就是,我可以等你,等你想好。什么时候想好都可以来牵我的手,什么时候都不算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