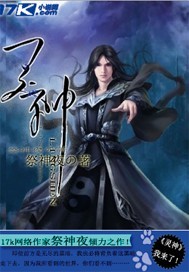终于知道了答案
我没有为谁祝福
我只把自己锁在沉默里
没关系,生活依旧美好
只是这美好需要不断地忘掉过去
因为我已经认识了你整整七个星期零四十八小时
[1]
心惶惶,充满了矛盾、困惑、不安,和隐隐的抗拒。
安欣仍然时时陷在往日的伤痛里。那个人的影子挥之不去。那次初恋,带来的创伤如此深刻。
安欣对他确实心存感动,不过他不算是男朋友,只是非常要好、很聊得来罢了,安欣想。
这让她心有不安。她觉得柯博智是个相当天真和憨厚的人,我不能让他糊里糊涂地喜欢我,对我的“过去”还茫然不知。总有一天,我会详详细细的把我的故事,一五一十的全讲给他听。
[2]
柯博智又要了一杯酒,夜色更深,可城市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是个广告人。
我喜欢自己的工作,这不是薪水的问题。这个行业里充满了危险的竞争,它的创始人曾经让我嫉妒得日夜不眠。有时候我觉得比尔盖茨绝对是个奇迹,有时觉得他像我一样普通而触手可及。
卜铭兴奋地和他干杯。
“今天刚把一个客户逼疯,丫敢拖月费,这两天每隔半小时响他电话一次,快下班前他终于疯了——我已经叫人办了,你至于打这么多电话么。”
“呵~”两个人肩膀抖动着,窃窃私语。哈哈!你看锐思的广告或许还会有感觉吧?至少当时我们找回了广告的尊严——在污秽的地产广告里。
卜铭说的是锐思国际广告。一年前,俩个人同在那家公司,有不少女孩。她们主要做客户服务、策划、市场调研方面的事情。他们一有时间就谈女孩,女孩们一有时间就谈他们。
卜铭喊服务生要一小瓶香槟,然后转向柯博智说:“那会儿你已经不在公司了,那帮业务员午休时喜欢吃着盒饭谈论客户部新来的年轻女孩。”他倾过身子,压低声音说,“实际上,孙妍刚来时不在客户部,只是个前台,那阵子成天中午有人排着队请她吃饭……”
“就那么传奇?”柯博智半信半疑,心里想像着那个冷静优雅的Officelady横眉冷对千夫所向的样子,以前有好几次听卜铭说起过,实际上并不见得如何,这类传闻大多不可信以为真。
“你觉得怎样?她那时可真是惊人的风光呦,”卜铭说,“大家全都盯住不放,但还没人能泡上。”
“说不清,她身上有一种撩人的劲儿,有点儿傲,呃,我是说眼神儿,尤其是看人的时候,不过也许她自己一直没意识到。”
“哈哈哈,已经有不止一个客户这么跟我说了。不过,她那股劲儿还挺管用的,对客户就要居高临下一点,那些男人吃这个。我把她哄过来当客户经理算是用对人了,下一步死活要把她哄到手。”卜铭道。
“那……这么说,你多少在利用你的职权?”
“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并没什么错儿,况且她名校毕业,办起事来又干脆利落。”
柯博智沉思地凝视他:“权势是一种**。”
色戒里的话,是书里面的,电影里没有。
卜铭不看电影,更没时间看闲书。他的时间也更合理有效地分配给了谈判,应酬,翻阅公司的财务报表,和适当的体育锻炼。
柯博智透过酒杯的边缘审视对方。他的确很有魅力。宽肩,长腿,肌肉线条分明而不显粗蛮,永远只穿漂亮的灰色西装,长长的腰线。他脑子里一定是带了套刻度精准的自鸣钟,当初来到这世上时就上紧了发条,只要颤动游丝,指针便会及时地指向目标。
永远一丝不苟,不带半点纰漏,一架高智能的机器。
他太刻板,不属于年轻女孩一见钟情那种类型。
“想单靠耍嘴皮子打动那个档次的美人,的确大不容易。她知道男人们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将那份魅力当作自己的荣耀,因此充满了自信。”柯博智哧地勾开一听可乐,深灌了一口,随后把拉环当作戒指套在自己小指上,展示给卜铭看:
“不过,一颗钻石就可以让女人改变立场……,”柯博智戏谑地说,尽管是句玩笑话,可他多少有点儿相信钻石的魔力。“而她们最终只糟泱在这上面……,”感情永远战胜不了理性。他又补充道。
香槟酒到了,服务生撬开瓶口,将金色的液体注满他们的杯子。
“祝你好运气。”柯博智将套在手上的拉环丢回烟灰缸中,然后举杯。
他们啜着杯中酒,陷入沉思。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安欣弹钢琴的情景,那段舒缓的旋律浮动在厚重的乌云下,一层又一层地压在心上。那是他第一次透过安欣恬静如水的外表,窥探到她的内心。
[3]
在以后的五天中,朗智广告的人围着柯博智和卜铭团团转。他们仔细研究每天的市场简报,只有在这些时候,柯博智才能短暂忘记内心泛起的躁动。夜间,当创意部所有的人都离开后,他仍捕抓着四周时刻萦绕的声音。
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然而在他的脑海中,安欣却在**:“哦,啵一个,哦,天呀,我受不了啦……太好啦……哦,哦……”接下来便是长长而颤栗的叹息。
尽管从本能上他应该非常排斥这样的想法,但在他和安欣的故事中,还有一个又苍白又空洞的背景——那个叫A6的男人。虽然在视线中只是一个凝重而模糊的影像,却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枷锁。
然后,静寂象柔软的丝绒布一样降临四周,紧紧包围住他。
郭子不了解安欣,他想。安欣本身并不是一个世俗的女孩,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也许那个人在她渴望温暖的时候,确实给了她理解与关爱。
那个人究竟什么样子?
[4]
“你想看吗?要是想看就给你看……”
从那个见到流星的夜晚之后,大约经过了一个半月左右,柯博智看到了他们两人的照片。
那张照片从日记本里落出来,他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那是一张靠在那个男人肩膀上的照片,背景是长城。照片里的安欣明眸皓齿,笑得露出两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纯纯的样儿;男的是个头上光秃的胖男人,下垂的眼睑,那张嘴——鳗鱼般的嘴……
她说A6着迷一样地喜欢野营。他们认识的第二年,就一起去了黄花岭长城,他们站在高岗上,遍地都是野花。
然而柯博智却听到了另外一些声音。连微笑都上档次!——那个侧目而视的表情和微微下垂的嘴角。
他隐约感觉到那些声音在说什么,他在自己的记忆范畴内迅速搜寻捕捉着那些影像。然后,突然的,那个念头像是一道闪电一样,他被击中了。
一切都清晰可鉴,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
“什么?”
他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惊讶到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
“他眼睛挺像你,说话时眨个没完。”安欣指着照片对柯博智说。他的眼睛红了起来。安欣转过身,张开被自己捏得发白的手指,在空中犹豫了一下放在他心口上揉搓着,对他说:“你别生气,他来我们学校讲过课,他是……”
“他叫张维!”柯博智吐出这几个字后感到快窒息了,他不敢再看见什么,从齿缝中又蹦出两个字:“对吗?”
安欣烫手一般甩掉那照片,然后用圆溜溜的眼睛望着他,嘴唇一点血色也没有——像是见了鬼一样的表情。
这是个阴雨连绵的下午。
[5]
生活中的某些角落里永远隐藏着一种叫做悲伤的蛇,它们会在你心门外开满鲜花的时候,或者在你刚刚体味到一点芳香与甜蜜的当口,从阴霾间游动出来缠上你的脚踝,然后任由悲伤的毒液侵蚀至血管,刺痛感蔓延到心扉。
那些悲伤漫过脸颊,化成莫名的恼怒,在那里迅速膨胀至头顶,然后将所有记忆的片断,所有情绪与情感铸就的壁垒……全部融化。消逝掉了,化成脑海中一片苍凉的空白。
那个人大剌剌地坐在那里,脸上挂着堪称无耻的微笑,原来自己每次见安欣时的刻意拘谨和精心修饰竟如此的不重要。
说老实话,柯博智所接触的人里,不乏英俊优秀的中年男人,与那些帅酷的年青人不同,那是一些成熟而稳健的生命。
对,是生命!像孔雀的尾羽与雄狮的头颅一般,只有在最成年的时候才绽放出近乎完美的姿态。时间在他们身畔会像清水流过光滑的石板一样划过,却没有留下斑驳的投影;他们也仿佛脱离了时间的界限,像是在水里泡了几千年的铜罐的表面一样,映出岁月积淀出的厚重。这种魅力是不能用年龄来区分的,也是那些一味帅酷的男孩子所望尘莫及的。
在柯博智心底里,曾经不止一次好奇地想像过那个让安欣舍得付出青春与美好的人的模样,至少也应该像是他们中的一个吧?
可那个人是什么人,那个秃头的男人,哪里配接受一个纯洁女孩的微笑!
其实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无论哪一个都无关紧要,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都永远无法改变。
但,符合逻辑的结果至少可以让心里好过一些吧。
[6]
一个女孩如果肯倾诉一切的话,只有两种可能:说明她已经很在乎对方了,不然就是觉得有所亏欠。
那么安欣会属于哪一种?或是两者兼备。
但是有所亏欠的爱情还是爱情吗?
没法回答,也不愿回答。他心里唯一知道的答案就是自己舍不开安欣了,而安欣此时正在向他道明一切。
在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点虚伪和一丝谎言,她说了她的童年,说了她的父母,说了她单纯经历中的快乐与坎坷。说了追她的男孩,说了她的处世哲学。
“……从小我爸妈就借账过日子,你家条件那么好,你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你当然不明白欠人家钱是什么感觉。我上大学的钱都是家里借的,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觉得背着一身的债,我学习成绩是班里最好的,但我在好朋友面前还是抬不起头来,我爸妈能借钱让我上大学,但没让我有一点儿可骄傲的地方。
那个时候只有张维能懂我,我,……我没把他当有钱人,但我羡慕他能挣到钱,我也不在乎他有老婆,根本不想天长地久的事。我只在乎眼前,其他的,我都不愿多想。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就想有一天能让我爸妈过上好日子……”
她说得语无伦次,说到的一切都像是真的,她给柯博智的感觉与郭子形容的之间似乎有某种难以逾越的距离,某种无法统一的矛盾。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柯博智靠在空荡教室的墙壁上,他握着安欣的手发呆。安欣偶尔抬起手,用手扫去脸上的泪迹。窗子底下樱花树开得正艳,外面是灰蒙蒙的天空。风把半开的窗扇吹得砰砰作响,她的头发湿湿的乱贴在脸上。在那里她站了好久,犹豫了很久,终于紧张地把后面的事一件一件说出来给他听:
——“我们跟别人合租了一套房子,有时候一个星期去两次。”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每次放假的时候都不能陪我……”
——“每个月他给我一千块钱生活费……”安欣说得可怜巴巴,完全是一个不知所惜的孩子,那声调几乎是在企求了。
柯博智一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连自己喜欢的女孩也把自己的身体卖给了男人。
在她周围除了有很多意料之外,很多事情己经不会感到惊讶了。
不过,他还是吓了一跳。并不是因为她的过去。
而是因为她唐突的告白。
这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滋味,交错伴随的冲动。这时他从心里看到——那个男人正小心翼翼地把几张大钞票塞进安欣的手里。
这一瞬间,你怎么会没有叫起来,没有给他一个耳光呢?!——你,你从学生时代起就爱他了,为了他撒谎骗你的妈妈说学校值勤,说幼儿园每星期要值夜班,可他爱你吗?他干嘛不为了你去跟他老婆离婚?闹个家庭破裂,身败名裂!他只付给你钱,为了那些个夜!在他的心目中你是一个**,只不过如此而已——他就付钱给你!
你付出了纯洁与美好,这还不够,你还得受**!
对了,我忘了,他是个有钱人呀!呵呵~如果他给你跑车、豪宅……起码他还像个人。一千块钱一个月,连一个**也不会接受这么便宜的价钱!
因为,因为你是学生,因为你单纯得要死。
他想喊出来,想骂无耻的脏话,最下贱的话;就算他如何过分也比那个人好一万倍,可他没有,那些刀剑梭标一样的话只能留存在心里。
但他迅速收拾着东西。他要离去,马上离去。
安欣手足无措地看着对面的柯博智。他的心底灌了铅。他去拿帽子,帽子就搁在窗台上。他像酒醉的人一样趔趄了一下,只看见天外的白光。那株美丽的水生植物连同玻璃樽落向地面,他伸手抹了又抹,觉得粘得发腻。
双手紧握成拳头,掌指间是不断沁出的黏稠的血。
[7]
满地的湿滑和玻璃碎片。闪着湿漉漉的亮光,一片狼籍。
她抬起头,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安欣站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去,跪在地上,一小片一小片地捡拾着那些残片。她图劳地拼接它们,还原那些曾经的美好。一缕嫣红的颜色突兀地划在玻璃的锋刃边缘,几分钟前还流淌在肌体里的热度,融化在泥泞的水里,在地板上,却像化进了她的心里。
她不肯哭,可是泪自己往下流。
这是就我该受的惩罚么?
在这摇动着的巨大的白色苍穹底下,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两个的孩子在奔跑。清白的光线从云顶深处刺出来,随着风把他们嬉闹的声音传播得很远。
在更远的苔石背面,那只美丽的蝴蝶刚刚蜕变出蝶蛹,它发奋地生长着,四周满眼青翠。它破茧而出,那里被蛀出了黑洞;像待放的花朵般,它伸展开翅膀,可折断了的茎脉又重新垂下来。如今它躺在水里,仿佛一下子被夺去了生命,没有一点儿生气。
难以挽回,她自己心里清楚。
近处的远处的一切都安静下去。
头顶上的窗外散落下一两点零星的寒气,在手掌上化成了细细水珠。
是雪花。
十二月的北京会下雪么,为了她曾经丢失的美好?
[8]
几天后的一个正午,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为了与人商量工作上的事宜,柯博智约客户在一家咖啡店里。因为离邀约还有一段时间,他就到店内的杂志架子上拿出一本刚刚新鲜出炉的《时尚》杂志,随意地翻阅着。一张照片突然映入他的视野。那是一张在镁光灯下剪彩的新闻照片。
柯博智的头嗡的一声。在当作题图的彩色照片下,有一段非常详尽的文字说明。图说写着:华亿集团正式进军高端流行娱乐与资讯领域,其麾下的华星文化是一家最尖端、时尚人士聚集的多媒体实业,开幕酒会在上海举行,华亿总裁张维到场出任嘉宾。
看着这张照片,看着洋溢在那张脸上的上档次的微笑,眼前晃动着安欣和那个论年纪能做她父亲的男人在床上蠕动的镜头,他心中充满了痛苦,而这痛苦又逐渐变为愤怒。
这个陌生的男人,一辈子不相干的人,却毁了她,他把她毁掉,让他们的幸福也泡汤了。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那是一场梦。这张照片才是现实。
柯博智猛地合上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