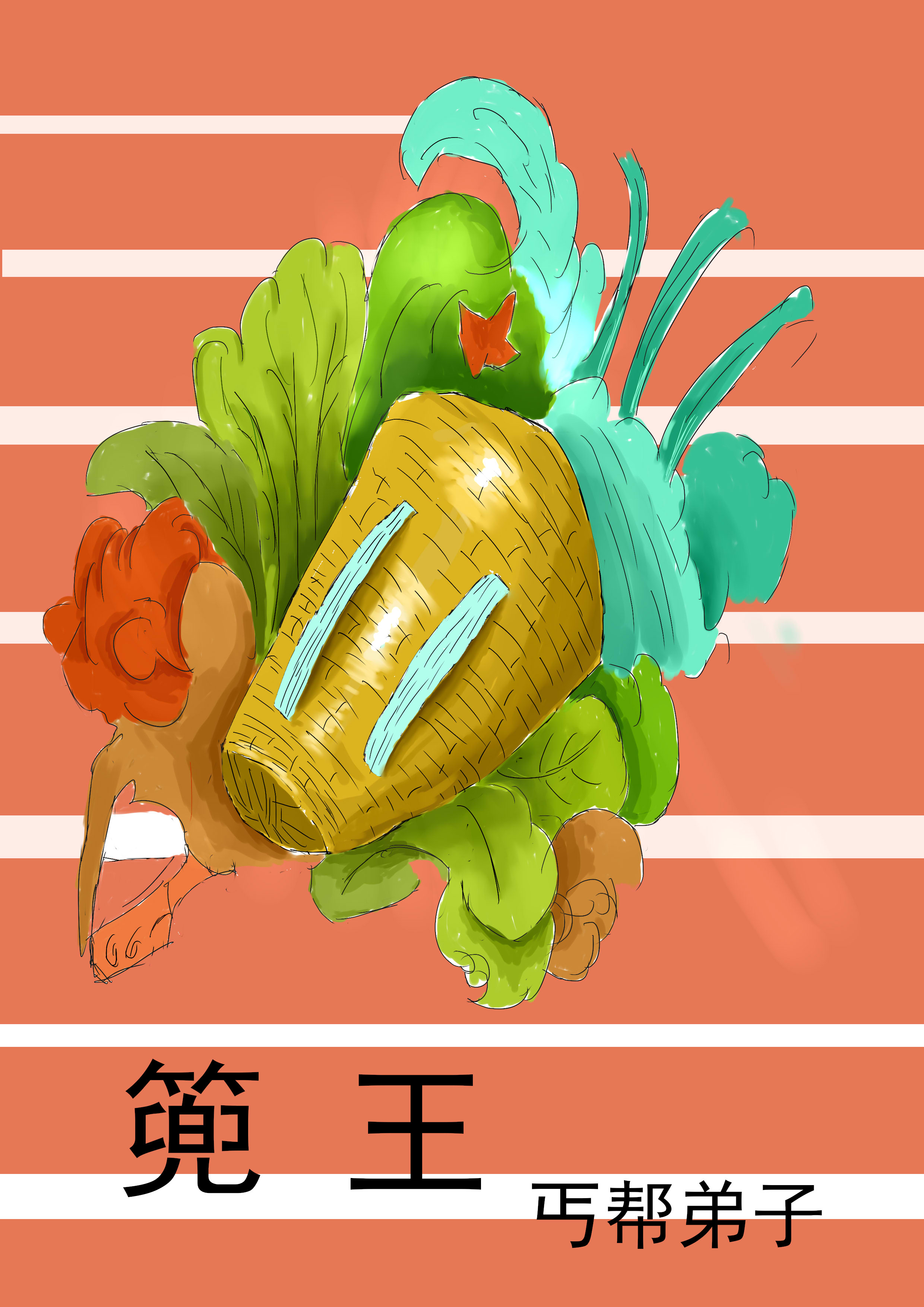“谟樾,来,师娘给你挽个髻,以后,就如此挽你的发髻。”
师娘帮谟樾挽好发髻后,从怀里掏出一个方巾,捆扎在谟樾的发髻上,谟樾穿越过来,虽对古人这些繁琐的头饰,还分辨的不是很清楚,可这种男式的发髻,她还是知晓的。
“师娘,为何要为谟樾梳男儿发髻?”
师娘没有回答她,到房里,找了一件青蓝色的棉袍,帮谟樾穿上,说:“这是师娘给你哥哥补的棉袍,这都穿了几年了,定是有些小了,正好给你穿上。若被他们抓了去,你爹和哥哥,还有你那死去的舅娘的付出,就白瞎了。所以呀,听师娘的,日后,就这身装束。”
听了师娘这些话,谟樾走到桌前,慢慢卷起自己慌乱中,从家里跑出来,弄散开来的那秘籍竹简,心想着梳这种男儿的发髻,就这身男儿的装束也好,更便于自己去寻找爹和哥哥。
“好了,师娘再去给你们抱些柴,添把火,也不早了,都早些歇着吧。”没想到,师娘说着这些,刚推开门,就被一支飞来的箭射中。
“谟樾,有歹人在此,快,快走!”
谟樾还没反应过来,又一支箭飞射过来。
“快——去找贤芝。”
“师娘——”
师娘口吐鲜血,一头栽倒下去。
而此时,有人在师娘家院子外的草垛上,点燃了火,火光冲天,照着冲进来的人马,谟樾一眼瞥见一个妇人,也在其中。
“是,畀娘?”
谟樾将手中竹简塞进衣襟,拉着绾偲,打开后门,朝后山跑去时,在路上遇到正往这边跑来的贤芝。
“贤芝,快,跑——”
谟樾牵着绾偲,又拉着贤芝,向山上跑去时,听到了畀娘在她们身后,扯着嗓子喊着:“她们上山了。”
谟樾边跑,边思虑着这畀娘定是也知晓了什么,否则怎会带着这帮人过来追杀?
“老远的,就见我家那边起火了。谟樾,可有见到我娘?”
贤芝边跑边问。
“师娘,她,被他们射中了胸口。”
“放手,谟樾你放手,放手哇。”贤芝想挣脱谟樾的手,折返回去,可谟樾抓着她,死死的不放,含着泪说道:
“师娘说,若是被他们抓了去,我爹和哥哥,还有我舅娘的付出,就白瞎了。现在,加上师娘,贤芝,我们不能让他们的付出都白瞎了。知道吗,贤芝。我们,我们跑。快跑哇——”
贤芝被谟樾拽着,边哭边跑,她们一口气跑上了山坡,又拐进了山林,在山林里穿梭着,谟樾没想到自己这小身体,竟有这么大的能量,她们一口气跑进了山林深处,贤芝和绾偲都气喘吁吁了,自己还能平和地喘息。
“贤芝,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谟樾指着山角下,一处被圈起来的房舍,好奇地问道。
贤芝揉了揉眼睛:“天啊!这是不是我娘说的那个瞒狱?”
“什么?瞒狱?师娘说的,绾偲她娘会不会被关在了这个瞒狱里?”
谟樾满脑子的疑问,没想到绾偲却点点头,说:“对,我听到过那鸾娘问一个老家仆,说起过山的那边,有个瞒狱,可他们没说我娘是不是就关在这个瞒狱里。”
谟樾说:“走,去看看。”
贤芝直摇头:“不可,万万不可。谟樾,这种地方,不能随意乱闯,此地关的当都是城旦舂,这些城旦舂……”
贤芝没有往下说,谟樾也知道她想说什么,贤芝毕竟在她们三人中,年长几岁,对城旦舂的这些人和事,定是比她们要知道的多一些,可绾偲一听要去瞒狱,便高兴起来,连着发了几天高烧的小脸上,凹陷下去的一双大眼睛,忽闪着光亮。
“姐姐,我们快去,快去找我娘。”
“绾偲,不可,不能去,被人抓到,是会被处罚的。”
贤芝阻拦道。
谟樾定定地看着贤芝,突然说道:“我们就近前看看,又不进去。”
贤芝无奈地答道:“不进去啊。我们,只看看。”
谟樾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嗯。只看看。”
从山上往下看,很近。
可从山上绕下来,真的走到这座房舍前时,天已经擦黑了。
远远地站在正大门朝里看,黑压压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们朝前走走,怎地什么也看不清呀?”谟樾悄悄问贤芝。
“我们,我们还是走开去罢,这里野草好深,会不会,有蛇?”贤芝扯拉着谟樾和绾偲的衣袖,说道。
“不怕,我们有大棒。”谟樾在脚下,捡起一根木棒。
一道光亮,突然照了过来,几盏马灯好似同时点起,照得一片通亮。
瞒狱的大门也“咣当”一声,打开了。
“回来了,他们回来啦!”一群崴动着忽高忽低的人影晃动着,欢呼着,从大门里一下子涌了出来。
而此时,她们的身后,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类似野猪之类的家伙,被四脚朝天地捆绑在一根木棒上,被人抬了进来。
跟在这群人的后面,一个被五花大绑的毛脸胡子男人,也用同样的方法被抬了进来。
这群从外面回来的人,与里面涌出来的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这股“洪流”汇集到门口,将谟樾、贤芝还有绾偲一同卷入进了这座被圈起来的“城”。
站在瞒狱里,她们才发现,这里的房舍,所有房门一致朝一个中心开着,围成一个圈,这个大门就是这个圈里唯一的一个“缺口”。
谟樾回头望了一眼大门边把守的几个男人,个个高大威猛。
谟樾小声跟贤芝和绾偲说:“别怕,我们又不是城旦舂,他们会放我们出去的。”
贤芝不敢吱声,只顾点头。
绾偲却东张西望,寻找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她的娘。
这些抬着野猪和那个毛脸胡子男人的人群,绕过神龛,终于在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
“苍天在上,瞒狱之人,也是人……”有人大声说着。
突然,一只大狗跟在贤芝的后面“旺旺”地吠叫。
“啊——!狼呀——”贤芝哭叫着,丢掉被谟樾拽着的手,拼命地朝前跑起来。一不留神,脚下一滑,跌倒在地。
谟樾抡起手里的木棒,朝那恶狗打去,被人喝道:“哪里来的毛头小子,胆敢打监长的狗。”
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来,谟樾心里开始有些懊悔了。
这是不是正如师娘所说,他们的付出都白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