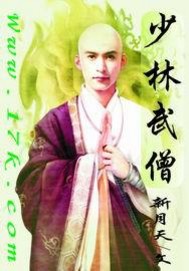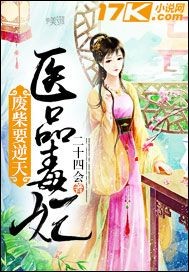文宣摇头,“不像。”
那场疫病的人,得了传染不到半刻就会发狂。一旦发狂就会彻底失去意识,没日没夜地咬人,不死不休。且传染速度极快,跟现在的比起来,那可惨多了。
好在守城大将发现得及时,在传染初期就把四方城门给封死了,才不至于把疫病给流传出去。只是,等朝廷派来的人撬开城门时,发现一切早已无力回天。
近三十万人的边境大城,竟没一个活物!城中黑压压,尽是断肢残骸,臭气熏天,那惨状,许多随军前来的大夫因受不了这味道而直接被熏晕。
后来,朝廷人下令将城中尸体集中堆积掩埋。
埋尸地好像就是青木禁地。
至于锁城后发生了什么,已无从考证。
只是自那以后,这药王就再也没在天上出现过,名字也在仙册上消失了。
大家都认为他是在神略大战中陨落的。
昊天神主发明仙册,意在方便通过仙册及时召唤神祇,所以,写名字用的都是仙家的最后气运。
神仙名字从仙册消失,就意味着彻底陨落,再无重返世间可能,这是件极严重的事。
千百万年来,天庭神仙来来回回,陨落飞升,飞升又陨落,名字会在仙册消失的少之又少。
唯一一次消失高峰是神略大战,密密麻麻上万个名字最后只剩下稀疏的几百个,相当于整个天庭都折了进去。少了个药王,也不会有谁在意。
梦回沉吟着,“难说,药王叫什么?”
文宣,“早忘了。神仙的岁月那么长,每天都是新开始,谁记这芝麻绿豆大的事儿。”
线索又断了。
梦回抬头望天,繁星点点投进她桑紫色瞳眸里,琉璃万丈,却也沉寂得可怕。
她变了,变得沉默而疏离,不再是以前那个把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的小乌龟了。
如今的她除外表像他的故人,里子藏着的,仿佛是另一个人的灵魂。
所有的熟络,不过是故意装出来的罢了。
“你怎么了?”他不禁问。
梦回侧眸望向他,“没什么,我在想,既顺着查不出线索,不如来个反向侦查试试。”
“反向侦查?”文宣眸光微漾。
“假定一个条件成立,将未知变成可知。”
这玩法,很是新鲜。
文宣顿时来了兴致,问:“你想假定的成立条件是什么?”
“主谋是蓼生。”
梦回信步朝前走,道:“昨天我在这附近发现了一批虫人。他们皆一致指认,那个诱骗他们服用长生丹的是他。就目前来看,长生丹效用与续命金丹差不多。续命金丹是葛天舒发明的,他作为葛天舒大弟子肯定知道研制丹药的方子。只是一点,我不明白,一向纯善的他,深知服用此丹后果,为何还要做出这种事。”
文宣听她把假设理由说完,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年头,幻化成某个人的模样,于神魔鬼怪而言,并非难事,更何况是欺骗几个普通老百姓。
虽说是假定,要是不小心猜错,怕是会将案件推向不可预测的方向。
她点头,“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
眼看她就要走出青木禁地了,风狼着急,连忙咬住她的裙摆,道:“等一下!”
梦回转身回首,望着趴在地上的他,问:“怎么了?”
“你忘了我们来这的目的?彩娟还没找到!”风狼提醒。
梦回微怔,好像是这样子。
只见她环顾四周,发现整座山林静悄悄的,除时不时传来的恐怖哭笑声外,再无其他气息。
“你有线索?”她问。
风狼摇头。
“你知道去哪找?”
风狼继续摇头。
“这不得了!先想法子把案件破了。说不定她就回来了。”梦回说完消失。
桐玉宫光洁明净的台面上,一抹鲜红影子正倚靠着雪榻狐枕,晃动着手中墨玉杯盏,饶有兴致地盯着台中画面。
“小颜妈妈!”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从万丈瀑布上传下,一只散发着幽幽红光的地萤出现在红衣女子面前,划出一道优美弧度后,落地成半大的女娃娃,双丫髻,素红衣,模样圆滚滚的,很是齐整可爱。
“怎么,舍得回来了?”红衣女子放下杯盏抬眼望向她。
女娃咧嘴一笑,露出整齐糯白的牙齿,跑到她身边坐下,故作神秘道:“妈妈,你猜痕儿找着了什么?”
说着,也不等红衣女子回答,将肉嘟嘟的双手合上,一阵红光过后,小心翼翼打开露出一只毛茸茸的鸟儿,“方才路过湘州地界,发现一只跟若姐姐殿里一样的鸟儿,便让小青给抓来了,是不是很好看?”
红衣女子微愣,差点笑喷,抬头望了眼盘旋在明镜台上空的通体雪白的上品神鸟雪王海东青,捏着她圆滚滚的小脸儿,道:“亏你想得出来,快给你若姐姐还回去!”
商痕大感委屈,泪眼汪汪,十分不服,道:“这是我在路上抓的,不是玉景殿的。”
“正是因为在路上抓的,才让你送回去。这会子她正找呢!”
红衣女子说着将目光投向台面上,上头映现的正是梦回站在青木山石像堆前凝神思考的画面。
“噫?”
女娃瞪着双乌溜大眼,一脸惊奇道:“若姐姐不是不喜欢出去的吗?什么时候离宫的?”
“前两天代表桐玉宫调查湘洲虫案去了,你路过时他们刚好在那。”红衣女子坐了起来,活动了下筋骨。
女娃双眼一亮,兴冲冲道:“什么虫案?好玩吗?痕儿也想代表桐玉宫查案,妈妈,你让我去好不好?”
红衣女子拉下脸,道:“就你三脚猫功夫,不添乱就不错了!梁辰。”
一道白光从星光环绕的内宫闪出,一个白影出现在明镜台下,冷着脸问:“找我何事?”
红衣女子一看到他那苦大仇深的样子,就忍不住叹气,“顺口就把你叫来了。既来了,也别急着走。痕儿方才把玉景殿灵宠给抓了,你帮个忙把它还回去。”
白影接过鸟儿,转身消失。
台面上的画面转向相月城郊绿树环绕的茅屋小院中。
月华如练,安静地倾泻在院中的每一个角落。
翠绿的桑叶顶不住山风的呜咽,心一软,便簌簌地落满整个院子,与地面摩擦发出嗒嗒的声音,像一阵绿色的雨,怎么下也不完,不觉间已然将新坟覆盖,变成一座绿油油的土丘,孤独地伫立在树下,仿佛在静静守候着谁的归来。
风狼按着带着张长月找到张家院子的时候,张丰年和王氏将将熄灯歇下。
她在门前站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推开茅屋小院的篱笆门,眼泪却忍不住簌簌往下掉。
记忆中的家,何等的风光无限,无论什么时候,家中都是人来人往。
就是入了夜,万籁俱寂的时候,门口依旧会有两三个守门人守着,丫鬟们也会穿梭在廊檐庭院间收拾家务,从不曾如此荒凉落魄过。
她步履轻盈走到庭院中的桑树下,抚摸着粗糙的枝干回想起家中药房前也有这样一棵树,不过那树要比这棵大些。
小时候奶娘时常抱着她指着那棵桑树跟她讲关于它的故事。
奶娘说这是她大嫂子像她一样大的时候跟爹爹来张府玩,拿着当药材用的桑树干子在这里种下。桑树干子本是养不活的,可她哥哥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在他坚持浇水施肥一年后,竟抽芽长大了!
而事实却是,那时张大郎六岁,已初具药物常识,他很直白地告诉小赵栖,这样种树是种不活的。
小赵栖蹲在泥巴地上,满脸满手污渍,盯着眼前不知从哪冒出的小胖子,眉头一拧,嘴巴一撅,哇地一声就哭了出来,跑到厅堂找爹爹告状,说张大郎欺负她。
张大郎也不是个吃闷亏的,为自己在两家爹爹跟前据理力争。
可他肉墩墩的屁股依旧没能幸免于难,吃了张丰年好几个巴掌。
临走前,小赵栖眨着双水灵灵大眼睛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之后,也不忘叮嘱他,一定要照顾好她种的小树苗,不然下次来家里玩,小树要是死了,她会找他算账的。
张大郎摸了摸火辣辣地屁股,再看了眼正眉目含笑盯着他看的张丰年,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便默默地点了下头。
自此,张大郎每天都会蹲在这桑树干前,每隔半个时辰浇一次水,并对这它念念有词,希望他能快快长大。
一次奶娘撞见了,实在看不下去,便道:“少爷何不找棵树苗把它给换上,就是赵家妞妞来,也不知侬换没换。”
小胖子蹲在树干前想了想,觉得奶娘这法子虽不正道,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便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桑枝干给换了。
第二天奶娘发现,觉得大少爷采用她的建议,是件十分值得自豪的事,便帮忙大肆宣传,说少爷的诚心感动了上天,把桑枝干给养活了。
府中下人们对此皆啧啧称奇。
这些话流传到张丰年夫妻耳中,他们也只是笑笑罢了。
春去秋来,花落花开,一晃就是八年的光阴流逝,当年的小屁孩都已成了公子佳人。
赵栖再次踏进张家门槛,已成张家新妇。
成婚第二天,她在丫鬟陪同下逛到药房门口,看到那棵亭亭如盖的桑树在微风吹拂下,簌簌地飘散着落叶时,一时有些出神。
这一幕被老奶娘看见,就美滋滋地跑过去跟新妇说起当年种种,并十分笃定地告诉她这就是当年她种下的那一棵。
赵栖一时间百感交集,原来缘份就是这么奇妙,在你不知不觉中,就已埋下,生根发芽。
她低下头,红着脸,也不知是害羞还是感动,“俺以为他没放在心上,没想,还真让他给养活了。”
自此以后,张大郎与赵栖一直是相月城中出了名的神仙眷侣,就连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们心里想的,都是彼此。
张长月被桑树旁伫立的一块木板吸引,凝神一看,月光下“亡妻张赵氏之墓”六个墨色大字如此醒目。
她脑子嗡的一下,想起自己回家前兄长对自己的嘱咐。
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她终是没忍住,跪在坟前呜呜哭了起来,声音凄恻,惊起山中鸟群,惊动了屋内尚未入睡的人。
因这些天发生的事,张丰年王氏虽是熄了灯,可他们躺在床上根本没有睡意,脑子想的一会儿是孙子,一会儿又是儿子,乱哄哄的,突然听到院子传来哭声,委实吓了他们一跳,忙从起身轻手轻脚沿着墙壁走到门缝上看。
只见一个身穿凤冠霞帔的女子正跪在赵栖坟前掩面痛哭。
这可他们吓坏了。
夫妻两相互交换了下眼色,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王氏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希望女鬼不要发现,不然他们这两把老骨头可打不过这鬼物。
“娘!”
文武兄弟躺着的方向忽然传来一个喊声,张丰年看了下他们,没有动静,估计是做噩梦了。
这两天他们都这样。
王氏忽然紧张起来,指着门口。
张丰年往外一看,差点没被吓死。
红衣女鬼已经从坟前站起,月光照在她惨白的脸上,胭脂泪痕横一道竖一道,模样十分可怕。
关键是她已经走到门前,还在拍门。
被恐惧支配的张丰年和王氏从一旁抄起扁担苕帚,鼓足勇气,只要女鬼一进来,他们就打死她。
“爹、娘!俺是虫虫!”女鬼忽然说话了。
两老愣了愣,不是很敢相信小女儿会在这时候回来。
张长月见里面的人不作声,便出力,使劲一推,把门推开了。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回家迎接她的是父母的一顿毒打,一边打还一边骂她,“虫虫?虫虫恁的会这时候回来,她又是如何得知俺们的住处?侬以为她傻,还是咱傻!”
“虫虫可比侬好看得多!”王氏道。
张长月差点被气吐血,要怪只能怪这身衣服和这浓厚的新娘妆。
她被父母追着满屋子跑,被逼到角落,蹲下大喊,“别打!俺真的是虫虫!”
两老愣了愣,好像面前这女的真不大像鬼。
“侬真是虫虫?”王氏将信将疑。
“不然!”张长月倍感委屈,泪眼汪汪。
她这是招谁惹谁了?回家就得挨打。
张丰年凑近一看,端详了好一会儿,才从那张哭花了的脸辨认出自家女儿来,问:“侬怎的回来了?妙生药师也来了?”
张长月摇头。
妙生药师是张长月师父的号,药材行业百科全书,泰山北斗般的存在。
很多药材商遇到不懂的问题,或是发掘到什么新奇药物,都会找他鉴定分析给出建议。
药材世家的家长都希望能把孩子送到他身边,要是能得他一两句指点,那可是件无上荣幸的事。
可他向来闲云野鹤惯了,无意收教徒,张长月是他的破例。
只见她将在路上听闻相月城出事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跟爹娘说了遍。
她是有跟药师提过要回家的,可药师并不赞同。
理由是相月城现在很危险,没找到解决问题方法,便贸贸然回去,跟送羊入虎口有何区别?就是回到了家中也是只有添麻烦的分。
当然,思家心切的张长月并没有听从师父的建议,趁他不注意,就偷偷跑回来了。
张丰年听了,差点没被气死,颤抖着手,指着她大声呵斥,“糊涂!你知不知道咱家惹了多大祸事,竟敢瞒着药师跑回来,恁的这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啊!”
“俺没想这么多,当时听到消息,俺害怕极了,怕爹娘出事,就回来了……”张长月被父亲吓到,深感委屈,抱着王氏呜呜哭了起来。
“咳!孩子不顾安危回来,恁的还说她。”
王氏搂着女儿安慰,发现她这身衣服冰凉滑腻,不像是普通的布料,摸着还会渗出红色的液体,问,“侬衣服恁的回事?掉色也忒的严重,一个女儿家,装成这样,成何体统,还不快快换去。“
张长月愣了愣,这身衣服是她从鬼洞穿出来,一直穿到现在,王氏不提,她并未发觉有何不妥。
只是母亲这样一说,倒也发现了,只觉身上湿漉漉的像是有许多虫子在皮下蠕动。
她想脱,却发现衣服没有开口,像长在她身上一般。
一丝不详的预感涌上心头。
她惊恐地推开王氏,开始撕扯身上的衣服,可撕下的竟是赤红的一片,鲜红的粘液与皮肤粘连着,缺口很快就愈合了。
可就算是仅是刹那,张丰年与王氏也已看清,在那鲜艳红衣下鲜血淋漓的肉。
张丰年忙把妻子拉过来,顾不上管女儿,大步流星冲向厨房水缸,想帮妻子把身上的红液冲洗掉,可他拿着水瓢转身发现,不知何时,妻子整个人都被红液吞噬掉了。
“爹娘,这是虫子!”
张长月慌慌张张从屋子冲出,发现母亲早已变成了一滩血水,父亲的一半身子也被一团红色的液体吞噬,满脸惊恐地看着眼前她。
“虫虫……”他伸出手,想告诉女儿,其实这些年他这个当父亲的,很想她。
能看到她回来,他很高兴。
可这些话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便融化成了一滩血水,与王氏融合在一起,顺着地势,化成无数条细小血线回到张长月身上,交织成一件更为隆重艳丽的嫁衣。
血红裙摆在月光映衬下,逐渐浮现出两个诡异的暗色图案,仔细一瞧,像两个老人惊慌失措的脸。
张长月跪倒在地,尖叫痛哭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院子上空竟多出了一道黑气,似乎有什么诡异物体隐藏其中。
忽然一道银光飞从院外飞来,将黑气击散。
银光落到地上,正是龇牙咧嘴的风狼。
它目光警惕地绕着张长月转圈,露出锋利的獠牙,作势要往她身上扑。
“住手!”
梦回人未到,空间界面已经到了。
风狼的前扑并没扑到张长月身上,而是扑进了她随机打开的一个通道里。
“你怎样?”梦回上前想扶她。
张长月却像见到鬼一样缩到一旁,连滚带爬跑开了。
“不要碰俺!”她道。
“这地方,煞气很重。”一个白衣男子从院外款步走来。正是文宣。
梦回白了他一眼,看向张长月,发现她身上衣服不一样了,皱眉问:“你衣服怎么回事?”
张长月闻言,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好一会儿才抽抽噎噎道,“它杀了俺父母。俺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这衣服,俺脱不掉……”
“你别激动。”梦回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张长月安慰道,“你先冷静下来,哭也没有用,我们一起想办法。”
“办法?办法它能把爹娘还给俺?”张长月问。
“人死不能复生,这道理你应该懂。”文宣语重心长道。
“侬……侬是何人?”张长月问。
“我?”文宣把声音拉长,故作玄虚,道:“我是你祖宗。”
…………
“你能不能正经点。”梦回没好气道。
文宣不服,“我堂堂湘洲府君,说是她祖宗有问题么?”
梦回不想跟他吵,对张长月道:“你别怕,让我看看这衣服怎么回事?”
“它会吃人。”张长月道。
梦回撩起她的袖摆,发现这料子粗看跟普通衣服差不多,但仔细看,竟是由一层层细红粉末般的虫子组成,想看清虫子的形状,得花费好一番精力。
梦回像脱手套一半从被虫子侵蚀的手里取出一双新手。
虫子无所依附,掉落在地上化为血线流回衣服上,与此同时,宽大的衣摆上现出一双暗红手印。
“什么玩意儿这么可怕!”文宣惊呼。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梦回道。
“你说。”
“你猜要是用这虫子对付血吸虫,那种会比较厉害?”
文宣耸肩表示,“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