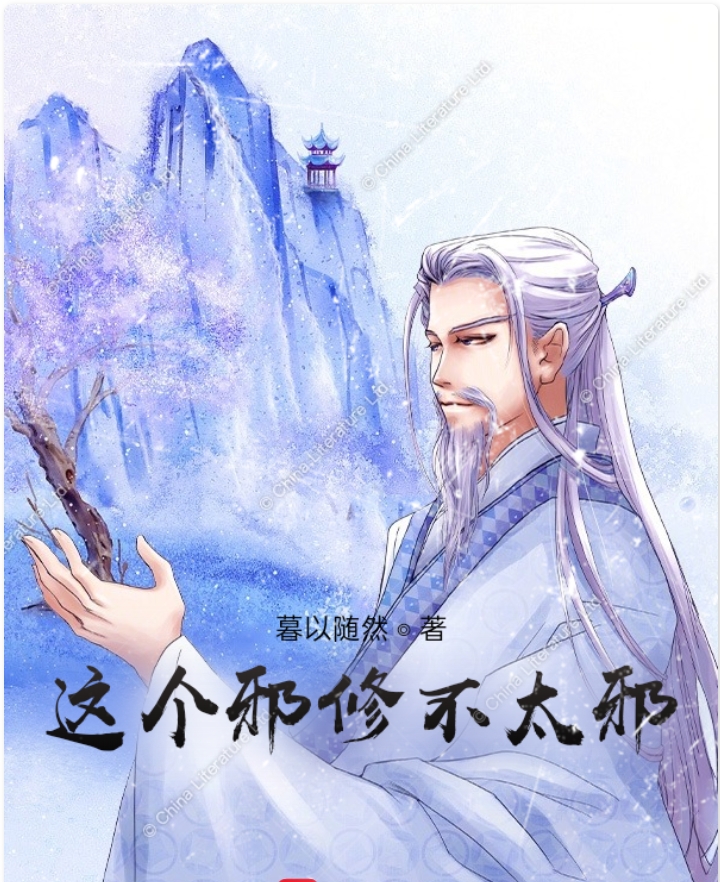夜幕低垂,万家灯火。
五楼的一家住户里突然传出一声撕心裂肺地大叫。何妹久下手果然狠毒,将何久倒吊着好一顿毒打,又以蜈蚣爬身,欲将蛊虫逼出。
只不过,非但未有蛊虫出体,何久却已是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何所惧忙将儿子放下来,不停责备妻子。
“老何,儿子肯定中蛊,断然不会弄错,你若是也中了蛊,必然会相信我的话。”
这是要给他下蛊的信号么?何所惧只感到毛骨悚然,一边连连摆手,一边叫了起来:“我可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你别胡来!”
看到丈夫吓得连连后退,杨妹久笑了起来,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老何,我不是这意思……”
何所惧一直后退,直到退到了厨房,把门关严,这才稍稍感到一丝安全,隔着玻璃窗叫道:“即便是真的被人下蛊,那也要先问个明白。打蛇打七寸,射人先射马,有的放矢才是正解。你这样搞,会把儿子整死的!”
杨妹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丈夫的话不无道理,目前来看,下蛊之人手段非常,要想逼出蛊虫绝非易事,唯有从长计议。
她将儿子扶起,掐了掐人中,让丈夫倒碗水过来。何所惧连连摇头,哪里敢出来,即便杨妹久做了保证绝不下蛊,他也不踏出厨房半步。
杨妹久笑言:“真要下蛊,你觉得躲在厨房里就一定安全么?”
何所惧懵了,出来也不是,不出来也不是,只得让妻子再三保证,最后发了毒誓,这才勉为其难的打开一道缝,见妻子和颜悦色不像是动怒的样子,稍稍放下心来,端了碗水挪步到她三米开外,突然将水放在地下。
“至于吗?”杨妹久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让我再缓缓。”而后迅速转身,跑去屋外吹风抽烟去了。
上刀山下火海,天上地下什么都不怕,唯独怕一只蛊虫。以后还是不开这样的玩笑为好,杨妹久也只能苦笑摇头。
何久慢慢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使劲的把手指往喉咙里抠挖,刚才吃的饭菜吐了一地。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妈,我难受……”
“想吐却吐不出来?”
何久点点头,哭道:“胸口还疼,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撕咬我。妈,我是不是要死了?”
“一只虫子而已,死不了。”
何久脸色一变,跳了起来,千算万算,千防万防,还是被人下了蛊。想到身体里有一只虫子每日每夜的在吞噬自己的血液,他的心就抽搐成一团。不管是什么虫子,给我弄出来,哪怕是开刀,挖也得给我把它挖出来!
杨妹久笑笑,告诉儿子知晓了病根,还需找到源头,才能想办法对症下药。何久本不愿意说,因为他答应过香香这是两人的秘密。但此刻也管不了这么多了,痛成这样跟个废人有什么区别?
……
……
认识香香,是在马蹄坡。
这年,她十八,何久二十八。
阳春三月,公司组织员工旅游,不喜结伴的何久独自游山玩水之际忽闻对面的马蹄坡上隐隐有歌声传来。那歌声,如百灵鸟,清新脱俗,悦耳动听。他一下子被吸引,不自觉地向着歌声的发源地跑了过去,这时候的他,早就将导游的再三叮嘱抛诸脑后了。
果不其然,马蹄坡上有一女孩一边砍柴一边唱歌。歌声甜,人更美,在深山里长大的女孩,浑身散发着一种别样的美。用他的话说,马蹄坡上歌声飘,恰似仙女入凡尘。只不过,他的赞美却惊扰到了女孩,歌声戛然而止,笑容随之冷却,她警惕的向后退去。
“我不是坏人,我一辈子都没做过坏事……”
女孩的脸上闪过一丝惶恐,一丝疑惑,下意识的向后退去时脚下被树藤绊倒,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
“你……是不是听不懂普通话?”
这个女孩难道是从不与外族人联系的夯吾寨的人,要不然,怎么可能见了生人如同遇见了猛兽一般?正考虑要不要上去搀扶,忽然从大树后面窜出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来,见了女孩,也不说话,只是“嘿嘿”冷笑着就往她的胸脯抓去。
“……”女孩声嘶力竭的怒斥。
语速太快,加上说的是苗语,何久根本听不懂,只当是自己吓着了她,心里不由苦笑。好人和坏人分不清也就算了,怎么见了生人这么害怕,世上为什么还有这么封闭落后的地方?不过对于这种事情他是无能为力的,记得妈妈说过,见到生苗的人有多远躲多远,因为生苗的女孩或妇女大多都会放蛊,他可不想平白无故的就被人身体里放一只虫子进去,想想那该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没走几步,身后突然传来男人的狂笑。下意识的扭头看去,一名汉子已骑跨在女孩身上,正在动手脱她的衣服。只是女孩似乎并不慌张,伴随着衣衫的裂响,她突然五指分张,一只褐色的虫子出现在手心里。
向来粗心大意的何久哪里留意到这个细节,见到有人欲行不轨,早已勃然大怒,三步并作两步往前急冲,飞起一脚将那大汉踢了个四仰八叉。那汉子显然不服,可何久自幼随父亲习武,虽时常偷懒,可二十多年来终究也是有些底子的,莫说一个人,就是三五个,也是近不了他的身,三拳两脚便将那汉子打得遍体鳞伤。
女孩鞠了一躬,她说话时语速很快,不时地向四周张望,这时候,何久突然见到有一只褐色的虫子沿着手臂钻入了她的衣袖中,速度很快,只一闪便已消失不见。
何久突然想起妈妈说过一句话,不要看生苗人的眼睛,那有毒。他盯着她的手,深怕她突然给自己下蛊,莫名的紧张起来。
这时候,一个男子的呼唤声传了过来,听到这个声音,女孩的脸色立马变了,匆匆向何久再次鞠了一躬。
这个呼唤是个重复音,何久听懂了。原本他也能用苗语对话,只不过妈妈教他时,他要么三心二意,要么敷衍了事,以至于旁边的张凤燕都学会了,他还是一知半解。到最后,只能用苗语说一些简单的话,十个字以上的他就费劲。
“你是……香香?”
听到他用苗语说话,女孩微微愣了一下,继而点点头,冲他微微一笑。
“我叫……何久,何——久——”何久尽量让自己的发音显得完整一些。但他的苗语如同两三岁孩童的“牙牙学语”一般,不阴不阳,不明不白,又不伦不类,使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我要喝酒”。
香香又微微愣了一下,但还是从腰间取下酒囊,先喝一口,以示无毒,而后递了过去。
何久知道她误会了,也不争辩,笑着接过来,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醇香,甘甜,爽口,这哪里是水,分明是米酒。
“好!好!好喝!”他呵呵地傻笑着,如同一个白痴一样,米酒自嘴角两旁流溢出来。香香抿嘴笑笑,从胸口取出手帕,小心翼翼的给他擦拭。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何久有些陶醉。从来没有哪个女孩子跟自己这么亲近过,又如此的体贴入微,张凤燕没有,王静怡更没有。头脑一热,他猛地抢过手帕。
“你……”香香睁大眼睛,显然被他的举动吓到了。
“我弄脏了……洗干净了还你好吗……”这是何久有史以来用苗语说的最长的一句话,犹如一锅夹生饭,让人吃着很不舒服。
“你是说要还我?”他的苗语不伦不类,香香需要确认。
“我……”何久不知该怎么回答。因妈妈是苗族,所以他知道一些苗族的规矩。手帕定情是苗族的一个规矩,问题是这个手帕不是赠送的,而是他抢的。他又不敢多说话,生怕一旦说错了,这个女孩会对自己下蛊。
“想好了吗?”
听出香香的话语中含有催促的成分,怕说错又不能不说,何久紧张到额头冒汗。
“要还吗?”
话音未落,何久便慌里慌张的脱口而出:“听你的!”再不说话,真的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活着离开。
“我又不是老虎……”香香笑了起来。
后面什么话何久没没听懂,但他很快被她的笑声所吸引,仿佛她的笑有种魔力似的,原本绷紧的神经完全放松了下来。
他忍不住抬起头来,突然深深震撼到了。肤白貌美,何止倾国倾城!即便是月宫里的嫦娥,也要逊色三分。
“不还了,可以吗?”忘记了妈妈的忠告,更忘记了不礼貌,他紧紧的盯着她那粉腮红润的脸,脉脉秋水的眼眸。
“只怕不行。”
虽是拒绝,可看起来她似乎在笑,又似乎有些害羞,那微晕红潮一线,拂拂桃腮熟的俏脸让何久呆若木鸡。
这时候,呼唤声越来越近,她背起干柴就跑,何久猜测那多半是她父亲,因为只有父亲,才能喊出那中关切又急切的声音。想到今后不知还能不能再见面,何久冲着香香的背影,用他那半生不熟的苗语喊道:
“香香,下月初一,这里!”
香香站定了,转身冲他嫣然一笑。这一笑,恍若云开雾散,百花齐放,似乎天地也为之黯然失色。
他摇晃着身子蹒跚下山,不知为何,只感觉脚底发飘,走路不稳,没走出多远,“扑通”一声栽倒。
酒,果然是好酒!
……
……
“就知道喝酒!你们一共见了几次面?”
面对母亲的质问,何久不敢有半点隐瞒。一共见了十八次,第一次匆匆一面,第二次待了三小时十五分钟,第三次是四个半小时,从第四次到第十七次都是一整天,最后一次出了夯吾寨玩耍了三天。
他如数家珍的说完,见到母亲的脸上冒着冷气,眼睛里喷着火气,突然意识到不妙,特么的说得太清楚了,比老爸教他习武时让他背的口诀都还要清楚!
“通常生苗的人胸口上会有痣,应该是三颗吧?”杨妹久注视着儿子,似笑非笑。
何久微微一愣,摇了摇头:“没有啊,我没见到啊……”
话未落,突然头上被狠狠地敲了一下。好啊,你个臭小子,瞒着你妈和生苗族的姑娘好上了!杨妹久一顿怒斥,却没有再对儿子“用刑”,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
“妈,还没到那地步……”何久想辩解,可又不知该怎么说,胸口隐隐的又痛起来了。
听到骂声,何所惧忙丢了烟头跑进来,杨妹久指着儿子冲他骂道:“瞅瞅你儿子,和人家姑娘都已经睡上了,生苗族的姑娘是你能惹的么?没救了!没救了!”
睡觉?这哪儿跟哪儿啊!虽然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但每当见到香香,这些乌七八糟的想法就从来没有在脑海中停留过一秒。最多也就是第十八次见面的时候亲了一下她的手,那三天来,他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却是他有生以来快乐的时光。
听着儿子的解释,杨妹久显然不信,厉声质问儿子到底怎么回事。何久矢口否认,只说无意中看了一眼,再没有其它过分的事。
何所惧笑道:“人家都已经暗示到了这种地步了,你会无动于衷?”
本不擅长辩解的何久越描越黑,连何所惧都撇嘴笑了,这回他也不信了。
如果说母亲刚才的那一顿毒打使得何久伤害一万点的话,那父亲的这句话父亲的话直接戳中了他的心。何久怒了,从来不在父母面前高声喧哗的他第一次拍着桌子怒吼:
“信不信随你们的便!香香是我的香香,我不许任何人污蔑她,包括你们!谁要是在我面前说她半句坏话,小心我翻脸不认人!”
接着,“嘭”的一声重重关上了门。
见到儿子发这么大的火,夫妻俩面面相觑,深深的担忧在杨妹久的心头浮起:若是中了桃花蛊倒也还好,就怕是情蛊。
何所惧下意识地退后一步,他这辈子都不想见到蛊虫,甚至连“蛊”这个字都不想听到,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请把那个字用别的字代替好吗?不要再说了!”何所惧作揖以表感谢,可又忍不住内心的疑问。
虽说桃花蛊通常情况下无人能破解,但世事永无绝对,手术加上药物辅助治疗,三年五载也能恢复。若是中了情蛊,只怕是尚未开刀,儿子和那个香香就都死了。
“那如果让那个香香自己破咒呢?”何所惧觉得自己灵光一闪。
望着屋外的万家灯火,杨妹久陷入沉思,何所惧也不说话,搂着妻子的肩,吹着晚风。
“老何,我想去一趟夯吾寨。生苗危险,你还是不要去了。”
“不,我陪你。”何所惧注视着妻子,将她额前的一缕秀发捋至耳后,语气平淡又坚定。
夏夜,依旧炎热,晚风带着丝丝热气扑面而来,空气像是被燃尽了一般,令人无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