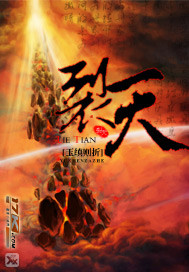二、魏晋时期的玄学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显学。玄学是以道学的典籍《老子》、《庄子》和《周易》(谓之“三玄”)为本,综合儒道而”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想。“玄”一词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玄学自何晏、王弼、嵇康、阮籍至郭象,经历了从贵“无”的本体论到崇“有”的存有论的一个发展过程。
(一)魏晋玄学的兴起
汉初以黄老之学治国,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东汉末年,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爆发了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儒学也受到沉重打击。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旧居之庙(指孔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
从玄学本身的发展来看,董仲舒神化儒学,创造了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理论体系。凭借神学支撑的儒学又倡导以“名”为“教”——把恪守各人的“名分”作为向人们实施教化的内容和目标。它告诫人们,做君主的要如何做才符合君主的名分,做臣民的要如何做才符合臣民的身分等等,各种礼仪规范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加之儒学被独尊以后,儒家经典成为人们求仕的敲门砖,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读经释经展开。读经释经日益繁琐,致使有的经典的一两个字被注疏达二三万字。许多人“皓首穷经”,也未通一经。正由于汉代经学烦琐的经注使人不得要领,粗糙的神学又易为人们识破,魏晋统治者就不能再沿用它,必须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玄学思潮便应运而生。
魏晋玄学是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的产物。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受到排斥。但道家思想并未从此止息,它作为官方儒学反对派的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如西汉末年的严遵、杨雄、桓谭,东汉的王充、仲长统等,他们在反对官方儒学神学目的论说教时,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杨雄吸取了老子清静无为的“道德”学说,但却反对老子废弃仁义、绝灭礼教的观点。王充继承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反对官方儒家神学。总的说来,汉代的道家一方面崇尚自然无为,另一方面又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其主旨在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学说,来论证封建等级秩序的合理性。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
汉末魏初,出现了一股崇尚清谈之风。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求声名与官禄,各树朋党。互相吹嘘,自此臧否人物成为风气。之后,清谈由品评具体人物发展为讨论才性问题与圣人标准问题,从而产生了才性之学。刘劭著《人物志》,提出弄清人的才质问题是鉴察人物的关键,还认为圣人应具有“中和之质”。刘劭的才性之学直探人物的本质,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而何晏、王弼的玄学清谈比刘劭的清谈更进一步,它从更抽象的角度,远离具体人物的讨论,直探世界的本源。
(二)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1.王弼的玄学思想
王弼(公元226__249年),字辅嗣,仅活了二十几岁,是玄学的真正开创者。他所提出的有与无、有名与无名、有为无为、名教与自然等问题,都成为后来的玄学家们的论题。王弼的思想是通过诠释《老子》、《周易》、《论语》等书而阐发出来的。他以道解儒,注重义理,一改两汉离经辩句的烦琐学风,开一代新风。
(1)“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在《论语·述而》中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日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意思是说,无亦称道,它无名无形,无声无体,不可为象。然而这“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也就是说,宇宙中一切有形、有象、有声、有体之万物,都是“无”(即道)派生的。所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老子道德经注》第三十八章)王弼对此从以下方面作了论证。
第一,从本末关系来说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他说:“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老子道德经注》第五十二章)这里的“本”是指无形无象的“道”或“无”,作为“道”的“本”是母,即“道”“(“无”)是“万物之母”。这里的“末”是子,子是母派生”的,因而“以无为本”。王弼还进一步认识到,无形无象无名的“道”或“无”虽然具有统摄万物的宗主地位,但它又并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而是与万事万物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它通过具体事物的得以体现。
从“以无为本”的思想出发,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崇本举末”的命题,并以之作为《老子》一书的根本宗旨。他以治国为例说明这一道理:“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政)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老子道德经注》第五十七章)“以”道治国即遵循“无”这一根本规律,以之作为治国之本,”则必然顺应自然,顺应规律,因时而动,因势而立,也即实行”无为而治;而“以正(政)治国”,则容易执着于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墨守成规,必然引起各种弊端。这些思想表”明王弼还将本末关系的理论运用于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
第二,从动静关系来说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他认”为现实世界是变化的,但否认作为本体的“无”或“道”的”变化,因而提出了以静为本,以动为末的形而上学的动静观。”他说:“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又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道德经注》第十六章)也就是说,万物千变万”化,根源在于“本”,而本是虚静的,动只是静的一种表现。”这就把静作为动的本原,而“静”就是“无”的别名,以此”说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其形而上学的动静观,是从属”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而是与万事万物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它通过具体事物的得以体现。这就把静作为动的本原,而“静”就是“无”的别名,以此”说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其形而上学的动静观,是从属”“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的。
第三,从一多关系来证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王弼”以为,万有是多种多样的,不能自己治理自己,必须有一个”“至寡”的东西来统率它们,世界才有秩序。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又说:“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在此,王弼将“至寡”解释为“一”。“一”又是什么呢?他在解释老子的“道生一”时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道德经注》第四十二章)意思是说,“一”也就是“无”,用“一”来统“众”,也就是用“无”来统“万有”,所以说,应“以无为本”。
(2)“言不尽意”的认识论
所谓言,是指表达思想和事物的语言;所谓意,是指思想意识或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言意关系的论述始于庄子,他将二者理解为工具与目的的关系,既承认“言”对于“意”的作阳,又反对执着于“言”。他以筌蹄(工具)和鱼兔(目的)为喻以阐明这一道理:“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王弼则继承并发挥了这一观点,进而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认识论。
“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这是魏晋时期人们探讨的重大话题。欧阳建等主张“言尽意”,王弼则主张“言不尽意”。王弼所讲的“言不尽意”,是对儒家经典《周易》所讲的言、象、意的关系的解释。《周易》是古代的占卜书,而占卜是靠卦象来进行的,每一卦都有自己的本意,本意表现在图象上,图象又靠语言来解释。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周易略例.明象》从言与象的关系来看,象是本,言是末,“言”,是用来明“象”的;从象与意的关系来看,意是本,象是末,明“象”是为了得“意”。因此,如果囿于物象和语言,就会舍本逐末:“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周易略例·明象》)言或象只不过是帮助人们得意的工具而已。得了意之后,则可以弃之不顾了。在此,王弼讲“言”不尽意,指出了语言的局限性,是认识上的进步。但他将言与意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让人“得意忘言”,则又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3)“名教出于自然”的伦理观
为了帮助统治者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王弼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宣扬名教(包括等级制度,伦常秩序和礼乐教化等)是“道”或“无”的产物,是自然派生的。名教出于自然,既抬高了名教地位,论证了名教出于自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强调了不要忘记根本而去追求名教的形式。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作用。
王弼认为,“道”或“自然”是仁义礼的本体,如果不明此理,仁义礼这些原本为调节人际关系而设立的道德规范就会走向其反面。故王弼得出结论说:“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老子注》第三十八章)这就是说,舍本求末,只能导致假仁假义;只有出于大道,出于自然,无所求的道德行为,才是名副其实的仁义礼。可见,为求仁义而行仁义,难免会出现道德虚伪。王弼的玄学调和了儒道思想,这是他与后来的阮籍、嵇康相区别之处。
2.阮籍、嵇康对玄学的发展
(1)“大人先生”醉吟与“广陵散”绝唱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生活在魏晋交替的政治动荡时代,他们不满司马氏的篡位夺权,以老庄之学作为立命的精神支柱。
阮籍(公元210_363年),字嗣宗,“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据说,阮籍行为怪诞,他常一个人独自驾车外出,任由马自己走,行至路之尽头,才痛哭一场,返回家中。阮籍有一漂亮女儿,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晋文帝每次派使臣去见阮籍,他都喝得酩酊大醉。阮籍如此醉饮达六十天,使臣终“不得言而止”。阮籍不但狂饮,还喜好女色。阮籍邻居为一酒肆,酒肆老板的妻子“少妇有美色”,阮籍经常去喝酒,醉后即毫无顾忌地躺在美妇身旁。阮籍还以超脱世俗的“大人先”生’’自况,作《大人先生传》等弘扬老庄思想。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史称:嵇康年少奇才,好老庄之学,“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嵇康生活与活动的年代,魏国大权已旁落于司马氏家族手中。嵇康对司马氏家族采取不合作态度。好友山涛被任为选官,有意举嵇康代己,嵇康无意仕途,竟十分愤怒,以至写书与山涛绝交。嵇康的另一好友吕安被诬入狱,嵇康为之据理力争,司马氏乘机把嵇康投入大牢并准备处死。太学生三千人上书为其说情,司马氏不许。临刑前,嵇康面不改色,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时年仅四十岁。主要著作收入《嵇康集》。
(2)“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阮籍在《达庄论》中阐发了他的“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他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意为天地就是大自然,天地之内包含着万物,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天地之间的万物各色各样,但本质上又是相同的。“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在此,阮籍继承了庄子“通天下一气”的观点,指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非是“一气盛衰”变化的结果。
人与自然也存在着同一的关系:“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也就是说,人为阴阳之精气所构成,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为人之本,人应该与自然合而为一。
(3)“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追求
何晏、王弼提出名教与自然的问题。他们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二者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封建秩序是自然的秩序。阮籍揭露了名教的伪善性。嵇康则尖锐地批判名教,认为名教与自然是矛盾的,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才能够恢复淳真质朴的至德至善。
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出发,认为既然万物为一体,自然为一体,那么,儒家设名分、讲仁义、论是非等等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产生弊病的根源。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嵇康批驳儒生“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论调说:“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向之不学未必如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他们对于那些恪守封建名教的“君子”充满了鄙视之情。
他们进而对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和官僚阶层进行了抨击:“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人民,欺愚诳拙,……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这些思想与此后《抱朴子》中所记载的鲍敬言反对君主统治的无政府主张遥相呼应。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封建名教压迫下的痛苦灵魂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