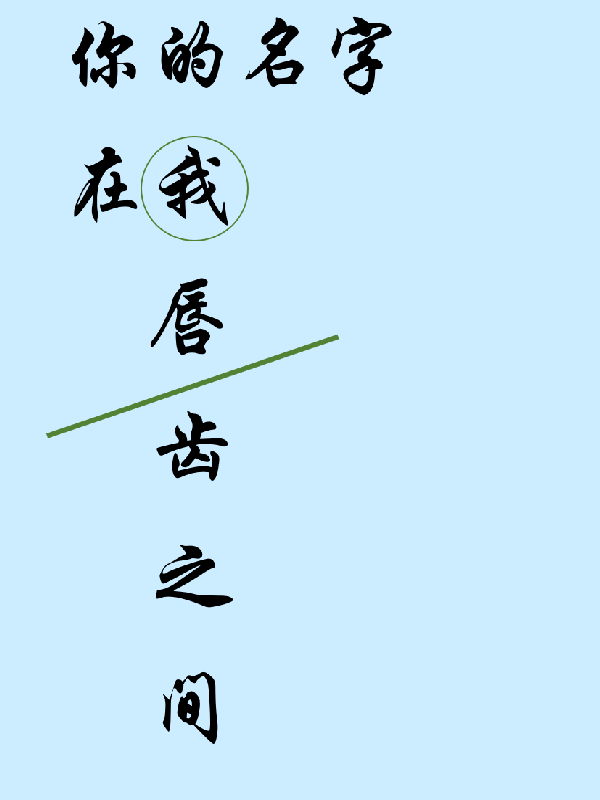云璞陷入了一片黑暗,而他昏倒之前心里想着,这小姑娘到底是谁,竟可以随意出入这地牢。
与此同时,辜老大带着星仔来到洞庭湖君山附近,等待云璞和四哥的消息,他们并不知晓云璞和四哥已经分开了。
这君山可是丐帮的地盘,也是星仔的地盘。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星仔就手痒得不行,非要赌上几把。
虽然还是腊月时分,但见画舫穿梭湖面,或赏雪赏景,或吟诗下棋,品茶饮酒,一幅烟雨江南,清新高雅景致、紧紧扣着悠游其间的过客行人。
只见得湖边西岸,正停泊一艘白色如玉的巨大画舫,瞧其三层高的雕梁画栋建筑物,直若一栋可移动之宫殿般那样奢华。
船头撑着一支旗竿,足足十余丈高,挂下三朵水缸大红色灯笼,写着“聚宝盆”三个黑大字。
任谁都知道,此船乃隶属于江南霸主袁晟。
袁晟,年约五旬。他出道江湖不到十年,即以一手聚财掌打遍江南六省未逢敌手,终也落个江南霸主的封号,这个封号可是连丐帮帮主都要敬上三分的。
十年前更被推为江南瓢把子,一时人面广开,相对的,开销也就大增,故而在好友建议下,便开此“聚宝盆”的赌坊。
一开就是十年,也未被踩过盘子。
这是其信用够,不诈赌,只要你有本事,多少钱,任你赢了即带走,绝不含糊,故而生意特别兴隆。
当然,想登此“聚宝盆”船,非得口袋装个千金不可,否则只有到江南六省的城巷中,那些较小号的分店走逍遥。以免蹲在这儿占位,干瞪眼。
尽管来此船者,大都非富即贵。
然而赌性张开,谁不是原形毕露,照样厮杀喝吼,声音甚至穿传数百丈,好端端地洞庭湖雅致也就全被破坏了。
尤其是第一层,乃是天九场之类的武场,一吼下来,可谓声如杀猪,掀天动地亦不为过。
还好,最高一层乃是麻将场,本有五间,此时却打通成一间,本是五张桌面,此时却收去四张,独留居中一张。
四个人分坐四桌角,周边则围了二十余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四位。
这第一位赌客则是个年约四旬的中年人,只见他一身青碧官服打扮,但差没戴乌沙帽,否则准十足像个县太爷。不过这也没有说错的,他可是苏州的知府老爷。众所周知,这人有要沾了官气,自然是喜欢摆阔的。
而第二位赌客乃是二十上下年轻人,且看他是一身白衣,上好的绸缎,一见即知这绝对是个纨绔子弟。再说了,他可是洞庭湖君山唯一首富李富贵的独子李罡。
明明长并不咋样,但他却放作风雅状,身边还带了一名妙龄妖艳的姑娘,时而挑弄逗笑。似毫根本不把这场麻将当成一回事。
这三位则是一位黑衣夫人。瞧她不过是徐娘半老,但风韵更是撩人,那殷红嘴唇老是微张微笑,向着周遭诸人笑,向着某特定男人盈盈媚笑。
她正是泠夫人,不知是何来历,老是以水汪汪般调情眼睛盯着对面那第四位穿得书生样子的年轻男人。
她频频浅笑对第四位男人,但他却莫测高深报以微笑。
这人看来像书生,但眼神溜处,又似狡猾无比的光芒。尤其模牌、砌牌那股自信,甚让人相信,他是个很难打败且难缠的角色。
其实他就是星仔,只不过想要上这船,非要衣冠整齐之人才可。这不,常常见云璞的穿着,他也学了不少。
也算是难得见他把那破破烂烂的衣服换下,不过,人靠衣装,这星仔穿上书生样式的长衫,还真是人模人样的。
如果常在君山这边赌场混的人,都会叫他一声“星哥”,以表示对他尊敬,或者可分点儿油水吃吃。
老实说,凭着云璞送给星仔那副穷酸般的素白袍,怕是没资格跟三位看来贵气冲天的大贵人相并而坐。然而在“聚宝盆”临时找不到人手,袁东家又不愿下场之下,只有把星仔给推上桌。
何况在泠夫人看中意之下,星仔也就大大方方坐上位置,准备大打出手。
牌已砌妥,位置也已选定,接下来该是谈赌金了。
那纨绔子弟李罡瞄了星仔一眼,黠笑地刷开白玉扇,扇着轻风,说道:“怎么算?公子我一向是用箱算的。”
一旁美艳姑娘娇笑道:“公子是说,他算元宝都是以一箱一千两算的,穷书生,你赌得起吗?”
虽然她说了“穷”字,但似乎对星仔并无恶意,毕竟像他那么俊男人不多。尤其那副满不在乎神情,总让人觉得天塌下来,他都不怕似的,姑娘只想看看他反应罢了。
星仔果然满不在乎笑了笑,道:“嗯……打牌……我好像从来没算过银子……”
当然也表示未曾输过。
泠夫人媚眼瞟来,轻笑道:“年轻人,你好狂?”
星仔笑道:“哪来的狂?我是说,我都是收银票,如此方便得多。”
泠夫人笑道:“你不怕输吗?输了以后,有人可能不要你的银票啊!”有意无意瞄了李罡一眼。
李罡轻笑:“谁知道他的银票,是不是自己伪造的?”
星仔向一旁站立如山的魁梧中年短须汉子,笑道:“是不是伪造的得问袁东家了,我的银票都是他开给我的!老实说,我打牌还没输过。”
想来李罡太过份,星仔也给他来个下马威。
李罡尚未开口,两旁妖艳姑娘已然动容欣笑:“你当真没输过?那不就变成赌神,家财无数了?”
星仔淡笑:“也许吧!”
李罡但见身旁女人倒戈,为别个男人赞言,脸面已挂不住。他冷喝道:“你行,那就一万两金子一把,如果你输了,袁东家你敢不敢负责?”
显然他不但表现财大气粗,亦表现赌术过人,当面向星仔下战书。
袁晟干笑道:“杜公子的银票自无问题,只是赌注要这么大吗?”
李罡冷笑:“我的行情岂只这些?玩不起,还是赶快走人吧!免得到时脱裤子都还不了债。”
袁晟脸色稍动容:“我是怕公子……”下一句“输太多”他未使开口,一时不知如何说下去。
李罡冷眼恼怒,冷冷地道:“怎么,你怕我输?我会输给别人?就算输,再插个花不就赢回来?我总不会把把输吧?附带说一句!”
转向星仔,黠笑道:“我打麻将,从来可以无限制插花,你行吗?”
星仔淡笑一声:“行。”
一旁从不吭声的知府老爷郑湃,此时已等得不耐烦,说道:“就一把万两,谁愿插花就插花,开始吧!打牌,桌上争输赢才是英雄;李公子你就杀他一个片甲不留便是。”
李罡重重点头:“有理!”头一甩,瞧那个嘴角长痣妖艳姑娘:“插花五万两花红。”
妖艳姑娘一愣:“我……我哪来这么多?”
袁晟道:“公子说了就算数,不必摆台面。”
李罡硬是耍派头:“第一次,总不便摆空,春香。把头上的彩凤玉簪拿下,我倒着看谁能赢得了。”
那叫春香的姑娘有点儿舍不得。但公子乃是首富之子,五万两算什么?他总会赔自己吧!于是当真把头上镶了不少珠翠的贵重发簪给取下,落落大方置于桌角。她笑道:“好吧!我陪公子助助气势便是!”
星仔瞧那发簪翠绿剔透,自知价值非凡,淡然一笑:“打个牌,还让姑娘破费,于心不忍。”
李罡斥道:“赢了再说,你押不押?大有不押即是穷小子的姿态。
当然,星仔一直都是个穷小子,不过,也许是穿上了长衫,这星仔也有正经的时候。他淡笑道:“我打牌从来不押花红!”
李罡正待取笑之际,围观者竟然开始哄动,大堆人喊着要插花,立即有人扛来桌子,置于星仔左侧角。
各自拿出似乎早就准备妥,且写好名字之布条,包着银子押在桌上,有的来不及准备,干脆把名字写在银子上,异口同声喊着要押星仔花红。
桌面堆出好高,看来少说也有万两之多,迫得袁晟叫来手下,找个大桶子装上,以免被人推倒而起纠纷。
如此情景,倒让在座三人感到意外。
三人先是一愣,但他们似乎经过大风大浪,随又立即恢复平静。
泠夫人笑道;“小兄弟看来真有过人之处,竟然受到那么多人捧场?”
星仔笑道:“大概我手气较好些吧!”
泠夫人笑道:“听说你叫杜星鹏,他们都叫你星哥?”
星仔笑道:“随口说说,没什么。”
泠夫人笑道:“我看有什么。这天下第一赌定下过赌之星的称号,你又叫星仔,星哥,看来你当真是大赌徒哩!”
星仔故意苦笑道:“状元考不上,无以维生,只好流落风尘,夫人见笑了。”
泠夫人笑得更媚:“是吗?你是这种人吗?”目光瞄向星仔左手有意无意露出之汉玉扳指,笑声不禁更媚了。
此时一旁群众已有人讪笑说着:“我们的星哥就是喜欢白板,你们别打就没事了。”
又有声音斥来:“你怎可乱说话!他们不打,我们哪来赢线?”
一个响头敲得那人唉唉叫痛,他仍尴尬笑道:“纵使别人不打,星哥照样能胡牌!”
这话听在李罡耳中,更是难受,他斥道:“哪来这么多烂杂人物?”
袁晟闻言,立即制止一旁的诸人不得说话,干脆把他们赶向星仔那头,以免落人口实。群众虽对李罡不满。但看在利字头上,也就聚了过去,暗地里却咒他最好把家当通通输掉,看他还能耀武扬威到几时。
袁晟始又问及在场四人,除了李罡插花之外,泠夫人和郑湃只表示志在玩玩,并未插花,
于是牌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