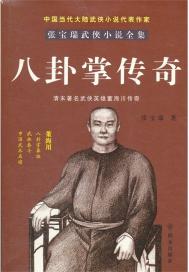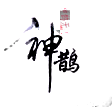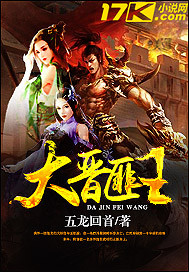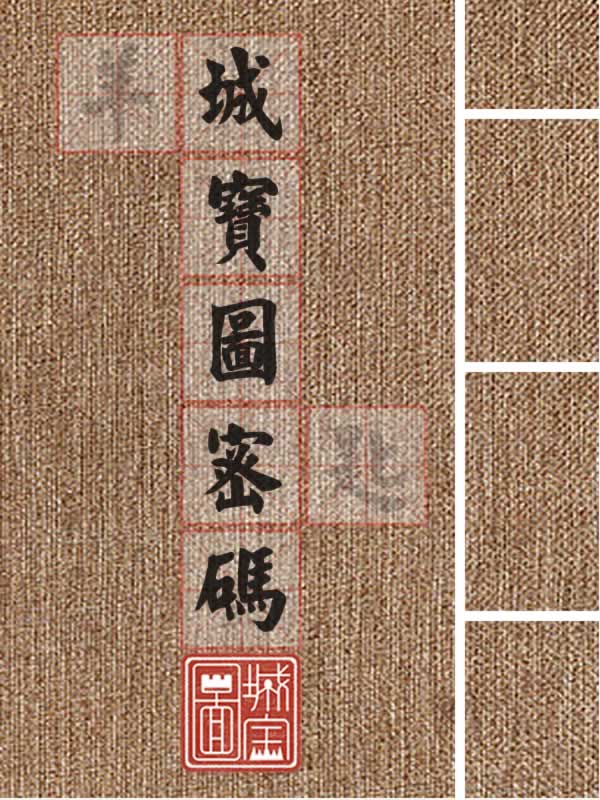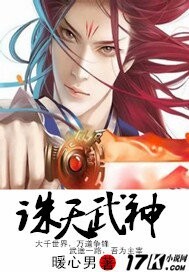原文
以疏间亲,宋有伊戾之祸;以邪败正,楚有郤宛之诛。斯乃暗主庸君之所迷惑,忠臣孝子之可泣冤。故藂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斯二者,危国之本。
——李世民 《帝范》
白话
离间亲疏的事例,有宋时有伊戾离间太子和平公,用邪恶势力败坏正义之人,楚时有费无极就诬陷郤宛的例子,这就是那些昏庸不明的君主,荒迷惑乱,所以有许多忠臣孝子被诬陷,实在是冤枉啊!兰花即使想长得茂盛,奈何被凄冷的秋风吹落。这就像忠良之臣往往被小人用谗言蒙蔽陷害一样;君王本来很想明察是非,但往往被小人蒙蔽耳目,不能成为英明之主。这就是奸臣、谗佞之人的危害。以上说的这两个方面,是倾覆一个国家的最大的隐患。
家训史话
晁错,颍川人,为人刚直而又严峻苛刻,他博才多学,善于分析,在汉文帝时期,他就官拜为太子家令,精心辅佐太子,并得到了太子的宠信。被称为太子的智囊。在这个时期,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就战争、充实边塞、农耕、爵位的封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帝对此也多有褒奖,以表示对晁错的宠信,并且采纳其不少的意见,以治理国家。
文帝去世后,景帝即位,晁错以其自己对问题的精辟见解仍多次地与景帝在一起进行单独的国政论谈,而且景帝仍能经常地采纳他的意见,并且依据晁错的建议,修改了许多的法令。景帝即位的第二年,便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
随着各诸侯王领地的不断发展和强大,一部分非嫡亲的诸侯王对朝廷越来越骄横,故此,晁错劝景帝说:“如今,削减他的封地,他会叛乱,不削减他的封地,他也会叛乱,如果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快,祸害会小一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反得慢,将来有备而发,祸害更大。”景帝让朝廷百官及宗室共同讨论晁错的建议,没有人敢与晁错辩驳。朝廷便根据晁错的建议对吴王等诸侯王的封地朝廷逐步的削减。
此后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晁错为名举兵叛乱。
吴国的丞相袁盎与晁错互不相容,于是伺机面见景帝,说:“吴王和楚王互相通信,说高帝分封子弟为王,各有封地,现在,贼臣晁错擅自贬责诸侯,削夺他们的封地,因此他们才造反,其目的就是共同诛杀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达到此目的也就罢了。现在的对策,只有先斩晁错的首级,派出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举兵之罪,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七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战争就会撤走。”景帝听后,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不会为了庇护他一个人而不向天下人道歉。”袁盎说:“我想出的只有这个计策最佳,请陛下认真考虑!”
过了十多天,景帝私下授意丞相陶青等人上疏弹劾晁错:“辜负皇上的恩德和信任,要使皇上与群臣、百姓疏远,又相想把城邑送给吴国,毫无臣子的礼节,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晁错应判处腰斩,他的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公开处死。”景帝批复说:“同意所以判决。”可晁错对此却一无所知。第二天,景帝便派人召晁错,欺骗让他坐车巡察东市,于是,晁错穿上朝服到东市巡察,结果到了东市就被腰斩了。
谒者仆射邓公从前线回来,向景帝上书分析回报战争的情况,景帝问他:“你从军中而来,听到晁错被杀,吴国和楚国的兵撤了没有?”邓公说:“吴王准备叛乱已有几十年了,早就产生了谋反的念头,吴王要杀晁错只不过是他举兵叛乱的借口,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错啊。再说,朝廷杀晁错,天下的士大夫还敢向朝廷进言吗!”景帝说:“这是为什么?”邓公说:“晁错忧虑诸侯王国势力过于强大了朝廷不能制服,所以请求削减王国的封地,从而尊崇朝廷,这本来是造福万世的好事。计划刚刚实行,他本人突然被杀。这样做,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我个人认为陛下不应该如此。”于是,汉景帝深深地感叹说:“您说得对,我也很后悔杀了晁错!”
古训今鉴
王者欲明,奈何馋人遮蔽。这是君王的一种无奈。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打的是“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幌子,晁错因此成了七国之乱的牺牲品。晁错为人性情耿直,忠贞不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品质,因此和其他大臣的关系处理不当。如果统治者想要知道真相,却被用心险恶之人蒙蔽,那么就会误断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