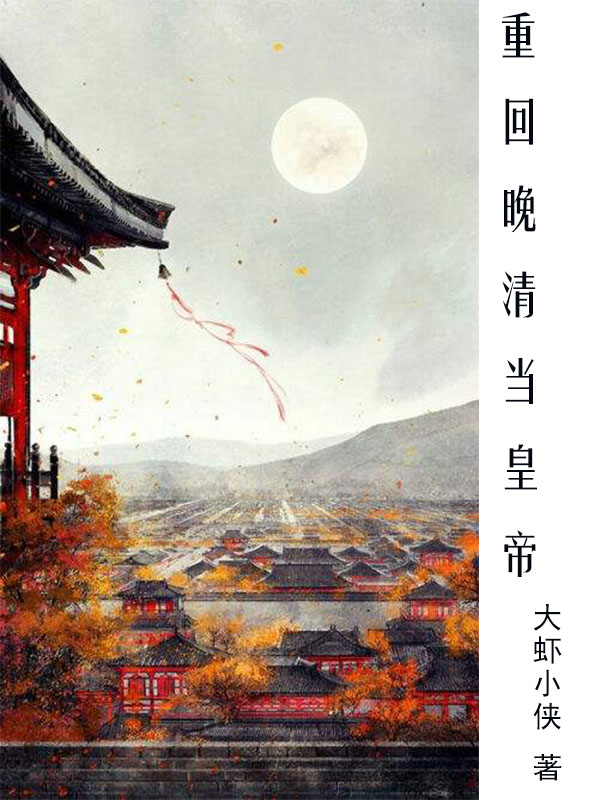连续三天的雨,断断续续的,将河北大地好好冲了个澡,洗去了银装素裹,浇出了草长莺飞。此时,这场大雨终于停了,在通往南皮的官道上,一行车马正缓缓而行。
马车内,大儒郑玄精神抖擞,他与孔融私交甚好,早年更是给刚刚启蒙的孔礼授过课,故此他接受了孔融的邀请,便一同随行入了朝。本来以郑玄的名望和身份在朝堂上谋个一官半职是手到擒来的,可是他求名而不求官,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在孔融的府中从事著书工作。
可自从去了长安以来,对于李傕郭汜二人的所作所为他实属深恶痛绝,更知大汉天下已是重疾难返,自此心灰意冷,遂托孔融找了份传旨的差事,借此来脱身。
一行人在黎禾进行了一天的休整之后,顺带着在周边几个城县转了转,说来平原战事才结束不久,可这里百姓安定,商甲熙攘来往,一片繁荣的景象,这倒让郑玄有一种回到了昔日和平年代的感觉,他很开心,更是欣慰,也许自己的这个学生真的可以托起大汉的一片天吧。
离开黎禾后,一行人又马不停蹄的向南皮方向前进。在经过阶泽要塞的残垣断壁时,郑玄不由驻足,虽一场大雨将这里冲刷了一遍,可是空气中那种焦糊味还是隐隐刺激着众人的鼻子。
一将功成万骨枯,郑玄曾几何时也有着兼济天下,再复大汉的宏愿,不料前路难行,只迫得独善其身,藏清于浊,将一壶酒水倾倒在地,终是长叹了一声。
“敢问可是康成公?”就在这时,一声爽朗的轻笑将郑玄的思绪拉了回来。
郑玄闻声回望,却见来人容貌儒雅,身高七尺,颌下有三缕黑须,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息,其身后跟着十多名披甲卫士。
“哦,是叔治啊!”王脩在北海为官多年,郑玄与他也颇为熟络,可是如今王脩身为青州别驾,大多时候应该在治所临淄处理政事,何故出现于此?但郑玄转念一想,便是脱口而出地问道,“怎么?又有战事了?”
“康成公一路辛苦了。”王脩却没有正面给出回答,上面笑盈盈地上前说道,“主公一收到康成公到了平原的消息便遣在下前来迎接,康成公,请。”
“多礼了。”郑玄见王脩避之不答,这才突觉方才自己的唐突,遂向王脩拱了拱手,也不再客气转身便上了马车,在王脩的护送下,一路向南皮前行。
途中,王脩与郑玄同车而行,王脩对儒学研究至深,二人自然是相谈甚欢,而王脩也趁机道出了此番的真正来意:“康成公今后有什么打算?”
郑玄先是一愣,而后笑道:“叔治真是好生奇怪,老夫是来传旨的,你不先问皇恩天命,却倒关心起来我这个半身入土、默默等死的糟老头子。”
“先生是过于自谦了。”王脩只是淡淡一笑,“以康成公当今的声望、地位,只要振臂一呼,这儒家的圈子里定会震上一震,况且我家主公也是先生的弟子,在青州的地界上,先生怎会无所作为。”
王脩这话只轻不重,郑玄曾入太学攻《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及《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之后,复客耕东莱,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家贫好学,终为大儒。又因与孔融交好,北海之下的儒家弟子大多也曾承他庭训,其儒家地位比之孔融也是稳压一头。
“哎,垂垂老矣,如风中残烛,此番离朝也就不打算回去了。”郑玄掀起帘子,默默看着道上的景色,语气忽变得伤感起来,“我这一生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到现在的少帝、献帝,大汉日渐衰弱,一路走来虽称不上颠沛流离,但也是饱经沧桑,此时此刻已是身心俱疲,得以埋骨故里已是上天恩赐。”
郑玄这番话无不显露出他的心灰意冷,王脩听在耳中,深有感触,微微颔首,随之一叹,继而开口道:“王朝的轮回更替必有定数,可唯有史册留其名,如今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康成公一代大儒,岂可惜身!”
郑玄摆了摆手,放下帘子,转头看向王脩:“不必想激老夫,老夫早已无心仕途。”
“非也。”王脩身子一挺,拱了拱手,说道,“我家主公曾言,大汉之祸并非党锢、并非张角、也非如今的军阀,其根源在于世家!”
“世家?”郑玄听闻一呆,这番言论他是闻所未闻。
“不错!”王脩正色言道,“我家主公说大汉糜烂,百姓从贼,皆应饥饿,百姓饥饿皆应无地可耕,而这些世家就是窃了百姓的地,更是窃了大汉的国!”
王脩一席话当得震耳欲聋,郑玄好似抓住了什么,问道:“所以玉伯才颁布了守田制,其本意就是打压世家,从根本上杜绝自东汉开国以来土地兼并的乱象?”
“不但如此,守田制的颁布只是其一,其二便要落在康成公的身上。”王脩微微颔首。
郑玄眯起眼睛,问道:“老夫能做什么?”
“有教无类!”王脩胸中豪气大盛,朗声说道,“我家主公要广开学堂书塾,这世间不是只有世家、贵族的人可识文断字,而是人人皆可教,人人可教即人人可学,人人可学即大众之学。”
“了不起,了不起!玉伯之胸怀、之远见更在老朽之上!”郑玄听得是热血澎湃,狠狠的一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脸色已由红变紫,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激动地说道:“儒学的意义本就在于将礼乐教化不分族类、不分老少向所有人敞开,实现有教无类!”
见说动了郑玄,王脩也不由笑了起来,只要将郑玄拉入孔礼的阵营来,那些儒家人才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孔礼的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