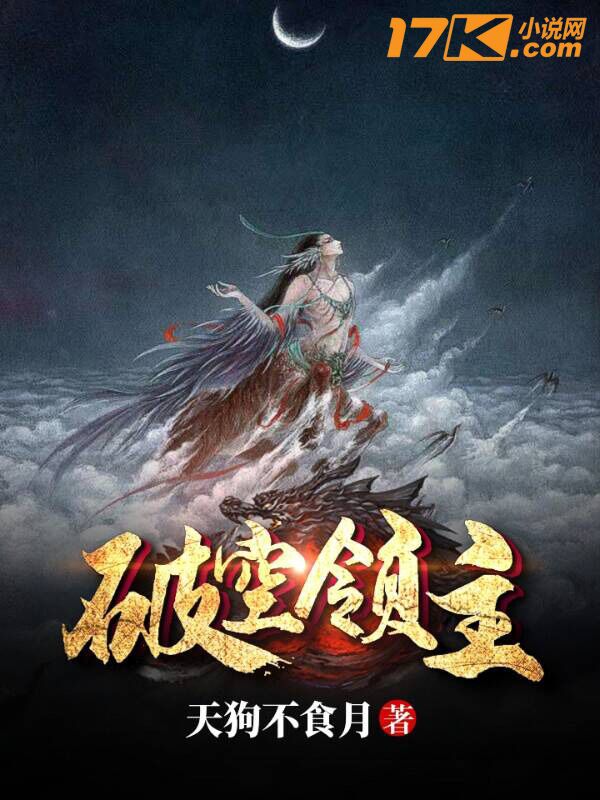只见蒋存尔突然推门进来,满身酒气,连眼睛都红红的,像在冒火华。他摇晃着身子,手上拿着一个酒瓶子,一屁股坐在卢益医生身边,指着印宏就厉声开骂起来:“你印宏说谁呢?谁是败家子,谁无德无才啦?难道你自己不是败家子,你自己就有德有才?哼,瞎话。”
他举着粗壮的胳膊,把酒瓶子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声音爆得吓人:“你小子,当过一阵子小助理,就要考核全国人民?你弄得集团上下,风声鹤唳,紧张得要死。你们集团效益突突下去,也不自醒自明,自己抽自己?其实,你是一个什么家伙,几斤几两,号呼靡靡,难道我们不知情底?说句老实话吧,你放一个屁儿,我都知道不会是香的,肯定奇臭无比。”
“哈哈,”印宏大笑道,“你蒋经理说话真逗,放屁难道不是臭的,还会是香的,奇香无比?哎,你这二郎神的架子,也未免太大了吧?怎不打个招呼就闯进来,是谁批准的?这是我的办公室呀,你难道不知道?私自闯入,违法犯法,在国外可以一枪毙命。”
“呵,”蒋存尔用眼睛瞪他,“我进来,还用谁批准吗?”
“那必须的呀。”印宏仰脸说道。
“哼,我进屋还用谁批准,笑话?你也不去打听打听,在松冲镇,谁家的门槛,敢不让我进去?”
“你再胡再蛮,再不讲理,也得讲个进门礼貌吧?”
“你在背后骂人,就是讲礼貌了?手电筒直照别人,不照自己。”
“那是你不在场,我顺口瞎说的,怎能认真?”
“不在场,就更不能骂人了。在背后捅刀子的,那叫黑里损人,比明的更黑,是最不礼貌的。”
“你砸桌子算礼貌?”
“你骂人算礼貌?”
——两人打起口水仗。一时间吐沫四溅,尘埃飞扬,分分不休,秒秒不让。蒋存尔得理不饶人。印宏悖理不屈人。卢益医生见了,连忙站起来圆场:“印宏啊,是我让老蒋来的,你不要见怪啊。他这人啊,说话一向岔得很,不着调儿,没谱儿,是一个没心没肺的酒鬼。今儿,大概喝多了,酒话也就多啦。你大人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就多担当点儿嘛。”
他又转身对蒋存尔说:“蒋副经理,你怎么又喝酒啦?你这样不约束自己,到处得罪人,让我难堪,小心集团董事会将你撤职。”
印宏则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看得出来,蒋经理今儿并没有醉,是对我意见大得去了。他在借酒闹事,想拆我的台。”
蒋存尔露出不屑神情:“是有意见,是想拆你的台,怎么样?老子明人不做暗事,这儿是老子的地盘,是你能随便吆喝的?你把我们吆喝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啥意思?你也不想一想,你能在这儿坐着说话,是我蒋存尔给的面子。如果老子说一个滚字,你就得立马扯铺盖走人,没有什么价钱可讲。”
印宏站了起来,也针锋相对:“耶,这儿是我管辖的领地,怎么成了你的?你睁眼看看,外边的天是男的,还是女的?这酒家挂着的牌子是酱色的,还是粉色的?华中绿豹集团千佛山项目临时办事处,我是办事处的主任,怎么成了你的地盘,笑话,大笑话。你问问卢益医生,他敢这么说是他的地盘吗?”
蒋存尔借酒仗气,上来就猛地推搡印宏:“还是滚出去吧,你的地盘?你问问,到底是你的地盘,还是老子的地盘?滚出去,再不滚出去,老子就要动手啦。”
卢益医生起身阻拦:“哎,老蒋,怎么动粗起来了?有话好好说,我们不在乎这一分一秒。你快放手,快放手啊。”
蒋存尔不给卢益医生面子,推开卢益医生,蛮横地继续推搡印宏,一直推搡到门边上,并大声地叫道:“老子在这里耕耘了十几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子辛苦扒拉出来的。这里就是老子的地盘,谁来摘桃子都不成。今儿,容忍了你们,来日谁容忍我们?我背后有成千上万的贫下中农,你们这些人,要他们断炊断粮,断了生活的根本,那怎么成?这口气,老子到死也咽不下去。”
“老蒋啊,”卢益医生走过去,婉言相劝,“印宏他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绿豹集团;他有护官符。我们不能动他。”
蒋存尔从鼻孔里哼出狠劲儿:“怎么,不能动他?老子今天偏要动他,看他怎么着?”说着,挥起拳头就跃了过来。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印宏被推搡了几下,已经很没面子。此时,又不便在关键时刻弄出栀子花絮,只好转身退出房间,随手将房门反手关住。
在下楼时,他听见卢益医生在上面训斥蒋存尔,声音很大很亮,分明是让印宏听见。印宏在心里嘀咕:“哼,一丘之貉,道貌岸然。却要装好人,演喜剧,唱二人转,把我当傻子啊?”
印宏感到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