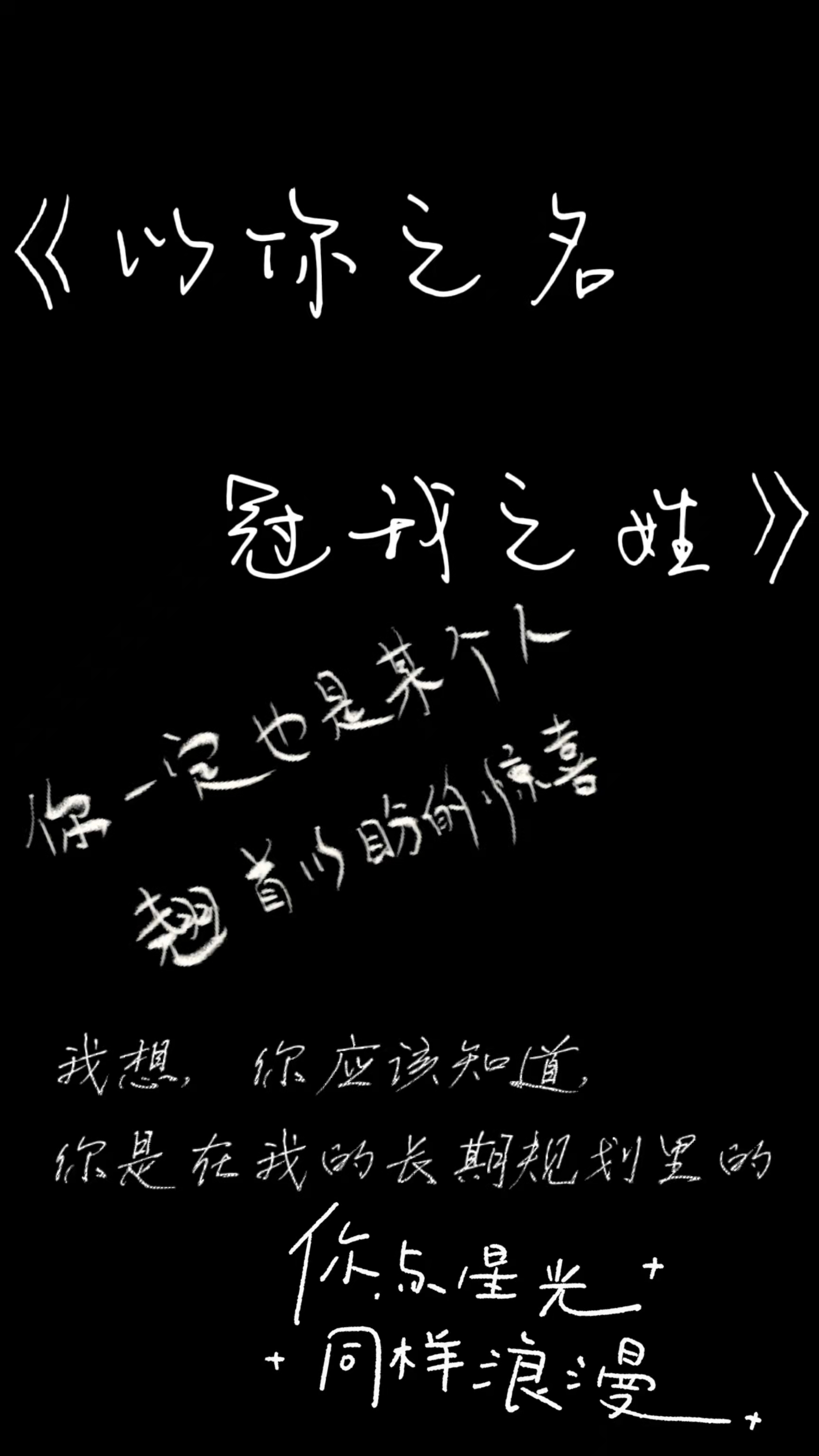水波有点犹豫不决地说,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他具体的地址。你知道,柳树本身就是个不确定因素,善于神出鬼没,大家喜欢他制造的惊喜和出人意料。对了,他去的是一个相对保密的部队,不可能公开地址的。我也只能看情况行事,通过市委的关系,找一个渠道,或者找一个熟人,或者是想方设法,绕过检查。总之,都是用一些不可靠的手段,做一些不太靠谱的事情,怎么可以连累你呀!
叶子天真无邪地说,这些你真的可以办到吗?柳树在离开的时候,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吗?
水波说,当然说过,他雄心勃勃,立志好男儿志在四方,做出一番大事业来。他要做中国的巴顿、拿破仑,说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说到这里,水波看出了叶子失望的表情,知道自己的表达与善意非常的失败。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吃柳枝拉柳筐——肚里编”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觉得自己有点堕落了,能够在心爱的人面前说谎不用打草稿,可是他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真诚。
就说了这些吗?
是这些呀!我们到一块除了吹牛还能说些什么呀?
我是说,这一年来,他都到哪里去了?
水波偷眼看了看叶子,又动了恻隐之心。他试探着说,这么长时间相互没联系过吗?
叶子略有所思地将头摆了几下,似摇非摇的作为回答。
水波小心翼翼地说,你走了以后,他就到了一个山区插队,然后就……
屈指算来,虽然只是短的几个月,在人生的长河中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对于叶子来说,却经历了断壑似的跨越。她隐忍了许多,身心的创痛和艰苦的环境,使她承受了多重的磨难,既有死里逃生的惬喜,又有无法排解的忧怨。她之所以能够熬过来,都是信念的支撑。当身心极具脆弱,忧愤难解无力支撑的时候,她仍然相信爱的力量,把伤害诠释成一种切实的表达,尽管非常的害怕未来。可是那荡人心魂的笛声早已写满自己的天空,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那个爱恨交集的身影也乘着笛声的翅膀油然而现。可是她却没有想到,柳树会不辞而别,绕道远去,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有。是失忆了?忘记过往,忘记给予她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碰撞?忘记那道在她心中和身体上留下的印痕。难道他大脑中充当内存卡的“海马体”失去了转换功能?或者是大脑皮质中的神经元有了异变,无法形成持久的网络?拒绝认可所有的转换的信息。她更害怕的是,自从那天运河岸边发生了不堪的事情,海马区选择性规避风险,逃脱责任,对其所发生的一切,作了系统的删除,或者残忍的格式化。假设这些都成立的话,所发生的一切已不复存在,为何还要掩胳埋胔,到远远地保密单位工作,岂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水波说,在柳树家,你也没听说什么吗?
叶子当然想打听柳树的行踪。可是之前发生的事,让她无地自容,柳家人只字未提,她又怎么好意思开口询问,纵使想问,人家也未必说呀?这些话她只能憋在肚子里,却不敢向水波吐露半个字。
水波有点生气地说,沈阿姨什么也没有对你说吗?
叶子天真地说,是我没有问。
水波无可奈何地说,叶子,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你们两个分别了八个多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
叶子呈现出狐疑的神态,张了几张嘴,却无语。
水波自言自语地说,世事难料呀!
叶子不解地说,水波,你真的让我莫名其妙。你们两个既是好哥们,不要再斗了好吗?
水波说,叶子,你写封信吧,明天的这个时候交给我,千万不要错过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