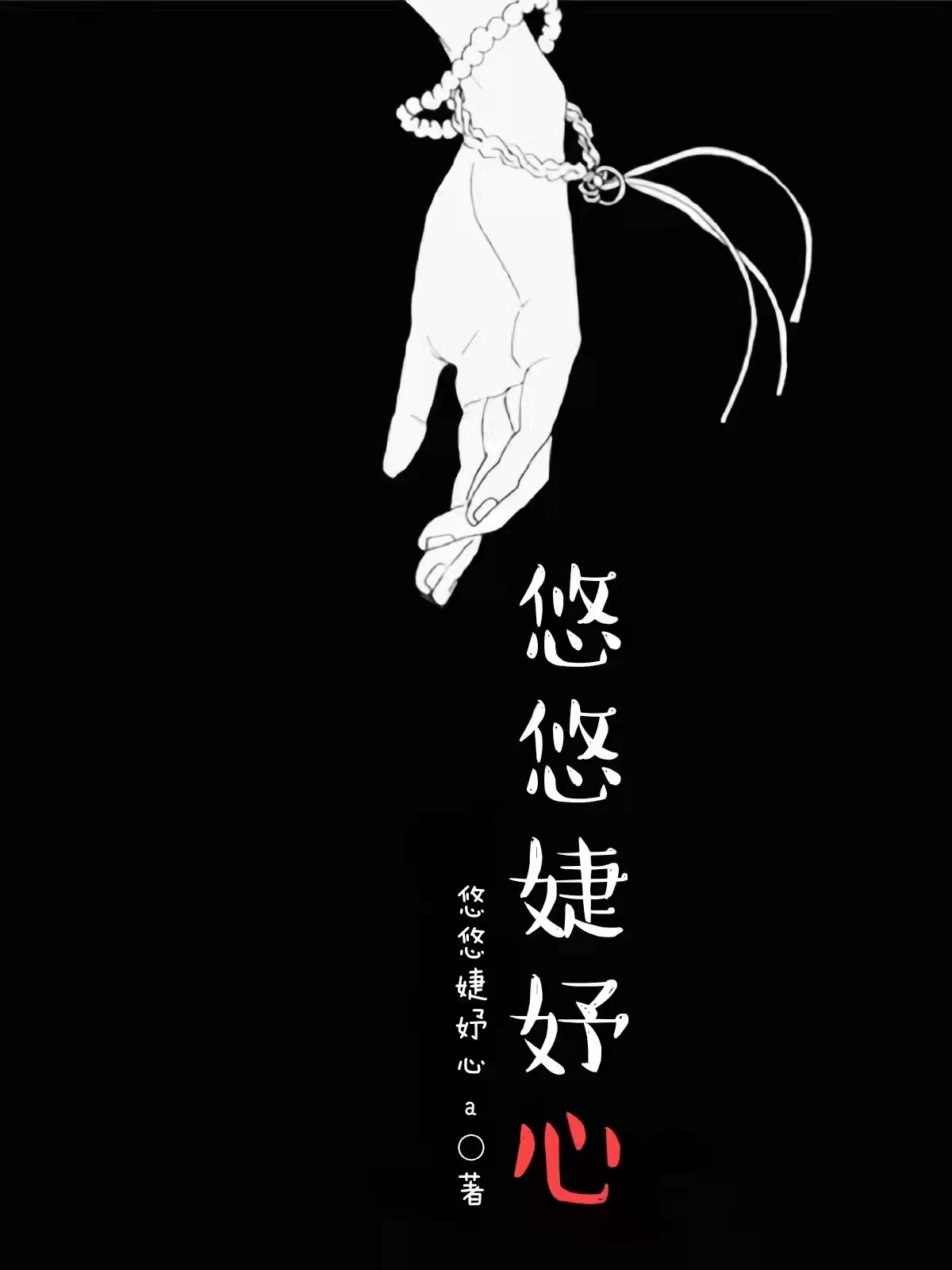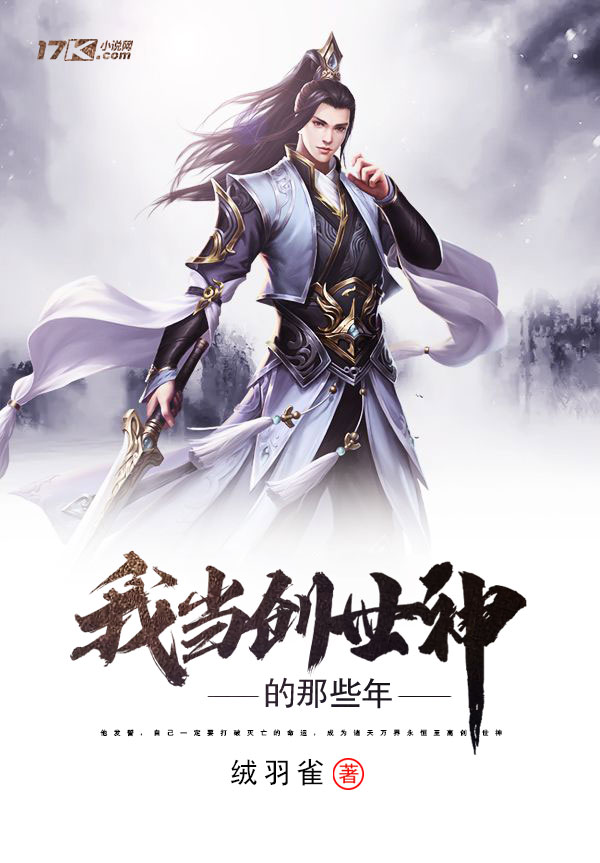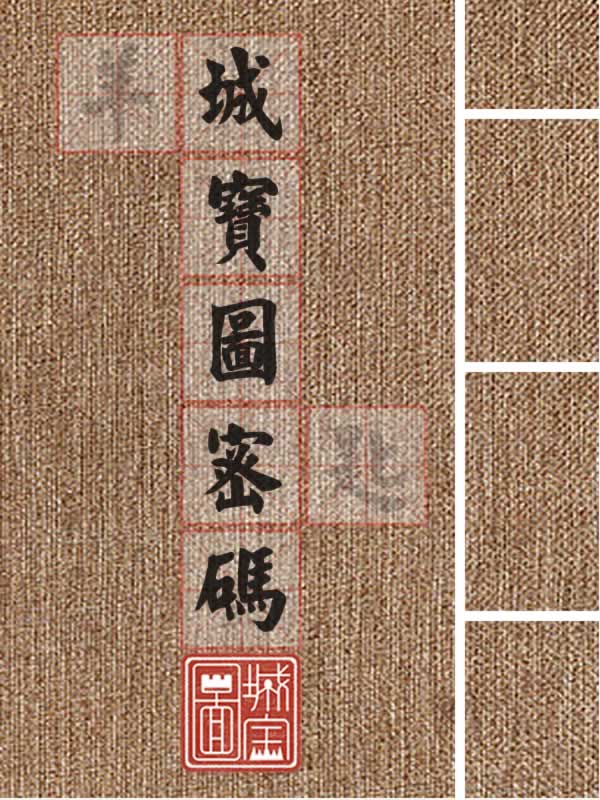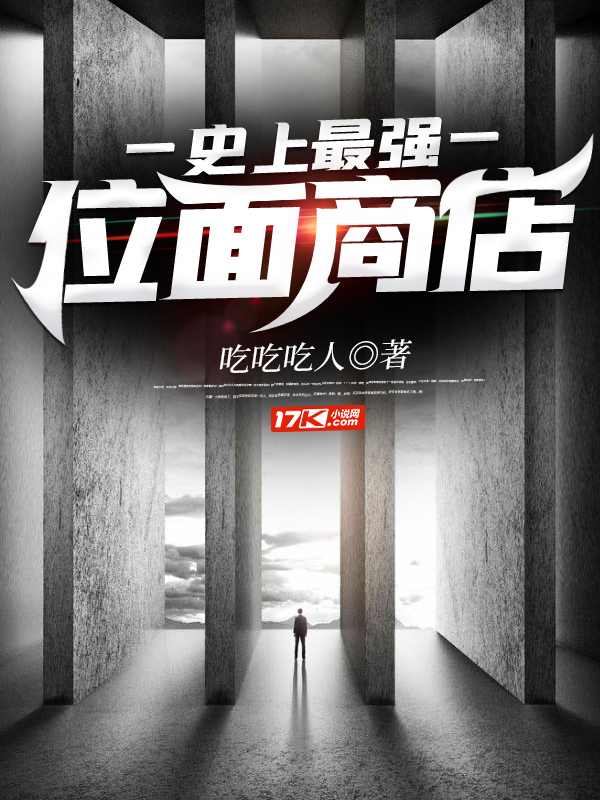叶子的外公是一位民主人士。
所谓的民主人士,“是对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而又具有****历史的知名人士的称谓,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爱国民主分子,以及一小部分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分别在不同领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声望。
老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笃好读书和崇尚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书卷气和文化氤氲,讲究的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家风。自明末清初以来,便是有文化有地位的殷实人家。其家族不但拥有较多的书籍,还把读书作为陶冶性情、家族的传统、家族的象征。正是因为有了“特殊家庭环境”的熏陶,教育出来的孩子才会变得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气质高雅。
老先生曾经留学日本,信仰三民主义,由于家庭出现了变故,回国后一直打理家族事业。抗战期间,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却也为抗战将士提供过不少的物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积极参与公私合营、土地改革,在民主革命时期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取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人民政府成立了,他进入统战部门,协助分管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
叶子就是在这环境出生并长大成人的,她满满的自信来自家庭教育和熏陶。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曾经留过洋,具有严谨认真地治学态度。
外公光明磊落宁折不弯的性格,不单单影响了她的妈妈,同时也作为遗传因子渗透在叶子的骨子里边,造就了她孤傲而又倔强的性格。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往往在是非面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幸的是,在讲究社会关系的年代里,运动的非常时期,外公总是处在敏感的风口浪尖之中。无论是反右,肃反,还是社教运动,都无一漏网。因此,外公是洪洲市著名的“运动健将”。皆因外公对解放事业有一定的贡献,又是拥护党和人民的开明人士,每次都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可这次运动史无前例,来势凶猛,连市长省长乃至于中央的老革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更何况他一个出身复杂的民主人士?
就是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叶子的全家,搬出了在洪洲城。
虽然生活相对的平静了许多,但是随之而来的困难也接踵而至。生活的困难还勉强可以解决,就是这政治上的待遇,是无法左右的。此时,叶子的父母并没有因为运动停止自己的工作,更没有泯灭远大的理想。他们仍然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在沙漠的边缘地带创建了中国乃至于世界上第一个绿色保护组织。名曰:沙漠绿洲。就在他们为了理想,为了未来日夜奋斗的时候,一场罕见的沙漠风暴夺去了两人年轻的生命。
叶子成了孤儿,与年迈的外公外婆相依为命。
生活的落差,丧失父母的创痛,在叶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宋朝的大诗人苏轼,在《和董传留别》的诗中写道:
粗缯大布裹生涯,
腹有诗书气自华。
厌伴老儒烹瓠叶,
强随举子踏槐花。
囊空不办寻春马,
眼乱行看择婿车。
得意犹堪夸世俗,
诏黄新湿字如鸦。
李老师发泄私愤的一席话,无疑戳到了她心灵深处最痛的地方。多少年来尽管她努力从悲痛中走出来,跟外公外婆学会了坚强,随遇而安。而她一个孩子,仍然在心灵深处,埋下了创伤。她无法承受的太多,特别是这种无理的指责和屈辱。
她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来面对当前的局面。她多么想逃离这个环境,远远地去舐试自己的创口。可是她不能,她要接受正规的教育,像爸爸妈妈,像外公一样有知识有抱负。她想更加深刻地认识天和地,认识整个世界,做一个像爸爸妈妈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有理想的孩子,虽然没有说出口,却缄默于心。她向未来的叶子承诺,一定会苦苦守候梦想和信念,直到实现的那一天。
歧视和误解卷走了她的笑容,却不能湮没自身的聪颖和漂亮,缺乏雨露滋润的花,虽然让花瓣失去了光泽,可夺不走内心的强大和对未来的期许。跟随外公外婆生活的日子里,让她学到了很多,她也更加喜欢儒家四圣之一曾子的话,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努力属于内部、可控、不稳定的因素。为何可控的因素不稳定?自己能够做到的是努力,可控的是自律,其他的因素都属于客观存在,无法改变更无力把控。
每天上课时,她两眼直直地望着黑板,不敢再发出什么别样的声响,特别是上语文课,她更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唯恐不慎再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
水波仍然不失时机地表现着自己,每次的表现总是愈演愈烈,且总是有叶子在场。时间长了,这便又给那些欣赏水波的女生们以口舌。有人说,水波是故意在叶子面前出风头献殷勤。还有人说,是叶子勾了水波的魂,叫他魂不附体。更有甚者说,小资施了魔计,毒害革命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