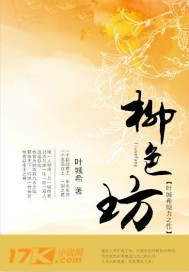祁树从石桌旁的水池里舀了水,注满了水壶,然后把炉火燃起,把水壶放了上去。做完这些,他舀水蹲在一边洗了洗手,然后在石桌前坐定。
他看见公仪敏在一旁站着,看他做这一切,便问:“敏城主,怎么了?”
公仪敏的脸上,露出一丝尴尬,说:“我原以为,这水池是专门用来洗漱的……”
祁树似笑非笑看着她,说:“所以你每次习完武,就直接伸手在里面洗脸洗手?”
公仪敏点了点头,嘟囔说:“这几天,我都——这水还能饮吗?”
祁树哈哈笑道:“没事,就算是你在此洗了澡也没有关系,这水是活水。”他一向喜欢占些口舌的便宜。
“活水?”公仪敏有些不信。她上前查看,才发现水池底,一边在汩汩冒水,而另一边,却似有缝隙,有水不停地往缝中钻。奇就奇在,这水池的水,居然可以一直维持在同等的水平线。尽管刚才祁树舀了些水,这水也不见明显减少。
祁树看着公仪敏,说:“人的智慧,不得不让人称奇,是不?只有肯花心思,什么样的奇思妙想都能实现。”
公仪敏回到石桌前坐下,说:“你知道,这是谁设计的吗?”
祁树略一思索,说:“依我看,应该是公仪夫人出的设计。据说,这之前明着是宾丘贾在主事,实际拿主意的是公仪夫人。当年,锡城重建,也是公仪夫人出的银两。我看这锡城的设计,处处透着精妙,定是一个奇人所设计。观世人,有玲珑心的,只有公仪夫人而已。”
公仪敏一惊,说:“照这么说,公仪夫人对这锡城了如指掌。依你推断,这里会不会设有直通外面的秘密暗道?”
祁树笑着说:“你别担心。上有命令,下有对策。即使是公仪夫人出的设计,真正建城,却由石老将军负责。以石老将军的老谋深算,他怎会将锡城轻易置于一个外人的股掌间。就算当时设有密道,这会也定被石老将军堵住了。”
公仪敏一愣,说:“外人?想来,我公仪敏也是外人。要不然,他怎么不将这里有秘密院落的事,告知我。”
祁树敛了色,说:“敏城主,你就是过于沉迷于人事。他人是否待你真心实意,确实很重要。可是,这不意味着他人就得事无巨细都和你禀告。我刚才看,那院落没有什么奇异之处,除了破烂,堆满文字。看那设计,应该之前那里是旧城的宅子。有人被禁在里面多日,人数至少有三人。这是丑事一件,石老将军如何无缘无故和你谈这些?”
公仪敏被祁树教训了一顿,笑了,说:“祁树,你真是人小鬼大。”
祁树撇了撇嘴,说:“好像你自己很大似的。说白了,你自己不还只是个小孩,情绪化严重。遇见一点开心的事,就乐得呵呵笑。遇见不顺心的,就搞得活不了了似的。别人对你好,你就想着要去回报。别人对你不好,你就想着为什么对你不好。就因为你公仪族人大公无私。天底下的人,都得对你们这些公仪族的人掏心掏肺。”
公仪敏怪叫道:“祁树,你何出此言?我何时讲过这样的话?”
祁树没有理公仪敏。水壶的水开了,他为两人重新沏了杯茶。完了还站起身,重新给水壶注满水,放在炉火上。
看着祁树慢悠悠的样子,公仪敏越发气恼。她咆哮道:“祁树,你不能说话只说一半啊?!”
祁树重新坐回石凳。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水面上浮着的茶叶,然后抿了一小口,悠悠说:“都是一城之主了,还如此沉不住气怎么行?我既然开了口,试图一吐为快的人应该是我。你该耐着性子,淡然坐着,等我发泄才是。哪有人,着急找人说教的。”
公仪敏深吸了两口气,平复下自己暴躁的心。她端起茶杯,闻了闻茶香,说:“这茶叶不错,颗颗饱满,茶香沁人心脾。该是今年的头一批茶。”
祁树笑着说:“孺子可教也。茶树经过一整个冬天的积蓄。当春天来临,它终于迸出了第一颗嫩芽。此芽饱满,富含养分。此后,茶芽一次比一次单薄,直到下一个秋冬的到来,停止吐芽。如此周而复始。”
公仪敏叹道:“果然万物的盛衰,都是周而复始。我公仪族建城千余年,想当初何等豪气云天。到了今天,我父亲连个儿子都没有留下,难道到了灭族之时?”
祁树苦笑一声,说:“公仪敏啊公仪敏,你怎么如此悲观了?遇见任何事,率先转起的,都是不好的念头。”
公仪敏喝了口茶,沉默不语。心却一惊,难道自从家里出事后,自己的性情也变了?记得小的时候,心头何时转过不好的念头?
祁树说:“我只是想说,做任何事情,没有一定的积蓄是不行的,尤其是打仗。而如今,莘城已经积蓄够多了。一则,千年未有战事,没有破坏,每户人家都有丰厚的家底。二则,当年朗城主惨死,连累了不少的人家,每户家中都持有‘报仇’的狠劲。三则,如今莘城人才济济,大家都想施展自己的才华……”
公仪敏没有想到,祁树会说出这些话。这明摆着,是劝战。可是公仪族的祖训,就是万事和为贵,人人安居乐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公仪敏打断祁树的话,说:“祁树,任何战争,都避免不了伤亡和破坏,带来无尽的灾难。如何可以,我宁可选择拱手送城,也不愿我莘城人面对无尽的生离死别。”
祁树笑了,说:“想不到,你父亲把你教得如此好。当年,你不满十岁吧。居然把这些大道理,都教给你了。看来,你父亲真的是把你当下一任城主来培养的。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了。就算你想安稳度日,公仪夫人会答应吗?就算你想拱手让城,莘城城民会乐意吗?你已经无路可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