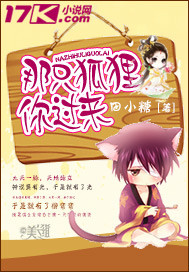他们所有的衣衫都被浸泡在绠老爷家的的木盆中,木盆中的菘蓝,在水中弥散着好看的青蓝色。
“这几件锦缎的长衫,想法去街市上换些碎银,储二孝无需讲价,能换多少,便换多少,切莫争执。最好,换给那些到街市上兑换土特产的山民。”
“山民?这些山民哪里能要穿这种上等的锦缎。再说,他们哪里会有碎银?”
储二孝嘴里嚼着一根菘蓝,不解地问道。
“可知这土货,也可兑换碎银。只这锦缎拿在手中,就是祸端。”
见阚鹤如此一说,储二孝点头说:“如此,天一亮,便去街市。”
储二孝将手伸进木盆,翻了几下盆中衣物,都已经上色的衣衫,浅了许多,都成了水蓝,也还算是鲜亮。
“可以挤干了,烘烤了,这烘干了的,颜色会加深一些,当比这水蓝,更适合男子穿戴。”
储二孝将盆中衣衫挤干了,挂在长凳上烘烤。
“阚贺,你身上这身素白,为何不脱下上色,留这一件素白,可不还是“寿衣”?”
阚鹤下意识地将自己的衣领拢了一下。
“无妨,这水蓝色的套在外面,当色差比对,更加好看。”
衣衫滴着蓝色的水滴,在火塘边冒着白雾气,储二孝跟阚鹤说:“阚鹤,可知适才到绠老爷家仓库,我看到了何物?”
“何物?”
“别看绠老爷这把年岁,这方圆几十里,还真没人跟他比这稳当当的生意,当然,这眼红的可不少,都是做了皮子生意,有了本钱的,还有那皇家染局的,他们有权势,好像找过绠老爷几次麻烦,听说盯上的还不止绠老爷的这生意,还有他的家当。只绠老爷现时的,哪有心思跟他们谈这些。”
“哦?绠老爷除了你说的仓库,哪里会有多大的家当?”
“看见没有,这半边的山头,便都是绠老爷家的,适才看到的那狗,是看家护院,还看羊的,他们家马棚里的马,就有上十匹,还有三辆上乘的马车。”
不止这些,他家还是宫里的御药房的采取点,收购山民药材,还到外地进名贵的、稀缺的药材,可人家说这是门“绝户”,几房妻妾,不生养,只得抱了个女儿,可这女儿都十八岁了,也没人敢娶。”
储二孝小声地说着,又自己轻轻地咳了一下,接着又说:“这姑娘自幼抱来,就有个怪病,腋下有个小‘洞’,每年入夏就害,绠老爷只得带着她到这深山里来避暑,可这‘洞’却随着年龄增长,越害越深,还流脓水。”
“哦?这十几年在身上的‘洞’,越害越深,本宫,哦!不,吾去看看。”
“哎!哎!阚鹤,万万不可!且莫说男女授受不亲,只你这医术,别还没进村子,便被人轰了出去。”
绠老爷出来了,一脸苦相。
“这么晚了,你们歇着吧!老夫也疲惫不堪了,要躺歇一会儿,唉!腰酸背痛。”
“爹,疼啊!爹——”
女子一声接一声的shenyin 声传来,阚鹤实在不忍,便起身想到近前去看看,却被绠老爷拦住,严厉喝道:“这位小哥儿,老夫好心留你等避雨,万不可毁了绠家女儿的名节。”
阚鹤浅笑。
“绠老爷,吾可是跟了高人学了医术,只……”
“阚鹤——”储二孝也过来拉扯。
“疼——疼死了!”
女子shenyin声揪心。
“小哥儿,当真懂得医术?”
阚鹤只点了点头,便掀起门帘,进了房内。
房内已是满屋青烟缭绕,几乎看不清物件,只闻女子shenyin,却不见女子身影。
阚鹤闻声寻去,走到近前,见榻前一堆野蒿草熏过的灰堆,还冒着点点火星,女子上半身几乎悬于床榻和一把坐椅之间。
老者忙过来点亮松油灯,只见女子脸色惨淡,精神萎靡,那被熏的腋下浓水欲滴,如此,女子还要顾及羞耻,白色的长衣衫,也只在腋窝下,剪开一个洞口,任脓血,缓缓滴在蒿草的草堆之中。
可见,这顽疾折磨的女子,已骨瘦如柴。
“府上可有尖锐之物?”阚鹤看着女子的伤口,问道。
“有,有。只此物便是她娘的银簪,多时未用了。”
“无妨。拿来一用。”
“阚鹤——”储二孝担心地喊了一声,阚鹤没有应声。
伸手接过绠老爷递过来的银簪。
“再去端一碗滚烫的盐水来。”
“这——”绠老爷有些犹豫。
阚鹤想着前世见过这种长在腺体上的脓包,可这在几千年前,这种要用草药,还加了硫磺熏治的,还是头一回见,而且这种熏治,也只会让表皮的收缩,里面继续拱脓,哪里能将里面的腐脓熏出。如此下去,内间的腐肉只会越烂越深,甚至重度感染,致人命丧。
“绠老爷,现在若能弄到这些药材,便速速取来。”
绠老爷接过阚鹤写的方子,只见上面写道:鲜地丁、黄柏、白癣皮……忙应着:“哎!哎!有,有,都有的呢。”
只一会儿,绠老爷便将这些被晾晒的干蹦蹦的药材都拿了来。
“好在,这里还有些外出外伤救治的,做了备换的都是新进的好药材。”
“好,现在去拿些香油来。”
“香油?”
“阚鹤——”储二孝又喊了一声,绠老爷也迟疑了一下,看了阚鹤一眼。
阚鹤只低头将银簪子放进滚烫的盐水里,认真地来回晃着簪子的尖部,谁也不理睬。
绠老爷将香油端来,阚鹤将药材放进适才他们进来,就看见堂屋里放在的一个大药捻子里,将药材碾碎后,与香油调整成糊状,几人都关注着她手中搅合的糊状药材,却不想,她端着药碗,蹲下查看女子腋下包块,放下药碗,便将手中银簪猛然插进女子的腋下。
“啊——”
女子一声惨叫,将两个娃娃从梦中惊醒。
“娘——呜呜——”
“娃乖,不哭,不哭!阚鹤——”储二孝连连喊了两声,阚鹤还是不予理睬。这是阚鹤多年来,临床养成的习惯,一旦找到病灶,便投入忘我。
绠老爷见女儿虽是腋下的蒿草灰里,飚出的是一堆脓血,可女儿惨叫后,已痛的昏厥过去,便跳起脚来骂道:“煞医,你这煞医!怎可如此下手?女儿,女儿啊!爹不好,是爹糊涂,怎就信了这‘煞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