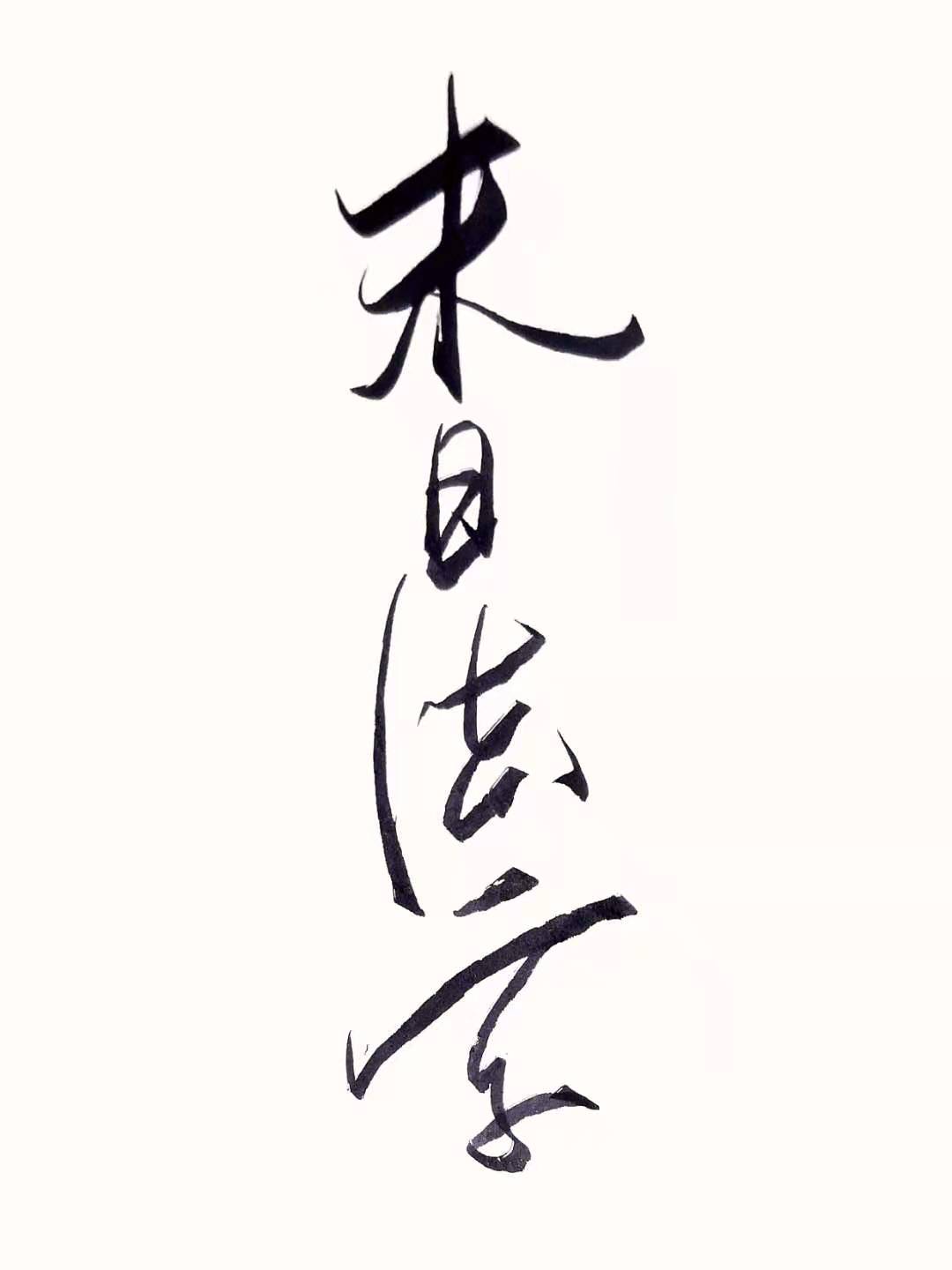我的名字叫杨鹏,一个十八岁的中小学生,新学期开学就上初三的乡村学员。
本来我们的生活开心的像夏季外伸嘴巴的狗,但自打星期六晚上我闲得蛋疼去看看广场舞后就越来越不好了。
那一天是星期六,晚饭后早已对广场舞执迷不悔的母亲火烧屁股般走出去跳广场舞了,爸爸领着五岁的小弟大约出来 散步了,家中就剩余我一个人。
我那一天由于晚餐吃得多了点,不喜欢弹出,就躺在土炕无趣地看一本小说。
这也是一本有关倒斗的书,书本上这些压抑感的描绘要我看见看见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扫了一眼空落落的家,又看一眼窗前擦黑的天,我认为我还是出来 比较好。
我将书一扔锁住了家门口便向村口的广场跑去。
天刚擦黑,村内的街道就静得十分,龙川县日爱叫的狗都没有了气息。
在快到村口的情况下,天逐渐雾大,浅浅的雾从地板上慢慢漂起,把前边的路弄得模模糊糊的。
一阵风从我身旁飞过,滴溜溜地漂了以往,路边的落叶刷一下地响了两下,听在耳朵里很难受的觉得。
夏季的夜里是归属于广场舞的時间,在广场舞盛行全国各地的情况下,大家这一叫韩家的偏远小山村也被蔓延到,这些平日拿长刀铁锹的乡村妇女好像一夜之间看到了自身的跳舞天资,陆续化眉画唇摩肩接踵,并迅速就舞动了瘾头,村口的那片闲置不用的广场当然就成为了他们神魔乱舞的演出舞台。
前边逐渐有背景音乐的声响传出,广场里早已欢歌笑语,而周边早已围了许多一个村凑热闹的人。
我四处寻找着我的一些小伙伴,由于跳广场舞而被移到一边的那副破篮球架子下边,我看到了徐平,潘铁、柱头还有一个叫溜子的小孩子。
我先走了以往。这种全是我的发小,潘壮和现在我或是同学。
打了招乎我倚着篮球架子望向广场里,一眼我便看到了母亲,由于我的妈妈很美,舞跳得也罢,因此 她在第一排,她的后边是我们家隔壁邻居牛二婶和潘壮他娘,他们的舞步就有点儿实在看不下去了。
“杨鹏,或是他妈跳得漂亮,在我们村他妈跳得第一好!”潘铁衷心地赞美。
潘铁说得没有错,二十多个跳广场舞的人就数我妈妈跳的最好是。我妈妈自身长得漂亮,身型又好,便是跳得一般也凸显漂亮。
殊不知溜子发布了不一样的建议:“为什么说杨鹏他娘跳得最好是,那一个长发穿绿衣的女人跳得最好是。”
溜子2021年十岁,仅仅的脑子仅有后脑壳存着一条小辫子,很像电视机里演技清朝人。
穿绿衣的女人?我睁太大双眼仔细地看见广场里,这影响到我妈妈的殊荣难题,当然粗心大意不可。
尽管大家村较为穷,但在广场舞的大趋势下,这种舞蹈的大娘胖婶们做一套统一的服饰 还并不是什么问题。
他们的服饰 是粉红色带黑框,这和翠绿色没一点关联,在荤场里跳舞的人都衣着粉红色的服饰 ,哪有一个穿绿衣的女人?
我疑虑地看见溜子,发觉徐平她们也用不太对的目光看见溜子。
柱头怪异地回过头看见溜子不解地问道:“你说?”
“那一个长发的绿衣女人跳得最好是。”溜子反复了一句她刚刚得话。
“是不是你头晕眼花了,哪里有穿绿衣服的女人,他们都衣着统一的粉服饰 ,为什么会发生穿绿衣服的。”柱头改正溜子的不正确。
溜子的双眼一定是火蒙了,如何平白无故看得出一个女人来。
因为我讲了一句:“是呀,溜子,没有什么穿绿衣的女人?你眼睛白内障了吧。”
溜子响声非常大:“你们哪些目光?她就在二狗他娘后边,那么大本人你们没看见?”
我认为事儿仿佛有点儿不对劲儿,二狗他娘是最终一排,她背后哪有些人的身影。”
“溜子,你看清了?二狗他娘背后哪也有人了?没有人呀!”
徐平、柱头和潘铁也随声附和,允许我的见解。
溜子仍然不识好歹:“你们这种大孩子目光真不太好,那一个绿衣女人已经看你们,你们却看不到她。”
溜子这句话讲完,我突然之间就觉得不对劲儿了,都说未过十二岁的小孩子超级天眼还开了,她们能见到很多过去了十二岁的人看不到的物品,难道说溜子看到了什么?
但这想法也就在我心里闪了一下就过去。
我与柱头、徐平等没当回事儿,继续观看广场里的民族舞蹈,并随意扯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题讨论。
徐平悄悄取出一包烟,隐敝分到大伙儿,我条件刺激地看过一眼荤场里,见母亲正舞得兴致勃勃,这时怕是连自身姓什么都忘记了。
我悄悄地引燃眼,吸了一口后门把握成中空握拳将烟藏在里面。
潘壮沒有要徐平的烟,在我第一口烟吐出来 的情况下,他忽然说:“我身上很难受,好像是生病了,我先忙了。你们渐渐地一下吧。”
讲完他就满不在乎地站了起來,绕开广场,消退在雾晚上。
过去了不一会儿,徐平和柱头也说身上发冷不舒服两人搭伴离开了,这儿只剩余我与溜子两人。
我认为内心怪怪的起來,大家这种农村孩子,平日比小猴子还淘,几乎就不清楚生病是啥味道,如何今夜徐平她们不谋而合地都生病了?难道说溜子说得话是确实?
“溜子,你见到的那一个穿绿衣的女人还在哪儿?”
“嗯,她老在看你。”
溜子这句话讲完,也不知道是否心理因素,我立刻觉得人体刷地一下子,好像有一块冰猛然贴在我的心脏上。
因为我觉得到有点儿不对劲儿了,或是回来吧。
我扫了周边一圈,沒有看到爸爸的影子,他可能是去小商店了。
叫妈妈回来那就是不太可能的事儿,她如今正跳成瘾呢击败也不会回来的。
这时候我身上的凉爽好像更为浓郁了,早已要我的大牙有互相撞击的不理智。
回家了,这儿不适合多做停留。
我基本上飞也似地离去广场,独自一人回去走,仅仅想赶紧回家了到土炕躺一会儿。
离去广场后,我感觉的身上的凉意清除了很多,暗自松了一口气。
掉转那村口那棵大榆树,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突然之间只觉四周很黑也很安静。
我四下一望,如何村庄里真真正正的连盏灯光也看不到,并且还听不见一丝响声。
我内心一慌,不由自主加速了步伐。
这夜里如何那么静?平日里叫个不停的狗都没声音,满全球仿佛谁又能的声音在耳畔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