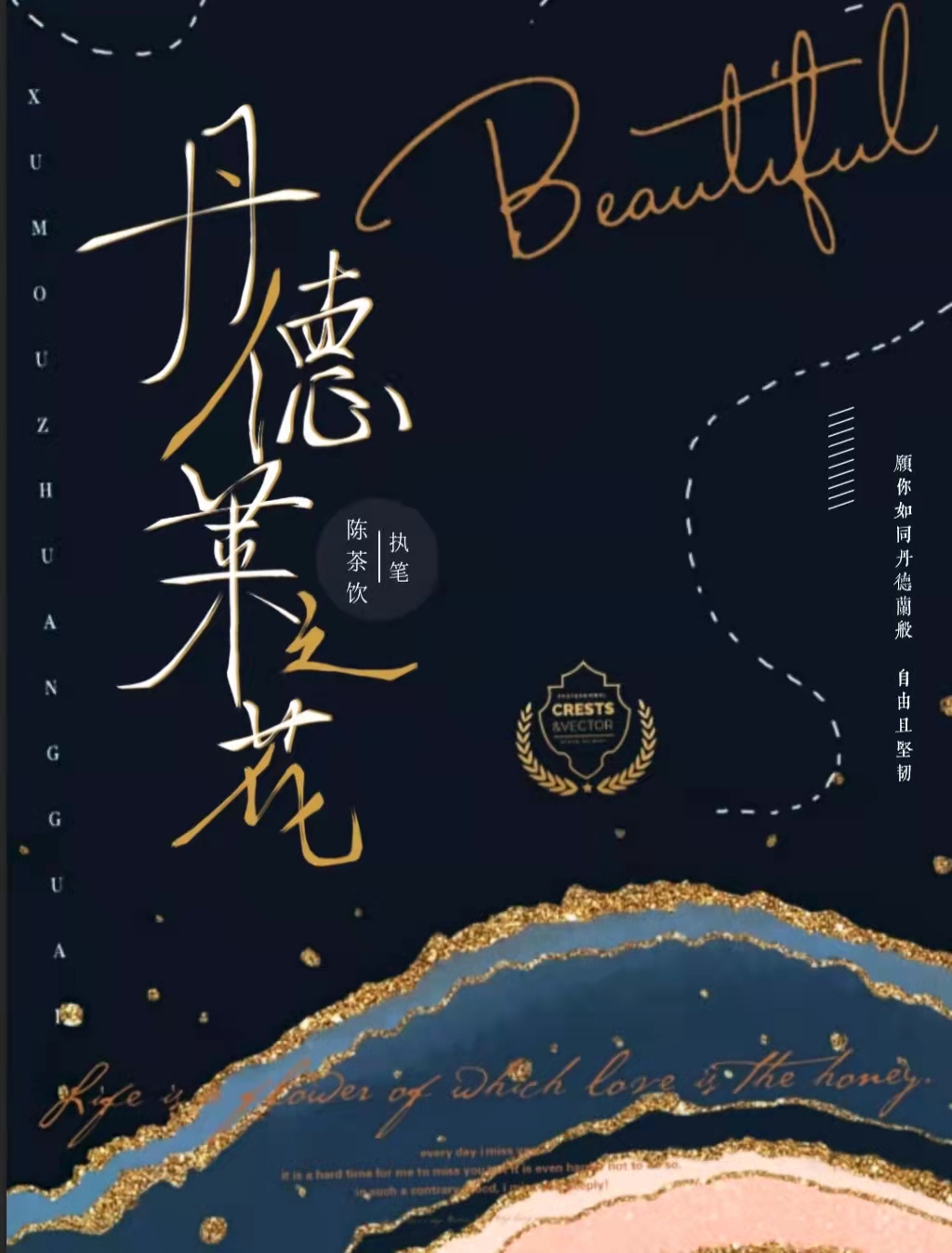京城的夜晚热闹非常,司倾见从没有见过京城的夜,原来,夜晚也不一定是寂静的,也可以是这样欢快火热!
圣北安也是头一次被人当成钱袋子,不过半个时辰,他的手里已经拿了大大小小十几样东西了。
司倾见看着什么都新奇,什么都想买来试试,试过了又都堆在圣北安手里,可怜圣北安手里早就拿不下了,想劝她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
他无法体会七年的孤独是什么样子,但那一定不好受,她难得喜欢,虽然自己遭殃些,但也随她吧。
司倾见看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忽然明白,原来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这个样子的,书上的字眼太空洞,她想象不到那么多人凑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原本她只觉得那是吵闹是烦杂,可是现在,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原来这世上的喧嚣,也能这样触动人心。
前方一处更是热闹,那边有一整个三层的楼阁,灯火通明,色彩艳丽,跑到近处才知道,这个地方叫金宵阁,也不知是什么地方是做什么的,只瞧着规模实在是不小,灯火通明、浓香扑鼻,还有很多浓妆艳抹的妙龄女子在楼阁上欢笑舞蹈。
司倾见素手一指:“那是什么地方?看着挺热闹的哈。”
圣北安抽空抬头看了一眼,可不得了,司倾见说着已经抬腿往那奔了,那可是妓院啊我的小祖宗。
他把手里的东西一扔,赶紧把司倾见抓回来:“那个地方你不能去!快回来!”
“你扔我东西!”司倾见挣扎不开,被圣北安强硬地拽了回来:“为什么不能去,我看着明明就有不少人进去了啊,他们都可以去,你拦着我做什么?!”
圣北安一时语塞,他该如何跟她解释,解释了她也不一定能听得懂吧,又要跟她说又不能说的太明白,索性道:“那个地方有规矩,你进不去!”
“什么规矩?我不缺钱!”司倾见指了指圣北安的钱袋子,满脸的迫不及待。
“我知道小祖宗你不缺钱,那我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我十六了!”
“那个地方年满十七才能进!”
“为什么?!”
“那是人家的规矩!”
司倾见满脸失落,那个楼看着就很好玩儿,楼又大又漂亮,里面的美人儿又多,还欢声笑语的……
司倾见叹了口气,忽然感觉有人拽她衣袖,正是束瑶。
束瑶指了指自己:“我十七了!”
“你十七了?”司倾见不可置信道:“你顶多十六岁跟我一般大,怎么可能十七岁?!”
“我看着很小吗?可我确实十七岁了啊,小姐你也没问过我啊!”束瑶摸了摸自己的脸,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小吧。
“我能去吗,我能去了吧!”束瑶还没忘了正经事,抬腿就要往里进。
圣北安:“……你忍心扔下你家小姐,自己一个人去玩吗?”
束瑶摇了摇头,这不道义!
“那不就结了,等你家小姐十七了,你们想怎么进怎么进!”
“这地方的规矩是根据什么订的啊?”司倾见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规定,她没听说过哪个酒楼因为年纪小就不让进啊。
“可能是人家楼主订的吧,反正这个地方规矩多得很,一年一变,明年兴许就不是这个规矩了。”
“那明年是什么?”
“明年?明年要求满十八才能进!”
“……这规矩该不会是你订的吧?”司倾见皱眉,感觉自己被耍了。
“那倒不是,我瞎说的!”
圣北安拔腿就跑,司倾见举着个糖葫芦在后面追,街上的人纷纷让路,以为是小情侣之间的打闹,倒也热闹。
圣北安自顾自的跑,司倾见象征性地追了两步吓唬吓唬他,却无意间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一身紫色,仿佛是藕戈,离的太远天色又暗,看的并不是太清,只是她那一身紫色的衣袍实在是太明显了,放眼整条长街,也没有几个穿这样独特的紫色的。
前面圣北安已经跑的不见了踪影,后面束瑶也还没有跟上来,犹豫了一下,她还是跟着那身影去了,她确信那个人就是藕戈,敌明我暗,多好的机会,她可不能错过了!
那紫袍女子谨慎的很,时不时便要四处观察看是否有人跟踪,即便看不到可疑的人也要绕几次路,还偏挑黑暗的地方走,只不过她的紫袍实在是太显眼了,司倾见又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隐匿脚步也不是什么难事,跟踪她绰绰有余。
紫袍女子越走越偏,眼看前面是一座小山,难不成,她要去那山里?她去那里做什么?
山路崎岖,又不是很熟悉,危险难以预测……
只是已经跟到这了,多一段路少一段路也没什么区别了,索性还是跟了上去。
走了半晌,山上越来越寂静,踩着杂草的声音也变得清晰可闻,为了不被发现,司倾见只能慢下来与她拉远距离。
天已经黑的完全了,朗月当空倒还算亮堂,偶尔还会飞出几只萤火虫,虽然还是有些害怕,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这山不高,山腰处有一平台,左右前方各有一条路,方才离得太远,终究还是没能看清人往哪边去了,只是上山的路更黑更狭小,那人既然选择入夜前来,必然不会去走那条路,那么就剩下左右两条路了。
天色太暗,也看不出左右两条路的区别,司倾见只好向左走了二十余步,放眼望去并没有什么值得一去的地方,于是快步往回走,又从右侧的路往里走,走了不过十余步,便看到前方居然有点点星火。
就是那里了!
她悄声靠近,这里是一处山洞,里面空间很大,墙上有燃着的灯,映得洞内昏黄,她刚想走进去一探究竟,忽然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是藕戈的声音。
“你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吗?”
听这话的意思,难道藕戈又绑了什么人,关押在此处?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那声音低沉虚弱,应该是被关了很久。
听了这话,藕戈似乎没了耐心,急躁起来,音调也抬高了不少:“你能在司黎匀手中活了这么久,我不信你没有她一丁点把柄!
也许你知道她的秘密,也许你知道些她不知道的秘密,只要你肯告诉我,我现在就能放了你,你的自由,近在咫尺,只要你告诉我!”
“小姑娘,我真的没有什么能说给你的……”那男人咳了几声,似乎很疲惫:“我知道,匀儿的仇家不少,你是来找她寻仇的是吗?”
“是……也不是!”
“……是匀儿她害了你的家人?”
藕戈顿了顿:“倒也没有。”
“我实在猜不出……她到底是何处得罪了你?”男人的语气更低了,似乎已经耗尽了力气。
“她不认识我……但只有她死了,我心里才畅快!”藕戈拿下一个烛台,将烛火靠近自己的脸,给男人看。
“这回……你明白了吗?我是不是应该说,我这个样子……全都是拜你所赐?”
“你!你是!”那男人又猛烈地咳了几声,声音颤抖几近失声:“她竟然……将你遗弃?”
“是啊……”藕戈抚上男人的头发,神情淡漠:“我若与常人无异,她或许不会抛弃我,说到底,她恨的应该是你吧?”
“也许她有难言之隐,有些事情,她也是身不由己的……”男人闭了眼,两行清泪划过,眉目间尽是难以抑制的痛苦。
“瞧瞧,你都已经这幅模样了,竟然还想着维护她!”藕戈嗤笑一声,继续道:“她从未有一刻真心爱你!司黎匀对外宣称你战死沙场啊,闻将军!”
闻将军?
司倾见眉头紧锁,她大致已经猜到里面的人是谁了,闻姓,圣墓王朝仅此一脉,那个人,应该就是闻容画。
当年整个京城都在传,说司黎匀攀附承继爵位的小将军闻容画,甚至恬不知耻地行了苟且之事,本可以光明正大的一段姻缘,却不知为何突然被揭穿,还被人传成了这个样子,为了维护清白形象,司黎匀只能随便收了一个书香门第的庶子入赘,又匆匆怀上了孩子。
孩子落地,也就是她司倾见自己,生出来是一对毋庸置疑的黑眸,那么司黎匀所有的嫌疑都被洗清了,再加上她本就是嫡女,如此一来,家主之位也非她莫属。
这是她能想到唯一的解释,司黎匀抛弃了她和闻容画的孩子,收养了自己,只不过是为了稳固她在司家的地位,让自己摆脱困境,什么母女之情,不过是利用罢了,哪个母亲会舍得将自己的女儿囚禁,数年都不去看一眼?
原来她这些年为司黎匀找的借口,不过是骗骗自己罢了,她对自己的无情、冷淡,就都说的通了……
司倾见咬着牙,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泪却早已流了满脸。
男人再次开口,说的却是:“也罢,终究是我对不住她……”
烛火一暗,藕戈忽然撕心裂肺起来:“你对不住她?你哪里对不住她?你是在说你这双眼睛对不住她吗?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像你一样,也被囚禁在这个地方十年二十年?!
我有什么错?我又做错了什么!
啊……不对,她不应该囚禁我……她应该在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掐死我!
你说对吧?父亲大人!”
“父亲大人”几个字藕戈说的咬牙切齿,她不明白,司黎匀这样对他,甚至不肯承认他的孩子,他还有什么好替她隐瞒的?!
难道他就这么心甘情愿被司黎匀玩弄?!
她不愿意,她藕戈不愿意,她被抛弃被放弃,难道就是应该的?凭什么,她凭什么要经历那些痛苦,她不甘心,她做梦都想要司黎匀下跪道歉,不还不够,她要让她尽失所有,生不如死,就算是死她也要司黎匀陪葬!
“是我对不住你们,孩子,你若是心中有恨,就杀了我吧!”闻容画起身,仔仔细细地看着藕戈,似乎要将她的模样烙印在心中,他道:“我应该为因我而起的因果付出代价,你动手吧!”
藕戈突然嗤笑一声,也流下泪来:“杀了你,岂不是替你解脱?你就在这里生不如死地囚禁着吧,什么时候你肯开口,什么时候我便给你了结!”
为了这双眼睛,我受的痛苦还不够多吗,我要让你看着司家覆灭,看着你爱的女人如何从云端跌落,这才是真正的解脱,不是吗,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