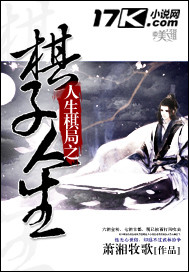我的爷爷名叫约瑟夫。
约瑟夫爷爷是二战时期的老兵,是一位根正苗红的英格兰人,早在十七岁时就已经光荣地以一名士兵的身份为击溃德军的事业效力,并在1939年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1940年,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损失了大量兵力。正当德国占领完西欧,发动海狮计划,企图向不列颠的领土伸出魔爪时,年轻的约瑟夫爷爷与另外千余名战友们在英吉利海峡的上空顽强地抵抗着入侵者,在长达数周的奋勇决战后,守住了英伦三岛,给了长久不败的恶魔一记当头棒喝,以英雄的身份凯旋而归。
人们都说,约瑟夫 · 弗里曼的一生中有三次蜕变。第一次是他十七岁那年被迫参加士兵选拔的那一次,那时的他总是畏畏缩缩、蹑手蹑脚地,只敢越过自己浓密的眉毛注视别人。身边的成人们纷纷调侃他神经过敏,妄想症犯了。当然,这是绝对可以体谅的,毕竟在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后,没有哪个十七岁的孩子可以让阳光自信的目光再次从眼眶中照射出来。但是那一天,他成为一名士兵了。
他的第二次蜕变,是没有人能预料到的,几乎是没有前因后果的。那是1939年二月的一天,那天他从训练场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擅自背上行囊溜出营地,像一个逃兵一样向远方走去了,两天后才回到训练营。为此,他被罚了许多天的禁闭。
但是,在场的士兵们普遍注意到了一点细节——约瑟夫脸上的神情变了。由怯懦、自卑,变得坚定、强大。
自此,他将自己的潜力全部翻了出来,比其他人都要刻苦地训练,最后成为了一名王牌飞行员,并立下了赫赫战功。战斗胜利后,他又带领着战友们成立了工厂,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并组建了家庭。
他的这种充满干劲的积极精神一直持续到老去,一直到......他的人生轨迹第三次变化。
年过花甲,自从奶奶去世后,他的精神状况急转直下。人们都说他疯了。他将自己改在郊外的老别墅封锁得严严实实,大门上布了五道铁锁,每一丝墙缝都用混凝土补上了,每一扇窗户都钉上三层厚木板盖了起来,只留下一扇面对前院的窗户还留了一道缝隙。每天一半的时间他都坐在这扇窗后,透过缝隙用浑浊的眼睛惊恐警惕地扫视着房前。他的邻居们都被他的这幅模样吓坏了,指责父亲为什么不将他这样一个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
我就是由爷爷带大的。从小到大,陪伴我最多的就是约瑟夫爷爷。每当我在学校被别的小孩欺凌时,总是爷爷安慰我,替我解围。而且爷爷的学识十分渊博,我的功课他都基本可以拿下。小时候的我十分胆小,总是会觉得身边有怪物会伤害自己。当我因为恐惧睡不着觉时,爷爷就会为我讲起他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他说,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充满了快乐与魔法,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且总是会帮助爷爷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若是有怪物企图伤害我,这些朋友都会挺身而出来保护我的。他有时会打开过去的相册,将他那些仿佛是用拙劣的修图技术合成的黑白老照片翻出来一一指给我看,上面印着那些他为安慰我而虚构出来的神奇伙伴们。
他掏出一张照片,照片里印着一个带着贝雷帽的男孩,他的周围围着一群鸟儿还有兔子。
“看!这个小朋友叫爱德华,他可以和任何小动物说话!”
他又指着另外一张照片,里面是一个女孩,她在空气中划出一个像是传送门的结构,正微笑地看着镜头。“这是达科塔,她能在一瞬间转移到数米开外的地方,厉害吧!”
“在看看这张,”他又掏出一张,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门框,“这是雨果,雨果是隐形的。他们都是爷爷曾经十分要好的朋友!”
这样的照片还有大堆。
之后,他就会手舞足蹈地描述起他们之间发生的趣事,幼小的我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着,哈哈笑着。
我就这样在爷爷的童话中长大。
很明显,爷爷的童年都是编出来的。他的青春里充斥着战乱,只不过不想将这些悲惨的事实展现给我罢了。当时的我由于比较无知,便接受了爷爷的这些奇妙的故事。
当时的我,十分崇拜他。
而现在回想起我和爷爷的往昔,我不禁怀疑那是否就是爷爷的精神出现问题的开端。
约瑟夫爷爷发生转变时我十二岁。那天,我跟着父亲步入熟悉的爷爷家,刺鼻的排泄物气味扑面而来,房间里乱糟糟的,各种废弃的书籍、破烂的家具、浸水发霉的旧报纸塞满了所有空间,餐盒、废纸和其他腐臭的垃圾散落在地上,蟑螂和苍蝇已经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乐园。房子的灯显然是许久之前就已经坏了,整个房间昏暗闷热又潮湿。房间里唯一立着的家具是那把窗边的旧沙发,在它上面,一手将我带大的约瑟夫爷爷盖着被扯坏的发霉窗帘蜷缩着,胳膊里抱着一杆猎枪,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窗外,仿佛是他又回到了深渊般的战壕中。我们来到他身边时,他先是惊恐地将枪口指向了我们,大声嚷嚷着什么,看清了我们后又狼狈地跪坐在脏兮兮的地板上大哭着。
父亲将他带到了精神病院,医生诊断说爷爷是因为青少年时期受战争影响,心理阴影太大,精神受损,导致老年痴呆后出现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具有强烈的攻击性。于是,爷爷顺理成章地被关进了病院,成为了一名精神病人。
之后,我们探望约瑟夫爷爷的次数也被限制了。
直到前天,约瑟夫爷爷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病房里。
他已经僵硬的尸体坐在躺椅上,浑圆的双眼直直地注视着天花板,嘴巴半张着,仿佛是直接被吓得魂不守舍一般。在他遇害时间的监控里,只见他只是坐在躺椅上睡觉,下一秒就瞪圆了眼睛,死去了。他的身体里没有查出任何毒性物质,但是咽部出现了器官黏液,堵塞了他的呼吸道。
对此,院方给出的解释是,约瑟夫爷爷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十分恐怖的东西,然后被这个想法吓得气管内黏液上涌堵塞咽部,呛死了。
我对这种无厘头的猜测简直是嗤之以鼻。爷爷作为年轻时的王牌飞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臣,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怎会因这种可笑的死法死去?
今天一整天,我都忿忿不平。我约上了朋友查理,打算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查理是我的狐朋狗友,他是那种,就是你的家长绝不会允许你和他往来的那种小混混。但是,十七年来,查理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愿意和我交往的同龄人了。我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经常会叫嚷着看到了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大街上和路人擦肩而过时,我会突然因为一阵沁心的寒冷呕吐出来,然后一脸异样地看着对方,迎来周遭群众的不解。一些迷信的人会认为我身上有着某种诅咒,被恶魔占据了身体,于是请我去进行驱魔治疗。父母想尽了千万办法,拜访了无数神学大师,都没能将这“恶魔”从我的体内赶走。为此,我挨了不少欺凌。然而,查理觉得这很“酷”。他喜欢一个被当作恶魔的人走在自己身边,这可能是他这种人身上特有的一种性质。
下午,我和查理在街区西侧的小巷子里见面。
查理染了红色的头发,穿着深蓝色的棒球服坐在垃圾箱上吞云吐雾,正用布满文身的手臂在砖墙上涂鸦。整条巷子里花花绿绿的涂鸦都基本是他一个人的杰作。
“哟,你来了,四眼怪?”他看到我,飞身跳下垃圾箱。
“我来了。”我说着,取下了眼镜。
“所以...你的爷爷前天死了?”
“是的。”
“然后你很伤心?”他弯下腰试图观察我的表情。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冤枉,你应该知道我爷爷的...”我将眼镜放进荷包,“他那样厉害的人,竟然被冤枉成那种窝囊的死法死掉了!你说说,怎么可能呢?你应该看到我给你发的短信了吧,他们怎么描述他的死法的。”
“哈呀!不然他能是怎么死的?被你那些恶魔朋友们摄了魂了?”查理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伤心什么,你爷爷以前确实是个真男人,但他现在是什么啊?精神病人!这对一个精神病人是再正常不过的死法了。你想知道我二大爷怎么死的吗?”
“你真的很不会安慰人。”
“他他妈是被自己的耳机缠死的!怎么样,够窝囊吧!”
有时候我真的特别嫌弃查理,他总是一步步试探我的底线。但我一直以来都忍过去了,毕竟人都是需要社交生活的,没了查理,我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交谈了。
“每个人都要死,什么死法都是死,别挣扎了,接受吧!”他说。
“我无法接受。”我说道,“今天晚上,我爸妈会把爷爷对我留的遗言托付给我,我们再在这里见面吧。”
遗言是爷爷在进精神病院前就写好的。我十分热切地期待着,希望遗言里的内容会对爷爷的死法有所转机。毕竟一直以来,我对爷爷是最亲近的,父母和姑姑的工作都很繁忙,一直是年幼的我陪伴爷爷。说不定在遗言里,爷爷会将重要的东西交代与我。
夜晚,我再次和查理在小巷子里碰头。我缓缓打开手中爷爷留下的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条,纸条的边角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仍然无比清晰,足够辨认。
“这就是遗言?为什么会这么短?”查理一脸疑惑地看着纸条上的字,上面写着:
亲爱的孙子裘德: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你有好好学习吗?还是已经考上了优秀的大学?你交到知心的朋友了吗?还是你已经脱离了世俗,去寻找自己的宁静了?希望我的死去没有困扰到你,让你的步伐停滞不前。爷爷的一生确实受过了很多苦,但爷爷也有知心的挚友,而且也在不懈的努力后找到了幸福。对于你的遭遇,爷爷也觉得自己完全能够理解你。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我知道我的死法会被人们所嘲弄,但请你记住,我的死一定是一场谋杀。是一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解开的谋杀。我的礼物会指引你前进的方向。
安布鲁斯 ? 布尔斯
1939年2月16日? ? 明古莱孤儿院〇
一块破旧的手表被用胶带绑在纸中,那是爷爷生前佩戴过的手表。
“所以?你爷爷不是自己暴毙的?”查理说“他糊涂了?落款都标错了。”
“我...."我看着“谋杀”二字,陷入了沉思。这确实是他的字迹,而且他当时的意识一定是清醒着的,不然他不可能用工整的字写下这些话,而且这样的话,我对他死法的猜测也可以证实了。但监控中仍然显示,没有任何人去杀死他。
我又看向落款,落款明显是错误的,但我注意到了落款后方的那个圆。那个圆是如此醒目,以至于我无法将视线从它身上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