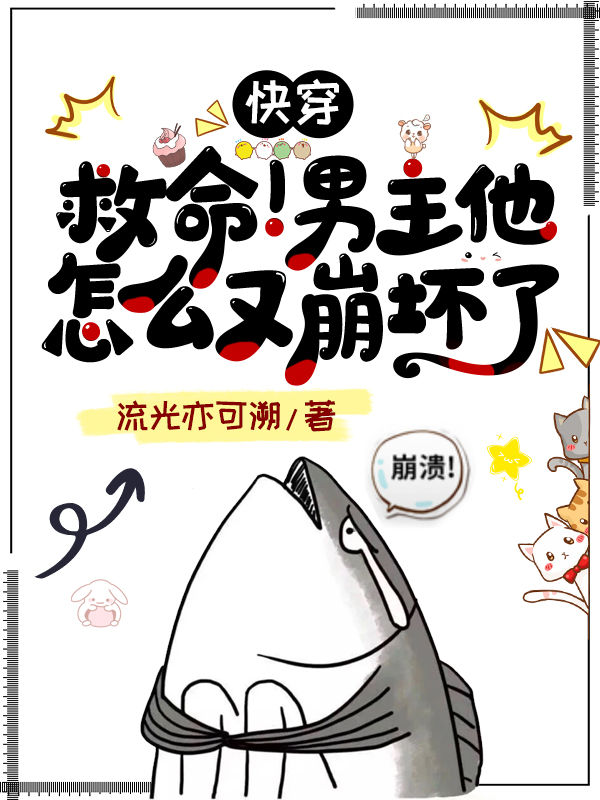见到这一锅剧烈翻腾的沥青,那一能和尚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一锅沥青,口里含糊不清地喊着:“厂公饶命,厂公饶命……”
“现在你认罪还来得及,不然这沸腾沥青的滋味,可让你尝个够!”霍维华半眯着眼,得意地诡笑着,语气里的寒意,让小和尚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小和尚到底未经人事,还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何种圈套,还在拼命解释:“请……请厂公相信我,我……我没有,我没有啊……”
她看着小和尚,心里不免悲伤起来,此刻只怕认罪也是死,不认也是死!
“臭和尚,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说着,霍维华拿起木车上的瓢,舀起一瓢沥青,缓缓地向小和尚走去,半眯着的双眼,散发着凶狠的光,让人心惊胆战。
“求求你,不要,不要……”小和尚双眼死死盯着霍维华的手,嘴里不住地苦苦哀求,双手撑地,费力往后挪动着身躯,不过一瞬间的功夫,额头上早已冒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
忽然,那霍维华一声闷哼,右手一挥,手中的沥青已然恶狠狠地向那小和尚泼了去!
“啊~~~~”随着一身惨叫,小和尚痛苦地在地上打起了滚,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倒吸一口气,紧咬着牙侧过脸去,不忍心再看下去。要知道沥青的沸点达二三百度,这要是泼在人身上,那是如何滋味,谁都无法想象。
这时,霍维华再舀起一瓢沥青,眼里是凶恶的光,作势要再泼上去。
“不要,不要……”小和尚不住地祈求哀嚎。
“你招是不招?”
“我招,我招,我什么都招……”小和尚早已痛不欲生,见还要来一次,如何招架得住。
“早招不就好了吗?就不用这么受罪了。厂公,奉圣夫人,这臭和尚已经招了,谋害皇上,罪该万死,厂公看……”
已经招了?这就叫招了?他招什么了?这连屈打成招都算不上!
她愤懑不已,可奈何此刻身在宫中,皇上已然病重,皇后看起来也奈何不了,她一个小小的信王侧妃若是贸然暴露身份,恐怕保不了这和尚,还要害了信王,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本千岁还需要你来指示该怎么做吗?”魏忠贤轻抬眼眸,一脸不悦,似乎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生生抢了去。
“是,是,是!是微臣一时失言,还请厂公见谅。”霍维华生怕魏忠贤突然变卦,更加唯唯诺诺。
“皇上中毒一事现已证实,兵部右侍郎霍维华遭奸人陷害,蒙受不白之冤,今日沉雪,无罪释放。另感其对皇上忠心一片,赏金百两。”
一听这话霍维华早已喜笑颜开,直磕头谢恩:“厂公英明,谢厂公明察秋毫,还微臣清白。”霍维华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
“咳咳”奉圣夫人轻咳两声,对这霍维华翻了个白眼。
“清禅寺僧人一能已亲口招认毒害皇上一事,来人哪,清禅寺僧人一能伤及龙体,罪该万死,特赐剥皮之刑,以儆效尤!”
魏忠贤向下面扫了一眼,一脸云淡风轻,嘴角是笑意,眸子里竟是冷冽的寒意。
剥皮之刑……一听就叫人毛骨悚然,众宫女太监皆震惊不已。
剥皮之刑,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凌迟。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
早就听说过九千岁好用剥皮之刑,其剥皮之刑却与平常的不一样,先前都是剥死人皮,九千岁却喜欢直接剥活人!
这听起来就极其恐怖,难道今日九千岁要在这乾清宫门口执行剥皮之刑?!
这时,魏忠贤手下的厂卫已然将那小和尚绑在一块门板上,他此时吓得魂飞魄散,瘫软地挂在门板上瑟瑟地发抖,嘴里不住地哆嗦着:“厂公饶命,厂公饶命……”
这时,她猛地跪在了地上,之后,许多宫女太监跟着跪倒在地,可还没开口,魏忠贤冷冷的语调已经传来:“谁敢求情,同罪论处。”
众宫女太监全都闭嘴,不敢再发一言,生怕这火烧到自己身上。
她只觉胸口憋闷,一把冲上前去,可跪在她身后的思铭早已死死拖住了她,她一丝都动弹不得,只能跪在原地死死地瞪着魏忠贤和奉圣夫人!
“厂公都赐剥皮之刑了,你们还愣着做什么!”霍维华厉声对身后的厂卫喝道。
“是!”
几个厂卫闻命,立即从庭院中间那口大铁锅中用小瓷筒取出煮成液体的滚烫的沥青,均匀、细致地从头到脚浇到被钉在门板上小和尚的全身,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
一时间,焦湖味、肉香味腾散于空气之中,一种发自小和尚胸腔深处的耸人低声惨嚎从被堵的喉咙中发出。
她脑子一直嗡嗡直响,侧着脸不敢看,可那股人肉香味传来,她还是呕吐不止。此时,其他许多人都蹲下来呕吐了起来,另外一些更好,直接就吓昏过去。
而魏忠贤此刻正用小金盅饮着热腾腾的热酒,欣赏着手下人的活计,不时出言指点一二。
“你们看仔细了,谋害皇上就是这个下场!”魏忠贤抿了一小口酒,回味地舔了舔嘴唇。
待小和尚身上沥青干透,一经魏忠贤示意,早已候在一旁的几个小太监狞笑着,有拿小刀切剐的,有拿木锤敲击的,几乎都是一级厨师一级裁缝的手艺,完完整整把小和尚的整张人皮活剥下来。
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地上,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小和尚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看见自己的“皮外衣”立在自己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
她听到动静,无意间瞥了一眼,瞬间脑子一片黑,吓昏了过去。
恍惚间似乎还听到魏忠贤的声音“来人哪,将剥下来的人皮制成两面鼓,挂在东厂门口,以昭炯戒。”
她再无丝毫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