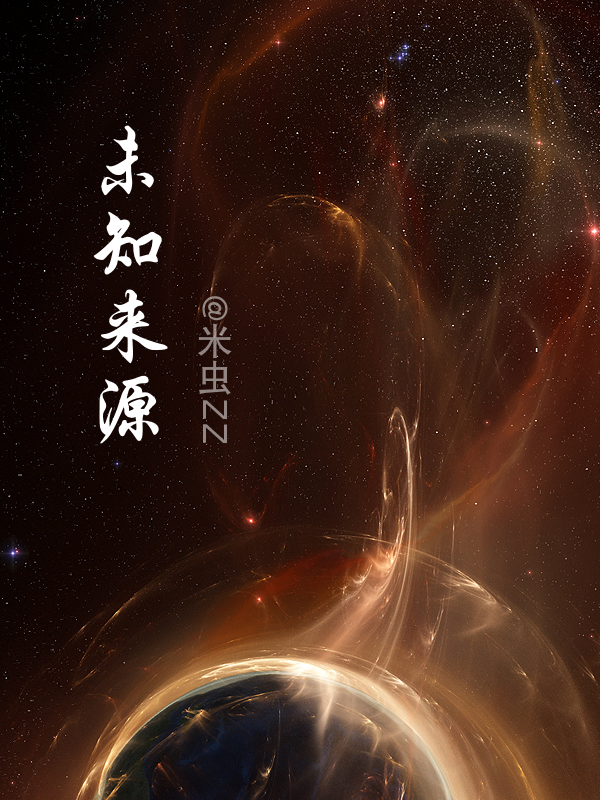LCD屏幕投射出来的背光从雨面前缓缓放大,经过液晶点阵的时候扭曲了,置换成微电流,信号穿过交错的时空网络然后又变成冷色的白光,牵引芸的视线。
合上翻盖的时候,芸看见整理书桌的时候翻出来的相册。
南夏大学馨谧圆的梅花开了,三点两点红妆,为这座城市的冬天增添了些许生气。芸趴在窗台上侧着脸向下望,透过这层玻璃窗,靠近阳光的地方有个很大的书架,上面堆满了各式各类的法律书籍,书架正下方的台面左侧立着一盏古铜色台灯,灯光照在厚厚一沓文书纸上,纸张用一本大法律辞典砸牢,辞典里夹着一枚印有“朝昕大学”校徽图案的墨绿色书签,一支黑色的钢笔静静地躺在光暗交织的地方,旁边有一竖相框,相框里镶着一张纸面有些泛黄的照片。
芸把相册重又放回到抽屉那一块安静的角落里,目光落在了相框里那张泛黄的照片上。相片里有个穿浅蓝色连衣裙的女孩,伫立在山的一端,微风吹起她的发向后飞舞着。她伸开双臂,镜头在雪白的臂膀上反射出一层七彩的光晕,光晕投射到她脸上,她那双明亮的深蓝色的瞳仁,好像在欢快地大声呼喊:
“飞起来了!”
……
别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雨说这是他最得意的摄影作品,他把它称作“芸之翼”,尽管他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当时我们之间只隔了两米的距离,可是我却总是觉得他离我好远好远,远得近乎于渺茫。大概在他心目中,我也是一样吧。
翻开照片的背面,碳素钢笔的字迹是雨的。上面写着:
“芸之翼WingsOfYun
1998年4月25日,江玉筠山。”
那个时候雨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龙飞凤舞的,又喜欢在我面前炫耀他的英文,以前他很喜欢在他的画作和所谓“字帖”上签上个大名送给我,可是这张照片他却说什么也不肯给我。他用吃冰激凌的五毛钱把这张照片过了塑,再用剪刀把四个角修得圆圆整整的,夹在每天看的百科全书里每天擦,这是他告诉我的。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他说得那么夸张,不过一个月后用威逼兼利诱的手段把它从雨手上抢过来的时候,确实还跟新的一样,连褶皱都没有。我有些吃惊,世界上真的可能有这么心细的男生吗?
世界是会变的,人也一样。
他变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前那个在篮球场上飞奔的雨不见了,那个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东蹿西蹿的雨不见了,那个跑十二里山路来给我送伞的雨,不见了。他变得内向,古怪,高中以后他变得更加沉郁。好像一直在想什么心事似的,我渐渐发现和他交流越来越困难,他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永远是那么迷惘和不确定的神色。
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还是世界变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距离在我们之间竖了一层隔膜,让我们看不清楚,猜不明白,这距离除了空间,还有时间。
还有什么是不会变的?是照片里载着浮云的天空么,还是照片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