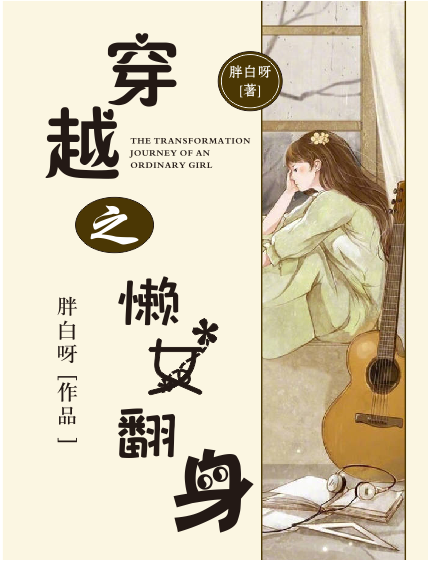“这你倒是可以放心,尘拜无霁已经把他身边的奸细择出去了!”
她心里其实还怀疑有别的内奸,尘拜无霁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就看刚才他吩咐夏之洐重新安排队伍,四人一组,相互监督。
墨浔又用那染了血的帕子捂着嘴咳了两声,声音低沉,胸腔内却有破碎的声音,絮濡沫当然听的出他内脏有破损,身体受了严重的内伤。她又想了片刻,突然抬头看着床幔后的身影,沉凝的问道:
“你认识我,那说明你在上船时就知道了这是尘拜无霁定的船,那么也该知道了我们是要去京都,如此你依然冒险上来了,是否代表你的目标也是京都…南韦闻靘没回韦国?他也去了启元?”
“安姑娘,你很聪明。”墨浔用帕子轻点了嘴角附近,确定没有血迹了才放下,片刻又揽起床后的床幔,有些支撑不住般的坐在了床上,深喘了几口。
透过床前的帐幔,絮濡沫依稀能看到他的艰忍,无所谓的笑了笑,想起久盘心中的疑惑,问道:“南韦闻靘跟韦国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要找的人究竟是谁?”
墨浔没料到她会问出截然相反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不算秘密,三国皇族和贵族都知道,第二个却是机密,就连他都不是很清楚,无声的一笑, “主子是韦国皇上立下的储君,至于主子要找什么人,我也不知道。”
絮濡沫奇怪的问道:“韦国储君?为什么叫韦公子不叫韦太子?”
墨浔抬头看了她一眼,沉凝不语。
又是不能说的皇家机密?她盯着他所在的位置,也不说话。许久,才听他叹了口气,声音透过床幔缓言道:“主子不是皇上的子嗣。”
絮濡沫有些意外,抿唇挑眉,听他继续道:“这事韦国举国皆知,皇上的子嗣很少有活过十岁的,几个十岁以上的也都非残即痴,没有一个能够继承国统。”
每代皇族之争都是一部血泪史,韦国也不例外,只是听起来韦国之争并不是发生在皇子身上,倒像是亲王或臣子之间的,残害的皇子非痴即残让皇上百年后无人继位好从中谋位,想来这个韦闻靘在韦国过的也不容易,长指抚过怀中揣着的长命锁,她斟酌着问道:
“韦国的皇子惨遭迫害,公主…应该都无碍吧?”
墨浔声音透着些疑惑,回道:“韦国不曾有过公主。”
絮濡沫不由惊讶,声音也提了提,道:“没有皇女?”
墨浔肯定的回道:“没有!若是有的话,皇上早就赐婚给了主子,那样的话主子也不用在韦国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履步维艰了。”
怎么可能没有皇女?南韦麒麟,天命皇女,难道这只是一句预言,不是这个时代的?不可能!絮濡沫坚持自己的判断,南韦闻靘要寻的人绝对跟这个皇女有关系。
她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死心的又问:“是没有,还是你不知道,这可是两个概念!”
墨浔此时也有些怀疑了,问道:“安姑娘对韦国有无公主怎会如此好奇?”
絮濡沫也知道这样说他肯定会有所怀疑,有些事,不能全说,却可以说一点,既可以打听到自己想知道的,又不叫人太怀疑。
“诚王和我都认为,南韦闻靘要找的,应该是韦国一名在幼年时被抱走的皇女。”
“幼年抱走?”墨浔的声音有些拉长,似是陷入了思考回忆中,“如今是我韦国尚德十四年,皇上还是尚王之时只听说有王妃没听说有小郡主,就连尚王妃也在十五年前那场延晨宫之变丧生,后来皇上登基主国的十四年来确实从未听闻茩宫有妃嫔产下皇女。”
絮濡沫听他喃声,不像撒谎,可是长命锁的机关细致花纹精美天下少有,也不像是无聊之举,韦国在这件事上必定是有所顾忌而欺瞒了所有人,韦国此举是为什么呢,难道是顾忌天命皇女这四个字?
她听到墨浔又低低的咳了几声,相比之前仿若更重了些。
通过谈话,她大概了解了他藏在船上的目的,其次,她的武功也不一定在他之下,而他此时还受了严重的内伤,也就不担心他会突下杀手了,她从他的低咳声中听出他这伤不治的话最多再能撑过两天。
她将长鞭搁在桌上,想了想,有些犹豫有些不舍的从腰间摸出一个锦囊,倒出其中一颗用油纸包细致包裹的药丸,极心疼的剥开取出一枚墨绿的药丸,走到床边掀开一直挡在两人中间的幔帐。
掀开了幔帐,她抬眼望去,不由呆愣了片刻,自以为见惯了各式帅哥的她,不相信这世上还有男人可以让她另眼相看了,可是,第一眼看到他,还是有些惊艳。
不同于眼药的孤傲寒凉,瞿瑾的阳刚冰凉,南韦闻靘的病态妖冶,尘拜无霁的疏离优雅,十一的清纯阳光,墨浔给她的感觉,并不像是一个侍卫,虽受了伤,气质却依然清雅,如玉般温润平和。他看起来不到二十,身着一套黑色紧身衣,勾勒出宽肩窄腰,身形修长挺拔,一头如墨的乌发随意的束了在头顶,鬓若刀裁,面如精雕,深刻却柔和,眉如鸦羽,斜长的凤眸微薄,眸似深潭,此时只静静的回望着她,视而含笑,挺鼻如岭壑,脸色有些苍白,更彰显漂亮如菱的唇艳若施脂。
絮濡沫借着欣赏美男不着痕迹的细看了下他的眉梢眼角,若一个人时刻堤防着准备着,眉梢眼角处便会不由自主的绷紧或有微的僵硬,而他,没有。很好,她笑了笑,伸出手,展出手中墨绿的药丸。
“不怕死的话,就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