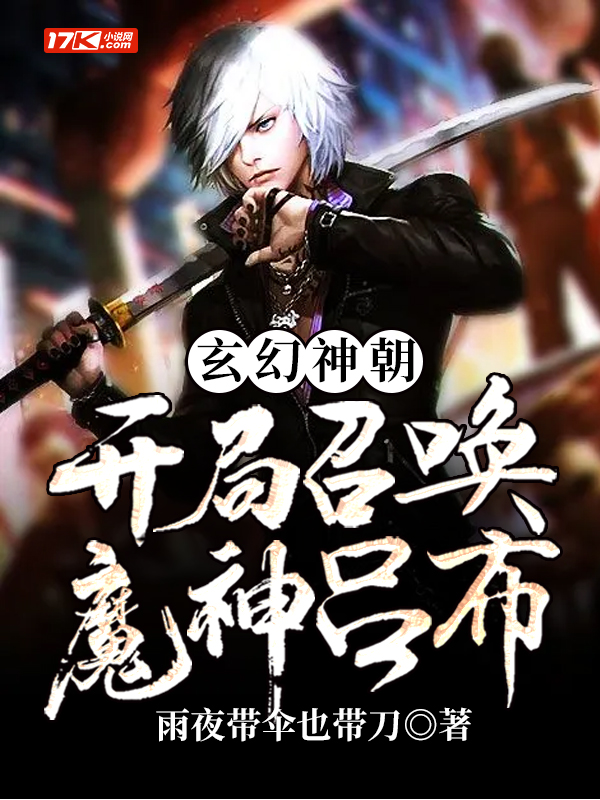时近中午,街上的行人川流不息,但宁州的街道极宽,是初商城的三倍多,虽然街边摆着各色的小摊,倒不觉得拥挤,闻靘在中,瞿瑾和絮濡沫在其左右,那些所谓的隐卫也不隐了,仿佛生怕闻靘趁乱逃跑似的,紧紧的随其身后,相距不到一米。
这一队奇怪的组合引来很多百姓的驻足打量,却又在最后惊慌失措落荒而逃,絮濡沫纳闷,回头一看,闻靘身后的侍卫中,其中有个三十多岁面堂微黑的彪形大汉,一边眉中一道竖着的疤痕从脸腮处直延伸到鬓角,深刻,扭曲而狰狞,眉毛也缺了一半,面相极其凶残暴戾,看到絮濡沫打量他,他也眼神如刀般直视着她。
絮濡沫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见他如此一下来了气,转了身子不再看他,口中却刻薄尖酸,“这张脸啊,也就适合当隐卫,但你偏偏要在太阳光下自爆其短,长的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唬人就是你的错了,不过也好,红花这玩意儿就是得绿叶配,你在我们身后,更衬托的本姑娘和你家公子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若天人,不错,不错。”
身后一阵拳风袭至,絮濡沫充耳不闻,反正她被封了内力,就不信瞿瑾那死孩子能由着她挨揍受欺负,果然眼角瞟到瞿瑾黑色衣角一闪,已拦在她身后,几声拳脚相加的声音后,闻靘轻咳了一声,“都住手!”
瞿瑾是真的关心闻靘,那刀疤男子似乎也有所顾忌,怕闻靘就此倒下,两人闻言后同时停手,瞿瑾又站到闻靘身侧,絮濡沫不动声色的把了下他的脉象,还好,没什么异常,却感觉闻靘修长冰凉的手指悄悄的捏了她掌心一下,她抬眼看去,见闻靘冲她眨了眨眼,飘渺的眼神中荡漾着一抹狡黠,他挥了挥手,“我还没死呢,都造反么,你们都离远点吧。”
身后却没有任何声音,絮濡沫再次回头,七八名侍卫都将询问的目光投注在那刀疤男身上,刀疤男哼了一声,恶狠狠的瞪了一眼絮濡沫,这才一挥手,率先隐去,其他侍卫见此也纷纷隐到了人群中或酒楼屋顶上。
她心中一阵阵难过,闻靘仿若根本没发现身后的一切,面色平静宁和,一身随风飞舞的天青色如同簇拥的火焰,惊姿绝艳,让她想到南美海拔四千多米人迹罕至的涯上一种花,她突然有一种预感,他的隐忍和积累都会在某一朝爆发,炫出极致的璀璨,惊天一色。
想到那种这个世界上没有的花,她眼中一片迷离的向往,“我见过一种花,名普雅。开在孤寂的寞涯,用一百年等待一次花开,用一生摇曳一季美丽,伫立高原之上,风吹日晒,生长环境极度恶劣,却依然努力采集阳光的温暖和芬芳,汲取大地的养料,默默营造自己的花事,等待了一百年,只是为了用一百年一次的花开,来证明生命的美丽和价值。”
絮濡沫看着他,眼中满是信任和鼓励,“我相信,你也能!”
闻靘心中一震,极惊讶的转头看向她,忍不住咳了两声,这次却不是装的,体内疼痛难忍,但他不为所动,只静静的看她,仿佛要将她的全部印入脑海一般,一线妖冶的鲜红顺着唇边蜿蜒而下,他突然淡淡一笑,比以往的笑加深许多,眼中也有了向往之色,于是,他的美更加灿烂耀眼,更加夺人呼吸,他随意的用袖袍一抹,动作有些粗鲁,下巴的血是看不见了,却将皮肤拭的较其他部位偏红,他点点头,“我会的!”
瞿瑾感激的看着絮濡沫,眼中甚至有了雾气,她有些鄙夷的瞪了他一眼,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三人正要继续前行时,一名丫鬟打扮的娇羞少女扭捏着行到青纹跟前福下身子行了一礼,一张秀气的小脸红彤彤的都快垂到胸前了,站起身后低着声音嚅嗫道:“不知公子可…有时间...我家小姐,想…请公子喝茶。”
说完,伸手指了指不远处一家极其雅致的阁楼,几人顺势抬眼看去,正好看到二楼一抹淡淡的粉色纱影一闪而逝,只余一线泼洒如远山深黛的发丝在风中旗一般的招展,如一只挠心的小手轻轻的搔抓着,又痒又惑。
闻靘是不愿意凑这个热闹的,但絮濡沫却极感兴趣的拉着闻靘的手,笑嘻嘻的道:“不是说你是陪我逛街的吗,我挺想去瞧瞧的,再说了,免费的茶,不喝白不喝!今天就当沾了你的光。”
闻靘眉间有些无奈和不情不愿,但依然样子极乖的点了点头。
絮濡沫牵着闻靘,后边跟着瞿瑾随着小丫鬟上到怡心阁二楼一间雅间,一推门便见窗边一位身着粉衣缕金百蝶穿花云缎裙的女子仪态袅娜的站起。女子肤如高山雪,雅如月下芙蓉,一张脸美丽细致如瓷,柳眉细细弯弯,凤眼微微吊起一个妩媚的弧度,挺鼻直俏,红唇微启,彷若开在仲夏晨雾中的玫瑰,晃着迷蒙魅惑的光泽。
女子落落大方如蝶翅荡花般翩跹至眼前,声音若黄莺出谷般婉转清脆,略施一礼,既有大户小姐的端庄,又有江湖儿女的洒脱,只听她道:“珞岚冒昧相邀,让公子见笑了。”
瞿瑾在门外守着,絮濡沫牵着闻靘走了过去,将闻靘按在一张椅子里,闻靘刚坐下便打了个喷嚏,絮濡沫赶忙顺势给他轻拍了两下背,他刚刚才吐了血,可别因此再牵出体内器官的震荡受伤,这金贵身子,一般人还真伺候不了,她柔声道:“别激动,慢慢呼吸,平心,静气,怎么好好的竟会打喷嚏?”
闻靘皱着眉,眼角微微一挑,不满的看向珞岚,“身上乱七八糟都些什么味道,臭死了!”
絮濡沫一楞,女人不都喜欢身上香喷喷的吗,她身上的草药味是从内而发,她也早就习惯了,这珞岚应该是用的茉莉香,哪臭了?这个闻靘,平时看着话不多,怎么这么毒舌。
珞岚面上也有些挂不住,楞了许久才回过神来,笑道:“公子想必是对花粉过敏吧,珞岚的错,这样,珞岚坐的远一些,可好?还未请教公子和姑娘姓名。”
闻靘轻哼了一声,不做声。
絮濡沫只好回道:“他姓闻,我姓安。”
珞岚坐在不远处,挂着温柔的笑,低着头熟稔的焚香,烧水,洗杯,投茶,润茶,仪态雍容,气定神闲,“两位不是宁州人氏,是为竞仙大赛而来?”
絮濡沫转头看向闻靘,见他依旧是安静的坐在那,彷如一尊慈悲的佛像般,低着头,不打算回答。
絮濡沫叹气,“的确不是。”
珞岚继续着手中冲水和泡茶的工序,“不知安姑娘与闻公子是什么关系?可方便说与珞岚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