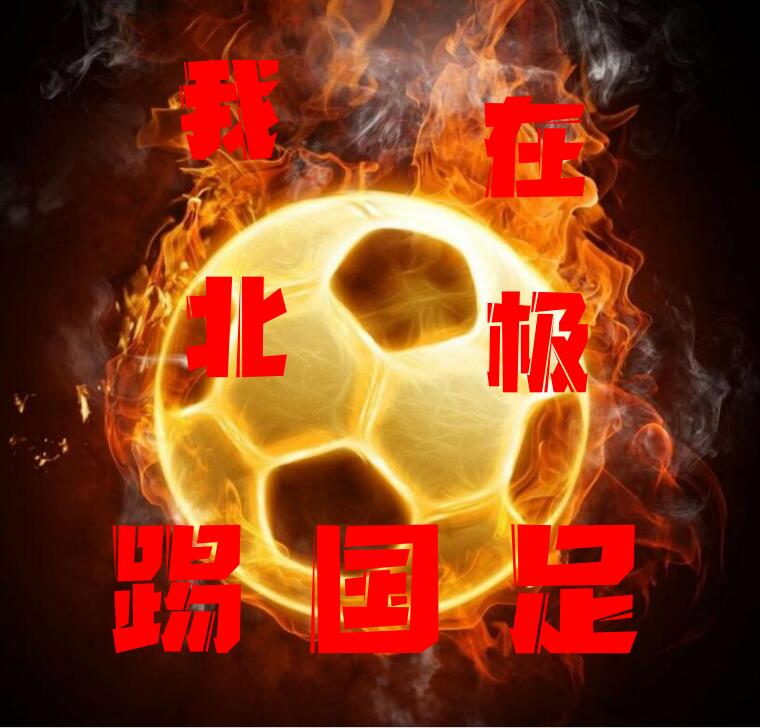原野蛙声一片。
左三年,右三年,这蛙声,沈恩衣记得,她的母校的老师和学弟学妹们在宿舍里的单人床上独自听了多少回?
沈恩衣问桃花眼:“零八那年你在哪?过得怎样?好不好?”
伍笔马没有想到沈恩衣会突然这样问,脑子转了许久后才说:“零八年,我高中毕业,一心计划去当兵,当时我们镇区总共才三人。三人抢两人的名额,我各方面不错,到体检那块却涮下来了,然后,就成了现在这样,住医院里。”
他讲完苦苦的笑,说:“沈恩衣,你呢?”
恩衣不愿地说:“零八年,雪灾了,年前回不去,年后回了又出来,雪灾过后又火灾,大火烧毁了我们村三分之二的房屋,这场火改了许多许多人的命,我的家也没了,突然就变得很穷。”
“你现在……”
“我现在,结婚了。”
“那个人,他有钱吗?”
“没有,他是我成人大学的同学。两个人都很穷。”沈恩衣说:“不然的话,我也不用坐错车,直接开车打导航过来医院就行了。”
伍笔马听了久久的沉默。
相传,晚上十二点的阳间是阴间的中午十二点,所以阳间晚上十二点人和万事万物的气都特别弱。
沈恩衣环抱自顾,她想赶走那刺骨的寒意。
桃花眼说:“进去吧,这地方可能会有蛇趁夜出来。”
他们走回医院的大花园,走进时光镜来到住院部的长廊,桃花眼突然止步不前,痛心疾首的说:“沈恩衣,我的一个亲戚,她也是在这家医院,住着住着就死了。”
沈恩衣吓了一跳,忙说:“别回了,我们又在楼下到处逛逛吧。”
“你会不会冷。”他问。
沈恩衣说:“不会,走路会暖和。”
实际上,沈恩衣她,千古寒的。只不过他看不出来。两人又慢吞吞的把医院各个角落走了一遍,又一遍,许多遍。
她以为她们会走一夜的。
可是太泠了。
当她和桃花眼走回病房时,邻床的两个病友已经睡了。入夜的医院走廟更加的静。
沈恩衣出了电梯门就脱了鞋。就算赤脚也要小心翼翼的,身怕弄出什么不好的声音。
桃花眼让床给她睡,沈恩衣不肯,她也让床给他睡,他更不愿。打着手势说他日睡夜睡脑袋都睡大成两颗了。
邻家病大哥早把帘曼拉上,沈恩衣把椅子搬过来放桃花眼的床边。眼一闭,六根清静。
早许多年前,她就学会这招了。
有一次,她在机场赶机,因为票点不方便,所以提前十二小时进票厅。
她所要乖坐的飞机第二日天亮六点才飞,而沈恩衣,已经下午三点就到,时间怎样都磨不完似的,等入夜,大厅的人走得差不多了,谁也不看谁。
她把包往长椅上一放,眼睛一闭,纷纷扰扰花花世界,它们全被挡在外面,与她再无关系。
沈恩衣在医院桃花眼的病床旁也是,她把眼一闭,就睡了起来。但她睡不着,因为她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
沈恩衣睁开眼睛,忧伤如目光的说:“小伍,你怎么不睡?”
“睡不着。”他说。
“哪疼了?”沈恩衣连忙坐正来问。
伍笔马指了指心,说:“这儿!”
沈恩衣仰起头,郑重其事的问:“小伍?”
“嗯?”
“你幸福吗?”
“不幸福!”
你幸福吗?
这几个字有无数希望隐藏在里面。
不幸福,这个答案也隐藏无数人生的感悟在其中。
最怕你不幸福。
你不幸福,沈恩衣哭了起来,她的泪直直的往下流。是又去到那个无休无止的疆梦里面去了,沈恩衣一直努力,想要把现在的每个日子过成将来不后悔的过去。
不幸福,是不幸福啊!
她告诉自己别哭,但做不到,那些泪就像可乐瓶倒掉后流出的液体一样自然而然,直到流枯流尽。
…………
“如果有来生,你想做什么?”
“云。“沈恩衣说:“小伍同学,你呢?”
“河。一条不老不伤,不死不灭的河。”
…………
医院的阿姨一年四季做着保洁员的工作,她每天都来病房换取床单,被褥,打扫卫生之类,她取了又换,换了又取,这一年,这样的事,她又重复做了多少次?
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沈恩衣望着她,一点点的收褥,一点点的收,怕惊梦似的。
是谁无情的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什么沈恩衣感觉一切皆去,满心伤?
她望着病房的边角那张空了的床,她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她也知道,从今往后,自己既使肯坐一村又一村的班车过来,也再寻不见她的同学小伍。
再寻不到了。
叶桠的妈妈在电话里隐忍的跟沈恩衣说:“恩衣,我们家的姨公死了,姨公去的时候我也在那儿,我们家的姨公和姨婆,一生好人呐,讲不尽道不明怎会得癌症那种病。
家里面的人一直瞒着老人家,直到当天晚上他病厉害了也不肯打电话通知我们,这次还是我自己感觉不好了去的。
我去到医院那,看到老人家全身都肿得跟水桶一样,他不能说话了,医生说他不行了,家里面的人才和他讲啊,他得的是和姨婆一样的病,是医不好的癌。
他的子女们问他‘如果你还有什么话就写出来,写不了做手势也可以。’姨公说他还有七万块钱的存款,交代完后事就去了。
唉,都成老人了,临了临了还那么痛,打针吃药,白受那么多罪。”
沈恩衣听了感同身受,思绪绵绵,竟一时无言以对。
叶椏的妈妈是许多个葬礼后才打电话告给沈恩衣这些事,那时,她既不能去喝酒也不能对谁痛哭一场。
癌症多可怕,似乎无往不胜。
不久后,叶桠的妈妈又打电话给她。
叶桠妈说:“恩衣,学校的老师,就那个叫权钟树的主任,也是得癌症走了,才四十几岁。”
沈恩衣问:“哪个?”
叶桠的妈妈说:“就那个会刻碑写字那个,他经常来我们家吃饭的,你忘了?”
“我忘了?我忘了吗?”沈恩衣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