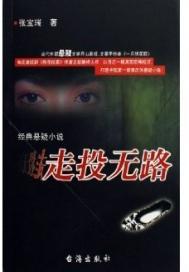徐迟
我不怎么读旧体诗词。它本来已经装进笼中,局处于一定范围内了。我不慎打开了笼子,把它放了出来。现在它繁荣一如往昔。新诗新作则至今没有格律,我不承认它们,只称它为“散文诗”。熊召政向来,我以为,是写新诗的,曾经为他的《瘠地上的樱桃》这诗集写过序文。今日得见他的格律诗,用了旧体诗词,他要我写序。且试为他作旧体诗词的集子—《闲人诗稿》写几句话,只能算外来人说点外行话,也算序。
打开这本诗稿,大别山脉挺立在眼前。这山很有军事上的名气,文艺上名气不大。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说的不是山,说的是仙。山有无名气,惟有依靠诗词来出名。四十年前我自北京下来,居于夏口,大火炉中。夏每苦热,无处避暑是非常痛苦的。那时我不知有羊角尖,不知有天堂寨,不知有桃花冲,不知有吴家山。直到这一次读了《闲人诗稿》,才想起召政曾讲过它们,称赞它们都是避暑圣地。但我均未去过。只是因为当时没有见到有关它们的诗句的诱惑。现在见到这些诗句,知道它们的凉爽和美就想去。然后悔不迭了,我未必能去了。来夏口时四十来岁,今已过了八十,已到晚年,何敢登山而望“海”?而召政却已在“海”里了。
八十,我的老年来得迟了些,犹似八十为“妙龄”。今年八十一,则正好来颠倒它一下:妙龄八十一,颠倒过来就是一十八。如今,民间流行着这样的话语:“世事可要倒着看。”譬如看报,就可以倒着看的。如所谓经济大好,当看清楚乃是某处经济欠佳了;又如说某事大有可为,其实正是某事之上出了大毛病,必发动起来,群起而攻之了。这些事,与我无关,我在这里说这个,只是为了主要是我要说“闲人”。要知“闲人往往是不闲的”,正相反他是“最忙的忙人”呵!此番就是他在百忙之中递过来这部《闲人诗稿》的。
光这一点就很不错。英国大诗人拜伦爵士也可以作为证人。拜伦他的第一部诗集就叫作《闲人诗稿》。一模一样,他亦非闲人。他亦不闲,为一个古国希腊的复兴而兴师动众,而写了许多闲人之诗问世,声震寰球。盖不忙就不知闲之珍,不闲亦不知忙之贵。他开了一辆车来接送我上招待所避寒,而当天就飞往海南岛的“海上”。三日后飞回来,说两小时后,翊日又紧接着飞去了深圳的“海上”。又三日而返,谁知他底事而如此之穿梭匆忙?不奇怪的,如今他已经是Busines**an(扎扎实实的忙于生意的人了)。然而居然又集成了一部《闲人诗稿》,共有两百零二首旧体诗词,发思今怀古之忧思,抒述山山水水之情趣。他哪是闲人?他下海了,他确是闲人?他进了山里了。这在后面详细说,一时还说不清楚的。
然而闲人还管闲事了。人是闲人,诗是闲稿,均不闲的。人有不等的闲人;事又有不等闲的事。举起森林般的手,他为此而写了新诗《制止!》,这闲事一管,从此天下多事!所谓一锤可以定音,音老早已经定好。闲人成为非闲人,虽然闲人可以自居,虽然自居闲人也是永远可以的。别人之事是管不得的,一管就管出了一个世界来,就是一劫。《闲人诗稿》扉页上就有了一句:“劫波度尽心仍钝。”这一劫管了十几二十年,还不知要管多久?这一个“劫”字呵!在《诗稿》中掷地自有金石声。金石之声有频率,震荡不停歇,从《制止!》一诗的发表,至二十四首七律(第三辑)谓之“劫波”,好诗就是这样产生的了。
《闲人诗稿》中佳句甚多,首首都有。第一首羊角尖,值得徘徊其下。其起句:“奇峰拔地傲苍穹。”奇峰引出奇句。贯穿一生的气概,惟傲字提纲挈领,则苍穹不可傲也。其结句:“万壑千崖寸寸红!”两个寸字就涌出亿亿万万都不止的“寸”字来。写的是奇峰,写的是红枫,其实是自己,也只是自已。起得好,结束得好,他十七岁时写的第一首诗句贯穿了他一生的。
《东湖行吟阁前有感》、《题梅》、《答友人》三诗及小注颇可一读,其中首句:“古国诗魂付劫波”,又见“劫波”,这也是贯穿古今的历史的不可逾越性。《制止》就是这样写出抛出的。新诗《制止!》,任人怎么说,是新诗的时代里的一声霹雳,响彻中华,它“浇出了中华锦绣林”。尽管现在大家都不再提它了,它是冻结在时代的冰层中了。也是新诗的骄“傲”。当时他这作者“独身风雪里,肃杀见精神”。新诗与旧体本是一家子,无论“人间情态年年改”,永远是“三闾遗风涕泪多”。几多小注都要紧,该入注还当加添一些。将来出书时,要做好编辑上的功夫。
《制止!》一诗,一发表就轰动了全国的,是他二十七岁时写的新诗。激起的冲击浪之大是从来还没有过的,一位省委副书记就此来问作者的动机何在?他要制止的势力,要出来反制止这首《制止!》之诗,在全国范围的激起了“制止”与“反制止”的冲突,结果当时是不了了之。而锦绣林是“浇了出来的”。不过,寒流还不断地从漠北刮来。我们还会多次地碰到它,这是大气象的变化,而气象终究要变化的。就是大变化快要来了。
总之,他一生之中,要遇到三次劫。他舅舅的事牵连他失学,回家乡劳役为第一劫。《制止!》一诗为第二劫。“马去羊来又一春,南冠遽变怆离情”,他被收审下狱为第三劫。而在这《闲人诗稿》第三辑中的狱中参禅确定了他余生的方向,“劫”字转化为“禅”字了。
他和夫人一起游了南岳衡山,在南岳的古庙里点上了香火,还留有劫中的惊梦,但展开在眼前的青翠山峰使他幻想到了蓬莱仙岛的酒壶(“古寺焚香惊劫梦,苍峰到眼幻蓬壶”)他有想法,要在这样的名山盖一顶草屋住下了……他在另一首诗中又想起“禅家活得无拘碍,尽日南山一局棋”了……次年游沅水,想起沈从文先生去世已有四年了,留下一个湘西的风物给他细看独看……当他下天子山的时候,“此生称意于山水,风月林泉送我归”……这一类的诗句,真是闲情逸致,可让读者自己细细读去,我不再多引了。但有一首《游庐山东林寺赠果一方丈》的诗,说:“禅魄归来觉愈迟”。这“觉愈迟”正好反过来看,愈迟则愈速,愈远则愈近,愈觉自己不及,不觉已经靠拢了。
就在这时,出现了《赠陈其明》的“十万缠腰豪客醉,东风老处看溪山”,他已经与商业发生了联系,终于下了“海”。不免生活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去了泰国的湄南河,过泼水节,去了东方夏威夷的芭丽雅城,去了**在六十九层楼上俯瞰港岛,他游了维多利亚海湾,而他的诗词也向这里辐射了。开始时,他还是有点摇摆的:
“攘攘人间世,飘然我独行。东林烟雨梦,西楚霸王心。半僧还半俗,弹富亦弹贫。词客多佳句,总向困时吟。”(《甲戌中秋抒怀》)
“投身商海作遨游,又赚钱来又赚愁。一个天生诗佛子,从来故意失荆州。爱钱偏又爱清高,避席常因浊气豪。还是去当闲士好,清风明月自逍遥。”(《经商一年戏作》)
到写作《定风波》时,逐渐地稳定了下来:“系梦儒林兴未央,年华四十谪仙狂。国脉忽惊商气动,寒士更弦只为赚钱忙。彩笔暂收心莫冷,前程转折亦何伤。贾客丛中当隐士,游戏人生好著大文章。”
劫转到了禅,禅又转到了商,正、反、合,商与禅是互协的,一切禅都能收下来,容纳进去的。
《闲人诗稿》有深刻的涵意焉。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