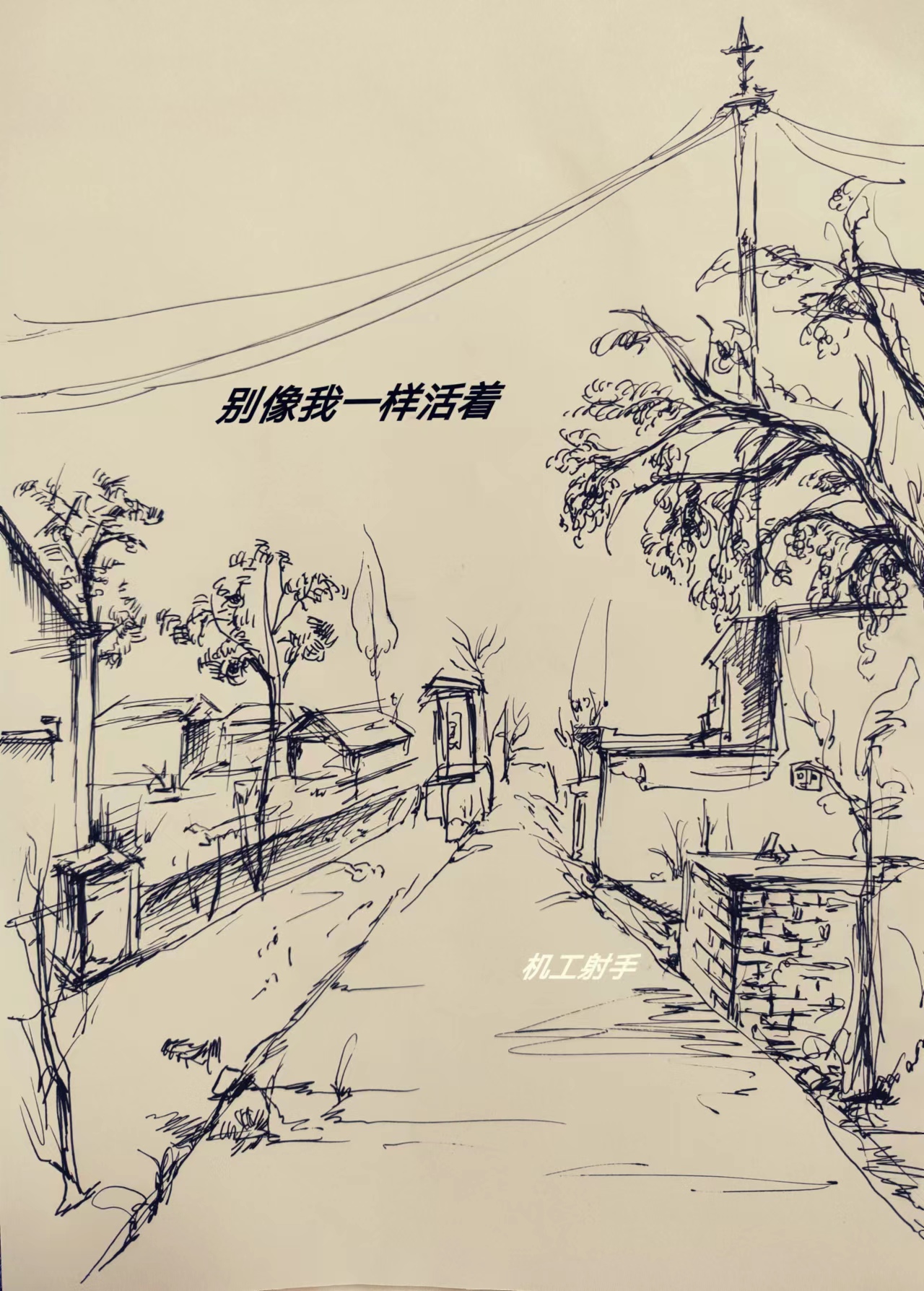第九节 小学时期朦胧的世界观
在初级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只有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没有科学知识内容,到高级小学的自然课和历史课中,初步学习了银河系太阳系等自然知识和从猿变成人、社会发展演变等历史知识,对学生进行初步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教育。小学自然课本也讲星系、恒星和行星的运动,也讲我们所处的银河系、太阳系和九大行星,只是不讲万有引力和运动的原理。那时的《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和《十万个问什么?》等课外读物中也宣传和解释一些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的内容。不过,那时的宇宙学与现在宇宙学也不一样,还没有宇宙的起源与大爆炸学说。我记得自然课上的刘老师给我们讲的宇宙是“空间上无边无际,时间上无始无终”的,似乎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观。
从社会上看,辛亥革命后,蓟县就“拆了大庙改学堂”,早就没有公开的烧香拜佛的场所了。但是在各家还是有祭祀神佛的习惯,信佛教的人家要供奉观音菩萨,信道教的人家供奉太上老君,信天主的人家供奉基督耶稣。我家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只是给祖宗牌位、财神爷和灶王爷烧香上供,还是相信有鬼神的存在的。1952年我奶奶病危时,我二叔和我三叔就轮流捂着我奶奶的天灵盖,以免老人家的灵魂出窍,被叫差的鬼卒抓到阴间去。到1955年以后,虽然经过政府多年的无神论宣传,但是中老年人的思想还是比较守旧的,不少人还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相信黄鼠狼、刺猬、狐狸和蛇等动物可以通过修炼“成仙得道”变成人形,有的道行小的也会“迷人”,控制人的意志。那时经常传说某某人夜间走路碰见“鬼打墙”了,也有的说走夜路碰见穿白戴白的女鬼了,也有的说夜里看见没脑袋的鬼魂了。还有说夜间走路途中遇到几个人赌博耍钱,他也跟着一起玩,赢了不少钱。听见公鸡打鸣,大家散伙了,这个人也回到家里,结果发现赢来的钱都是烧纸,原来是和鬼魂一起玩钱,因此吓出一场大病。1957年在我家租房住的县铁工厂工人卢世安就和我们说,1952年镇压反革命时,北京东面大路旁边有一处法场,经常枪毙犯人。一天夜里他们几辆大马车运货从那里经过,他正在车上迷糊打盹,突然听见骡马嘶叫,睁眼一看,见几个没脑袋的人正漂浮在路上,与他们车队同行。他当时也吓得冒冷汗,赶忙抽响手中的皮鞭,鞭声一响,那些鬼魂就飞走了。因为那时期民间也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有的人说自己亲眼看见鬼魂了,别的人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但也无力反驳。
过去民间也有的人对鬼神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我二爷孟宪增就这类人,他们不识字,没文化,从理论上说不出唯物主义的道理,无力反驳那些有神论的说法。但以他亲身经历,又从来没遇到过鬼神,也同意无神论的观点。所以他们就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没有邪骨头的人不中邪”。他们的观点是信鬼神的人就可能看见鬼,不信鬼神的人就碰不见鬼。黄鼠狼不可能迷所有的人,只能迷那些天生有“邪骨头”的人。说鬼神“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观点,实质上等于说鬼神存在于人的心中,而不是存在于客观世界。
古代的民间也有朴素的无神论观点,他们否认神仙鬼怪的存在,否认人死后灵魂不灭或需要投胎转世等观点。他们的观点是“人死如灯灭”,人和动物的生命如同煤油灯里的灯油,躯体如同灯具。出现意外的伤亡事故就如同灯具被摔碎,灯油洒在地上,生命和肉体同时消失了。病死和老死,就等于灯油耗尽了,生命消失了,肉体和灯具一样成了“空壳子”作废了。古话说“远怕水,近怕鬼”。远怕水,说的是因为远处来的人不知道眼前的河流深浅,水流下有无漩涡,会游泳的人也容易出现意外。近处的人了解了河流的情况,就不容易出意外。近怕鬼,说的是那些出现过凶杀案的路段,容易引起附近人们的恐惧感。外来的人不知道此路段有屈死鬼,也就没有恐惧感。因此,相信有鬼的人是自己吓自己。那些说自己走夜路见到鬼的现象,是人的幻觉,俗称“眼发离”。因为他们相信鬼神,才可能“眼发离”而看见鬼神,即出现鬼神的幻觉,不相信有鬼神的人就不会出现这种幻觉。他们说人被鬼魂“撞客”和被黄鼠狼“迷着”,都是一种心里疾病,也称癔病。说没有邪骨头的人不中邪,是因为没有迷信思想的人不会得这种心理疾病。可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旧中国,在佛教、道教和巫术的影响下,这种无神论观点无法占据社会的主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公开批判封建迷信思想,无神论观点也是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宣传报道的重点。年轻人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在农村的年轻人中,许多人的思想解放了,他们不但接受了无神论的思想,而且对清明节上坟烧纸,也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予以否定。
像我的叔叔们就如此,到1955年后,他们哥几个都不再迷信鬼神了。我曾祖母与我曾祖父合葬的坟地,在城西北面的大坨子。1955年我曾祖母去世后,我二爷孟宪增继承了房产,应该由他来操办三个“周年”(注1)。可是他也说人死如灯灭,上坟烧纸没必要,结果在1956年、1957年和1958年的三个“周年”,他一次也没有操办。没有像现在“办周年”这样,要有我曾祖母娘家的亲戚来参加,再把我们老孟家全家老小聚在一起去上坟烧纸,然后回来聚餐。不仅我二爷没有操办为自己的母亲过周年,我二叔在县铁工厂上班,三叔在北京打工,老叔在蓟县屠宰场打工,都没有请假回来为奶奶“过周年”。1956年我曾祖母“头周年”那天,就是西河套村我的姑奶奶、仓上屯我姑姑、及我母亲二婶等几个妇女到坟地去上坟烧纸,然后各自回家吃饭,也没有其他的亲戚来“做周年”。我和堂弟孟繁荣那时已经上学了,也没有跟着母亲到我曾祖母的坟地去。1957年曾祖母“二周年”也是几个女眷去坟地烧纸。1958年春季县里在城西北侧修建三八水库,这块地被划在水库里边,当时政府通知迁坟,我二爷孟宪增和二叔都是不信鬼神的,连每年清明节上坟烧纸他们都反对,自然不愿操办迁坟的事。我母亲和我二叔二婶,虽然觉得有些不妥,也说不出道理来。于是迁坟补偿费也无人去领,我家祖坟也就没了。曾祖母的三周年也没处去上坟烧纸了,后来也就无人给祖宗烧纸了。
我奶奶与我爷爷合葬在一起,那块地名叫“何家坟”,位置在城外西北面去下营官道的路西,也就是现在津围公路三八水库路段的西侧,西北隅农贸市场的北面,1958年公社化以后,这块地就属于西北隅的耕地了。因为城里的年轻人把上坟烧纸看做迷信活动予以否定,每年清明节都是我姑姑从十公里外乡下(仓上屯)婆家包来素馅饺子,带些烧纸给我奶奶上坟,开始让我和堂弟孟凡荣跟着去,我俩上学后,又让未上学的堂妹孟凡如、二堂妹孟凡珍跟着去。1959年吃食堂以后,没有上坟的贡品了,我姑姑也就不来给我奶奶上坟了。1961年5月集体食堂解散了, 1962年后的清明节,我姑姑还是从家里带来素馅饺子给我爷爷奶奶来上坟。这时我两个堂妹也上学了,我姑姑就让没上学的我二堂弟孟凡林跟着到坟地了。孟凡林上学后,我姑姑清明节来上坟,就让我三堂弟孟凡存、四堂弟孟凡义分别跟着到坟地去。到1966年开展破四旧活动,上坟烧纸钱都被认为是四旧,我姑姑也就不再来城里给我爷爷奶奶上坟烧纸了。
1970年冬季全县开展平坟运动,农田内各个高出地面的土坟头都被铲平了,但是地下的墓穴和棺木还保留着。
我爷爷奶奶的坟头无人每年添坟上土,肯定是越来越小了。还没等到1970年的全县平坟运动,就不像坟包的样子了。
1964年以后,白马泉大队、西北隅大队都为蓟县水泥厂提供制造水泥用的原料之一——黄粘土。制造水泥的原料有石灰石、黄粘土和炼钢厂的炼铁炉内产生的废矿渣。水泥厂自身的开山车间只生产石灰石,黄粘土和废矿渣都是买的。筹建蓟县水泥厂占用了白马泉大队和西北隅大队的一部分耕地,就把为生产水泥提供黄粘土的任务交给了这两个大队。每年秋后和春季,生产队就组织社员晾晒黄土,就是把高岗的土刨下来,铺在平地上,再把土块捣碎撒开晒干,然后用大马车运到水泥厂原料库内储存。水泥厂按每立方米土面几块钱付给生产队,这也是一项集体副业。
白马泉和西北隅的许多土地都成了晒土场地,何家坟这块地在大道边,是一块高岗子,于是就成了晾土场地,上面不再种庄稼了,用来这块地为水泥厂供土。不多几年,整块地都给挖平了,我祖父祖母的棺材和骨殖也不知被扔到哪里去了。生产队晾土不像修水库有迁坟的政策,有主的坟墓给钱迁走,无主坟墓就地深埋。生产队耕地里的老坟头没人添土和压“挂纸”(祭祀时放在坟头顶部的白纸条),就被视为无主坟墓了,整块地当土场了,在没挖到坟墓之前,有主人的就让你迁走,没人找的就视为无主坟墓了。挖出棺材板来,就当柴禾被人捡走了,遗骨保存较好的,在旁边地里挖个坑给掩埋了,时间长保存不好的残骸,也就当做垃圾扔了。
1970年冬季县里开展平坟运动时,并没有禁止人们上坟扫墓祭祀先人,而是要求各大队都划出一片土地建立公墓,同时各大队建立骨灰堂,社员病故后实行火化,骨灰盒一律存放在骨灰堂。那时社员家愿意把父母的坟墓迁到集体公共墓地的可以迁过去,只是那些多年无人祭祀的老坟头才被铲平了。可以说,在农村上坟烧纸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了。
而我们老孟家的人,我二爷孟宪增、我二叔孟庆华、三叔孟庆余、老叔孟庆宇,都是在1956年后接受了新思想,不再迷信鬼神了,也就不再去上坟烧纸了。我们这辈的弟兄姐妹们,也是自从上小学后,就不再跟着我姑姑去坟地给我爷爷奶奶上坟烧纸了,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认为上坟烧纸是封建迷信活动,小学生是不应该参加的。
应该说这种把怀念悼念已故的父母和祖先,与相信鬼魂存在混为一谈的观念,也是有历史根源的。古代人因为相信灵魂不灭而且就居住在坟茔里,才给故去的亲属上坟填土焚烧纸钱的。既然没有鬼神的存在,何必再去烧纸填坟呢?这也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那时并没有人认为这种不去上坟烧纸、放弃祖坟的行为是“不孝”。我在小学时政府还没有提倡丧葬改革,也没有禁止人们上坟烧纸,每年清明节县政府都要组织机关干部和学生去盘山烈士陵园扫墓。但是官方组织的祭奠革命先烈的方式与老百姓的传统方式不同,官方祭奠是低头默哀,是给烈士行鞠躬礼。官方宣传的是革命先烈的精神,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学习、继承下去,并没有说烈士的灵魂在阴曹地府里生活,需要我们给他们烧纸钱。所以,官方祭奠先烈先贤,和民间百姓相信鬼神是两码事。因此,那时在我这个小学生的心里就以为,既然人死后没有变成鬼魂,也不会在坟地里居住,也就不需要添坟上土和焚烧纸钱了,我姑姑每年来给我爷爷奶奶上坟,就是封建迷信活动了。
在这种社会背景和家庭影响下,我在小学时期也就形成了朦朦胧胧的无神论的世界观,这除了在学校听老师讲的自然科学知识外,对社会上的无神论观点,也被我亲身体会所证实。
因为我从小就是“夜猫子”,晚上喜欢出去看热闹,走夜路已经成了习惯。那时大街上没有路灯,小胡同里更是漆黑一团,我家也买不起手电筒,也没有照亮的灯笼,我们孩子们就是摸黑走,一边走一边说笑。有的孩子还故意装神弄鬼吓唬人,一会说“那边有个小白人”,一会说“那边有个小黑人”,吓的大家往一块挤着走。有的孩子还故意讲走夜路遇到鬼的故事,当时听着也是“心发毛”,头发根“发直”(毛骨悚然),也是精神紧张很害怕的。但是也有的孩子说:“那都是瞎说的,自己吓唬自己的。”还大声喊:“鬼在哪啊,你出来让我们看看。”当然也不可能把“鬼”给喊出来,时间长了,大家自然也就不相信有鬼了。
1959年之前,在西南隅村林家胡同居住的时候,晚上我经常和成志奇一块去大街上玩,看后半场电影或评剧,为了仗胆,我就带着皮鞭子。散场后我俩人从北面走进胡同,先到他家门口,他进去后只剩我一个人往南走。这时我经常想起我曾祖母说的,南王家舍粥时,我家大门两侧躺着许多山东来的灾民,每天夜里冻死好几口人的事来(注2),按说这里要有好几十个灾民的鬼魂啊,于是我就一边走一边抽鞭子。因为民间传说皮鞭子能避邪,开始时我以为皮鞭子啪啪的响声,就可以使鬼魂不敢出来。后来时间长了,一次也没有遇见过鬼魂,也就慢慢的不相信有鬼魂的存在了。
1960年搬迁到西北隅居住后,我家距离大礼堂更近了,走夜路的距离也短了,我就更不害怕了。
有一年冬季,三岗子村唱影,影台子搭在庄东北侧铁道西面的大场上,我们西北隅的几个小孩子去那里看皮影,一起去的有我们附近居住的孔昭银、王树仁、朱建民等人。那次三岗子唱影一连唱了好几天,我们每个晚上都去看。那次演出的皮影戏是《五峰会》,连续剧的演法,每个晚上演出的时间比较长,大约到午夜才散场。
那时城墙外边与三岗子之间还是一片庄稼地,我们从西北隅去三岗子要经过西关外的杀人场,也就是现在的东风宾馆那一片。过去这里是法场,死刑犯人砍头和枪决,都在这里执行,同时也是集市贸易的场所。每当路过这里时,大家也要说“有鬼啊”“来鬼了”等,戏闹一番,吓得走在后边的孩子赶紧往前边走。有一天夜里在三岗子看影时下雪了,有的观众就回家了。因为下雪不同下雨,把落在身上的雪花拍打几下也就没事了,所以一部分人还坚持看。唱影的不怕下雪,影台子是个小屋子,有人看他们就继续唱。我们一起来的几个人都说下雪了太冷,不看了回家吧。我的兴趣大不愿走,孔昭银他们几个就回家了,西北隅来的就剩下我自己还继续看,直到散场我一个人走回家。这场雪下的还不小,午夜皮影散场时,地面已经积了四五厘米厚的雪,地面房顶上全白了。我一个人从三岗子回来,心里也有些害怕,尤其是经过西关外杀人场时,必然要想到这里有过许多无头的尸首。但是心里还是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鬼的,不必担心害怕”来鼓励自己,顶着雪花踏着积雪走回家。到家时一看马蹄表,已经是零时二十分了,等于我一个人在半夜回家的。
正由于我从小贪玩好看热闹,经常走夜路,才使我的胆量越来越大,逐渐的不相信鬼神了。虽然那时还没有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还不知道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哲学观点,也不知道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也不知道生命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但是以我的亲身体会,认为无神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少年时代初步形成了无神论的世界观。
注1:清明节与过周年,北方人的坟茔都是土堆成的坟头,蓟县的习俗,每年的清明节要到坟地去祭祀亡灵,要摆上供品和焚烧纸钱,并且要给坟茔添一层新土,以避免坟头被雨水冲刷而消失。人死后满一周年纪念日、二周年纪念日和三周年纪念日,要举行祭祀活动,自家人和亲戚们都来参加,来客要带烧纸和份子钱。大家要到坟地去上供烧纸,然后举办宴会大家聚餐,俗称“过周年”。第四年后的逝世纪念日称为“祭日”,不再举办祭祀活动,但是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去上坟烧纸。
注2:冻死的灾民,详情在本文第二章老城轶事中第七节:遭灾百姓与南王家舍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