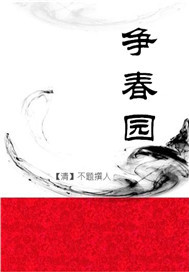从牡丹大家族中数以千计的国色天香,我认识了洛阳。一座风流妩媚之城。历千年兵燹、百回战劫而不毁灭的那些锦绣之根,现在更是春笋般茁起,轰轰烈烈地撒娇吐艳。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吸引了万国衣冠。
从“风回铁马响云间”的齐云塔;从花龙透雕、古柏森森的白马寺;从造像十万余尊的龙门石窟,我认识了一个坐在莲花座上的洛阳。这洞天佛地之城,有多少花宫梵寺。三千世界的高僧驻锡于此,意将辚辚的战车旋成常转的**,把咽下的黄河涛声吐成伽蓝的暮鼓晨钟。
从邙山大冢认识帝王将相之城;从升仙太子碑认识出神入化之城。侠骨剑气之城,倚在关林仪门前的铁狮子肩上;兽形怪物之城,幽禁在王城公园内的西汉壁画墓中。盘桓几日,洛阳如历史的万花筒,让我目不暇接。喜欢清静的我,来此竟不得做猿鹤之梦。为了要在这文化沃野的中州找到我的情结,找到一个儒雅淡泊的洛阳,因此我来香山。
香山在洛阳城南十几公里,隔着清清伊河,与西山的龙门石窟比肩而立。与西山相比,这里的游客少得多了,及顶上到琵琶峰的,则少之又少。
琵琶峰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墓地。沿琵琶峰以下的香山一角,围墙圈禁,僻为白园。
香山本是龙门东山,因地产香葛,故名。北魏朝廷在西山大凿窟龛的时候,东山也随着建起一座规模巨大的香山寺。临山起屋,依山凿佛。一时间,东山五色渥彩,胜景辉煌。洛阳城中的钟鸣鼎食之家,那年月,莫不争当香山寺的施主。
烽镝洞穿了富贵之梦。到了唐初,香山寺已钟磬寥寥,残破不堪。武则天执政后,采纳武三思建议,重修香山寺。东山又一度天花乱坠,香火旺盛。再过一个世纪多,等白居易来到洛阳接任河南尹,香山寺又因风流云散,年久失修而门可罗雀。对这一块鱼龙寂寞的山水,白居易可谓是一见钟情。他拿出为老友元镇写墓志铭所得的六七十万金,开始他三修香山寺的壮举。至此,东山的游踪才少了一些显赫的王气,多了一些飘逸的灵气。香山寺第三次的佛界,为诗人而开!
佛界里的尘心,是白居易的;尘心里的佛界,是诗人永恒的理想。自号香山居士的白居易,从凝滞着忧怨琵琶声的浔阳古渡;从落红委地,香消玉殒的马嵬坡前;从卖炭翁蹒跚而去的泥泞的官道;从新丰折臂翁四壁萧然的破屋,他寻寻觅觅,才终于找到这座香山。这位鸡肤老人,从此隐居于此,遗嘱葬于此,灵魄永栖于此。
自古的中国,通邑大都,繁华市井莫不属于王侯,属于将相,属于公卿大贵,属于风流巨贾。而深山老林,远浦孤村则为头陀、为道人、为哲人、为诗人而生。城市的精气塑铸一尊又一尊铜驼,山川的灵气涵养一颗又一颗真诚的心。
如今,在王气氤氲的九都故都,在这香山,那颗真诚的心,越过迢递时空,烟尘四合的历史,贴近我的胸腔。两颗心在同一种节律中搏动起来,他的和我的。我想,所有的诗人,不仅仅是诗人,应该说所有的中国的仁人智士,来这里,心都会跳动在一起。因为他们从古到今,从今天到未来,都有着一脉相继的真诚。
白诗人,我想你不会哀叹,说你的墓园比起洛阳城下的关陵过于寒酸。如果说关将军的陵丘算是死后一抔土,你的陵墓当然只能说是一撮微尘了。一支狼毫比起一把青龙偃月的大刀,在中国重门深禁的历史中,毕竟分量太轻太轻。我想你也不会生气,说你园中的牡丹太少,而且,对着你墓冢盛开的牡丹,也没有珍奇的品种。谁叫你当年那么忧伤地写着“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呢?深色花是大富贵,大富贵从来与诗人无缘。
站在这里,和四月的艳阳一道,和自魏晋就堆在那里的乱云,自唐自宋就一直纤瘦却还不至于衰竭的伊河的水声一道,对着你的墓碑肃立。远处嵩峰的烟雾,如青绡一袭,束着故国河山,也束着我的怅望千秋的思绪。我不是天涯沦落人,但同你一样,天不赐我操刀之手,却掷我一支忧患之笔。我们同是化民间疾苦为笔底波澜的饶舌者。只是我不能像你一样归隐,我的心尚热,我的血不会冷。
白诗人,是谁把你的陵园修葺成一张琵琶的形状?嘈嘈的大弦在哪里?切切的细弦在哪里?无声的肃立中,我想听铁骑突兀,我想听珠玉相撞,我想突然听到裂帛一样的心音。我终于失望,攥出汗来的手心里,只有寂寞孵出。走了的白诗人,你是不肯回来的。你只把一大把没有写尽的忧患留给我,留给我们这些后来者,只把这春雨秋风的白园留给洛阳。
走出白园,回望琵琶峰,不知怎的,我觉得它更像一方古砚。聚五岳的松烟为墨,磨黄河的浪,在那古砚里,研出民族的浓汁来。我想,蘸这样的浓汁写出的诗篇,必定可以惊天地,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