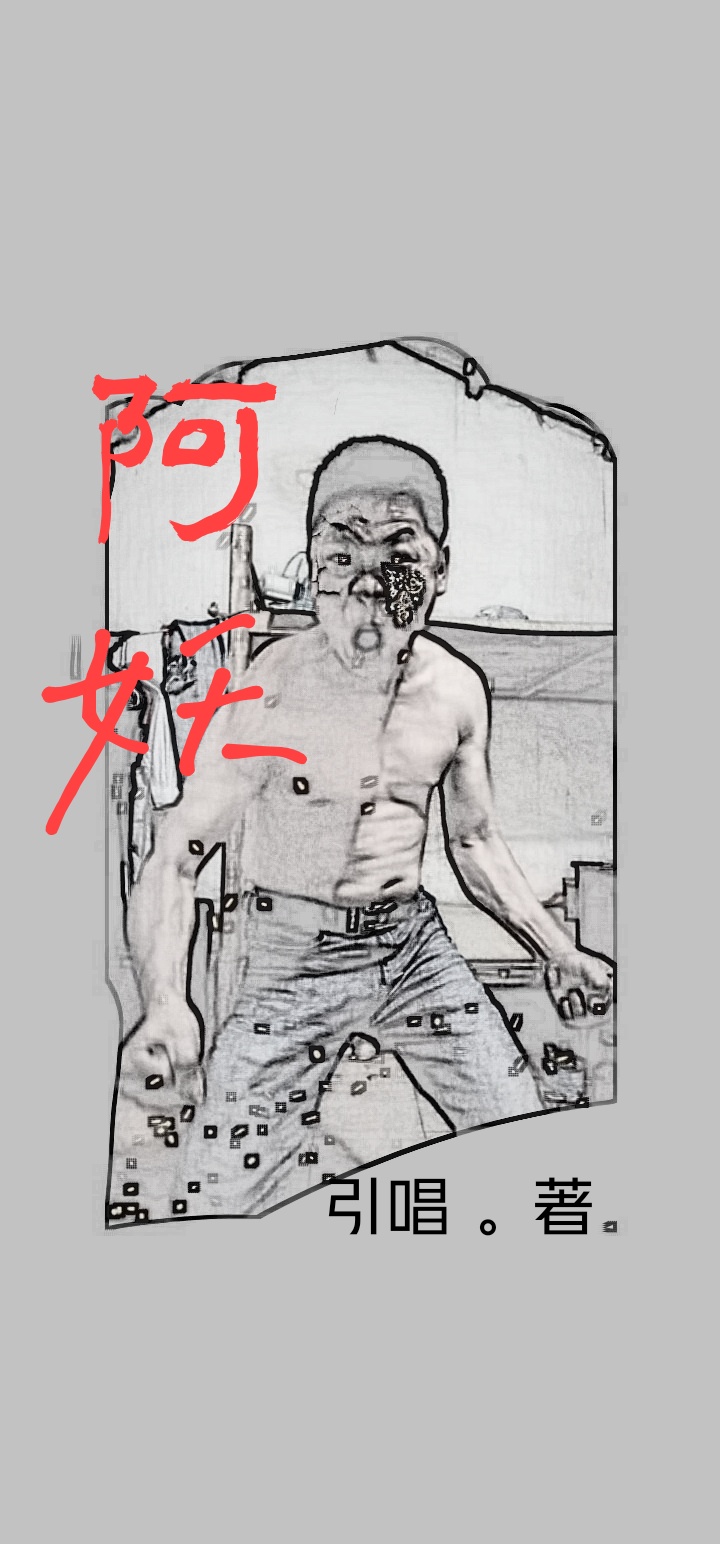话说云阳公主在魏文、魏灵的保护下,一直躲避在那个远离尘嚣的小乡村。小乡村的村民虽然都是逃难的落迫贵族,但村民之间的邻里关系都很融洽。
刚来前几天,出于安全考虑,魏文魏灵总是大门紧闭。那几天总有个十多岁的小青年提着在山上打来的野味放在门口处,魏文没有收下,而是送给了经过的村民,顺便跟村民问起了那少年的情况。
乡民都道那小青年十七八的模样,两年前自己一个人来到这山村,从未见过有什么家人,就住在村东头最破败的草屋里,村里所有逃难的人就数他最落迫,好在有一身武艺,靠打猎为生。为人挺好的,每个刚逃难到这里的人,他都会将打来的猎物分出来一半给人,村上比他迟来的人都受过他不少好处。魏文悬着的心终于稍感平稳,决定今晚去会会小青年。
夜色渐浓,村东头一间落败草屋内,一点星星般的烛光从无处不见的缝隙间透出屋外。那小青年正坐在桌上边擦拭着桌子上的弯弓,忽然察觉屋外有异响,转身翻过桌上的另一边,抓起挂在墙上的箭袋,拨出三支箭,搭满弓,一放,三支离弦的箭旋转着朝屋外的来者飞射而去。
“噹噹……”三声,三支箭落到了地上。“公子好箭法,不过公子不必惊慌,我是刚搬来的那一家四口。深夜才有空来拜访公子,以谢公子赠送猎物的好意。”
屋内那小青年赶紧从屋内出来,拱着手道歉道:“不好意思先生,不知先生夜里拜访,方才多有得罪,还请先生见谅。”
魏文看着眼前的小青年,不仅武艺超群,而且谈吐文雅大方,也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怎会落迫到如此?正想着问问小青年,小青年倒着问起了魏文:“先生何故落难到此呢?”
魏文被这忽然的提问毫不作心里准备,顿时语塞,支支吾吾地说:“我本是新郑城的一商户,眼看战争就要爆发,所以才带着家眷逃到此处避难,待到局势平稳时再回去经营!”
“从公子谈吐与武艺看,公子也是来自富贵人家,怎会落难到如此田地?”魏文反问着。
“我叫赵宇翔,齐国人士,家父原是战功赫赫的将军,被朝廷贪官陷害,落个满门抄斩的境地,我逃了出来,被追杀才落到此处落脚。”小青年泛着红眼说:“家中七十多口,现在只剩自己,我想不明白,我家兢兢业业,为国分忧,到最后只落下了个家破人亡的境地。”
魏文安慰式地拍了拍赵宇翔的肩膀,满眼都是怜悯之心。
“怪不得赵公子的提防心那么重,幸好我也有点武艺功底,换作了别人,身上还不是多了三个窟窿。”魏文半玩笑着说。
“先生大可不必担心,在下也从先生的脚步声估摸着先生有点武艺功底,又没杀气才射出三支简单的旋箭,如果是换作鬼鬼祟祟的脚步声,那我可能射得不是这三支了。”赵宇翔说着又有了点笑容。
“赵公子箭术果然了得,既然赵公子孤身一人,不知赵公子可愿到我家做我女儿的侍卫,保护我女儿,顺便教教我女儿射箭呢?一来可以彼此照应。”魏文满脸诚恳地说。
赵宇翔双手抱拳拱着手:“定不负先生的知遇之恩。”赵宇翔很坚定的眼神望着魏文,逃难两年多来,从来没有人如此这样对待过自己,哪怕交流都少,刚来这小村,自己也努力着想融入,但村民个个都保持距离,生怕有什么霉事会惹上自己。今天这魏先生不仅来接触自己,还收留到他家,那还不粉身碎骨都要报答他。
“等我收拾一下行礼。”赵宇翔望着魏文道。
魏文看了看四墙徒壁的房子半玩笑着说:“公子还有行礼能收拾的?我那什么都有,公子只身前往就行啦。”
赵宇翔面带腆色地望了望墙:“只有弓与箭了。”说着背上箭袋,提着弓跟魏文消失在这漆黑的夜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