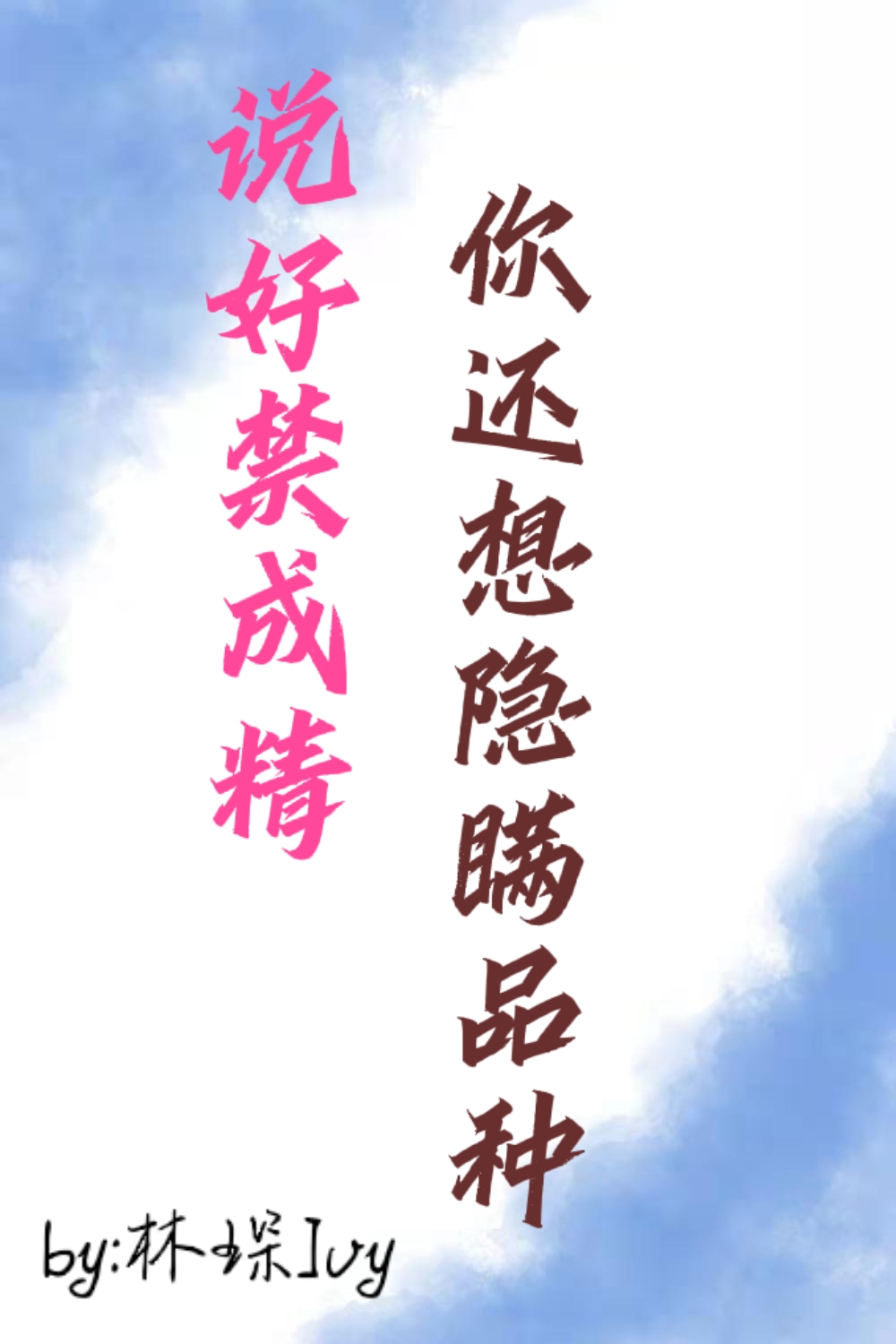文斐隔着墨镜和挡风玻璃目送集装箱车摇摇晃晃走远,右手始终握着变速杆;文松兴趣盎然地端视着他墨镜下被厚厚纱布包裹着的鼻子,有点想笑出来的意思。
“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直觉得好听。”文松调大车载音响音量。
文斐依旧出神地望着那辆车。
文松凑近他耳朵,突然大吼一声:“哈!”
文斐缓缓扭过头,恨恨地看着比自己大11岁的哥哥:“李荣浩<不将就>。”
文松摇头摆脑地跟着旋律哼哼,文斐从兜里拿出一包万宝路,垂下头在储物盒里找到打火机。
“出来抽,雨停了,”文松顺手抽出一支后打开车门,“车里有味道就当不了凯子了。”
文松走到车前用衣袖揩开引擎盖上的积水,一屁股坐了上去:“对了,俞家那个小妹妹到手没有?”
文斐一言不发,吸烟的频率较文松慢一倍,但每一口都是深吸。
“你不是打篮球的?吸烟没事?”
“……那些是什么人?”
“不认识。”
“为什么要我过来,你的人呢?”
“出糗的事被外人看见不好。”
“那我这个呢?”文斐伸出食指按住鼻子。
“那是你出糗。”
“……”
文松弹掉烟蒂,抬头望向依旧被乌云笼罩着的天空,暮色将至,风压低树枝,旷野间零星的建筑愈发显得荒凉。
“这他妈是什么地方?”
“GPS定位是越前镇,离镇上还有几里路。”
“送我回家。”
“哪个家?”
“从繁殖学的角度成年男性的家一般是定指。”
文斐保持60公里的时速行驶在路况一般的公路上,不管吸烟还是驾驶的习惯都显得少年老成,因为光线变暗已经取下雷朋墨镜,露出的额头比平常干燥一些,眉间有轻微痘印。
副驾驶座上文松喝着车上的苏打水,不时操作音响反复播放刚刚那首歌。
“刚刚你算是被绑架了?”文斐瞟了后视镜一眼。
“严格计时的话只是被限制人身自由。”
文斐稍微踌躇地问:“以前……有没有这种事情?”
“好像没有,所以这个对你来说属于黑天鹅了?”
“什么黑天鹅?”
“17世纪前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在澳大利亚找到了第一只黑天鹅。”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义,所以我除了绑架人也会被人绑架,接受不了就好好上你的学吧。”
文斐用提速表达不满,文松瞪了瞪眼调大音量。
“文继民最近心脏不好。”
“住人家的房子用人家的钱就好好管人叫爸爸,你这种叫半吊子。你妈呢?”
“正常。”
“……好了我有时间就过来。”文松脸带不耐地摆了摆手。
半小时后,白色福特锐界停在名为“左岸”的住宅区门前,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你今天是不是差点就死了?”文斐突然问。
已经拉上门把手的文松回过头,讪笑看着这时才真正放松下来的弟弟说:“是不是觉得很刺激?”
文斐摇摇头,双手从方向盘上滑落下来。
车门打开又关上。
文斐将音乐关掉,换档起步。
文松打开房门,放下手里捧着的三个包裹仔细辨认,从寄件的地址判断两件是衣服一件是鞋子,都是妻子网购的东西。墙上白色的电子钟指向6点45,职业是银行高管的妻子应该正在如常加班,文松感觉到饿,打开冰箱取出咖喱牛肉口味的速食米饭,准备拆开时又犹豫了起来,考虑再三还是放回冰箱,然后分别从保鲜室和冷冻室取出了盒装的青椒丝和牛肉丝。
做饭期间内手机很是识趣地没有响过,文松将青椒牛肉丝和油麦菜汤端上饭桌时瞥了一眼几分钟前金先生发来的微信消息:好好休息两天。
文松抬了抬眼皮,开始吃饭。
9点23分,沐浴后换了一身栗色风衣的文松走进闹哄哄的“龙宫”酒吧,经过在LED屏的海底背景前旋转跳跃的钢管舞女郎,避开从舞池里晕头转向撞来的红男绿女,径直走向一点钟方向的卡座。
卡座里坐桌子上摆着一瓶波士金酒、一个冰桶和两个杯子,桌子后面上了年纪的男人将杯中的烈酒一饮而尽;尽管两鬓泛白,但是不管绅士装背带下发达的胸肌还是豪饮的气势都张露出此人旺盛的精力。
“贝吉。”
“阿松啊,坐。”绰号“贝吉”的男人放下杯子。
文松落座,贝吉往空杯中倒了三分之一的酒,夹了两块冰块。
文松感慨道:“你还记得我的口味?”
“开酒吧的,属于职业习惯。”贝吉姿势优雅地收回酒瓶:“其实这里离你们公司很近,主要是见你一面不容易。”
“我在公司的时间不多,个人也不太喜欢喝酒。”
“托词。”贝吉将酒杯推到文松面前,爽朗笑道:“既然不喜欢喝酒又亲自过来,应该是有大单上门了。”
“大倒不见得,有点急。”文松从衣服内袋里掏出纸条和银行卡,沿着酒杯移动过的规矩推了过去:“清单和订金。”
贝吉看了一眼纸条,视线在纸条和文松两者间交互切换数次,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有一点我不明白,这是蔚然要的,还是你个人?”
“很重要?”
“当然重要,如果只是几把枪倒无所谓。问题是军用级别……说实话一是不好弄,二是卖给个人风险太大,行规你清楚,四级以上一般只走B2B。”
“可以加价。”
贝吉摇摇头,将纸条和银行卡推回文松面前。
“这里不是墨西哥。就算是蔚然要,我也要见金先生。”
文松不紧不慢地呷了一口酒。
“贝吉,我尊重你们的行规,问题是有些事正因为考虑到B的难处,才必须在C的层面了结——这是我们的行规。”
“那就没办法了,抱歉,”贝吉摊开左手掌:“只要是在这行混的都不可能接这单。”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鬣狗的?”
贝吉眼中闪过一抹厉色。
“和那种疯子做生意,你不怕黑吃黑?”
“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
“我负责西南片区这么久的理由只有一个——我虽然贪杯,但是脑子清楚,如果你招惹那种人进场,可就不止坏了规矩这么简单。”贝吉咬紧牙齿低声道。
“所以坏规矩总比坏大局好,加价两成,两天内要货。”文松起身。
贝吉重新拿起纸条,声音有几分气急败坏:“等等,这个当量的Black gold……你究竟想干什么?!”
“总不可能用来做善事。”文松回头笑道:“我是黑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