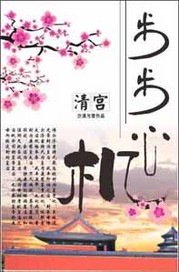夏日的天自瑖若走后,一天天燥热起来,知了没完没了地叫个不停,人心也烦闷不堪。
来到临水阁已经大半年了,从未听人提起过关于皇宫的任何消息,怀衫有些心焦,练剑也心不在焉,几次戴云辉站在了身后,她也毫无知觉,剑尖再前进一厘,就能触碰到他的鼻尖,每到这时,怀衫总是一个激灵,连忙清醒过来,继而周而复始地走神,失误,心里烦躁,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像自己亲手挖了一个坑儿,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点陷进去而没有丝毫的自救办法。
因为她是护国神相薛籽鑫的女儿,秋碧曳临终前对林椴衣说,让他隐瞒这个秘密,不要让她知道后孤身一人到皇宫里去寻仇。
思绪又一次飞到了九霄云外,“哐当!”手里的剑被震在了地上。
“林椴衣中秋节要回临水阁一趟,这些日子你要加紧训练,我这个师父可不能输给了你那个父亲,我要让他看看,我戴云辉教出来的徒弟,绝对比他强!”
“林椴衣要来临水阁?”怀衫只觉得脑袋里一震,嗡嗡嗡嗡地只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林椴衣要来临水阁!“
她还没未成功进入皇宫,林椴衣却已经寻来了!
既然逃不掉,那就勇敢面对吧!
心里打定主意反而能够静下心来,静静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审判。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浩淼河面,烟雾朦胧,一叶小舟顺着流水,徐徐漂入帝都,一个人、一壶酒、一轮月,林椴衣微微有了些醉意,蓦然想起,凌烟楼上一袭白衣俏生生的“公子哥儿”,今生只打过三次照面,却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也无法释怀那份浓厚的歉意和追思。
料也觉、人间无味。
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
林椴衣在中秋节当夜,到达临水阁。
每年这个时候,戴云辉都会在道场中摆下二十来桌,聚集所有因家不在皇城而无法回去相聚的弟子。
皇宫里照旧每年都会赏赐十几盒月饼,吃着御赐的月饼,与徒弟们举杯共饮,同赏明月,每待此刻,戴云辉总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惬意,天涯共此时!
怀衫安分地坐在师父身边,一手紧紧握着酒杯直至骨节发白,用疼痛迫使自己清醒冷静。
十几年如一日的一袭白衣,月光下拉的斜长的影子有些凌乱,摇摇晃晃地朝他们走过去,怀衫本能地上前去将他扶住,“爹爹,你怎么又喝多了?”
九岁以前,无论喝多少酒,怀衫都未见他醉过,娘死后,一切都变了,每次饮酒,他必定会酩酊大醉。
月光给每个人披上一层淡淡的霜华,几个月未见,怀衫突然发现,林椴衣老了,憔悴了,双鬓已染上了些许白霜,仿佛昨日,潇澜河畔,风陵渡,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竟已这么遥远,世事苍茫难料,她忽然感到难以抑制地悲伤。
林椴衣目光迷离地看着她,嘴张了张,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衫儿不好,衫儿不该不辞而别。”
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苦闷在清凉的中秋月夜稍微有所减轻,是什么时候林椴衣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那个秘密的呢?
应该是自己第一次逃离的时候吧?
在娘死后半年。
他们俩,一个纵容,愧疚,一个逃离,怨懑。
“衫儿,你竟来到了临水阁,这不是天意么?天意让我们父女再次相见,这就是断不了的父女缘啊!以后你想去哪儿,我绝不阻拦,只希望你此生能够平平安安。”
戴云辉不禁叹道,眼前这个人果然老了,以前的他,恣意洒脱,说话怎会是如今这个样子!
皇宫里的中秋节,气氛有些凝重。
自从太子回宫后,一众宫女太监已经提心吊胆地过了两个多月,每一日都谨小慎微,生怕一个不小心,屁股就被打开了花。
太监小圆子低头躬身地提着一袋子的碎瓷器片儿,不远不近地跟在太子身后,心里叫苦不迭。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太子带着他翻遍了皇宫所有的瓷器,就是没发现一个同破掉的一模一样的。
一向翻云覆雨的太子,也有不遂心的时候,眼见他脸上的阴沉越来越重,小圆子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上,只得哆哆嗦嗦地跪下说道:“奴才斗胆提议太子殿下,或许禹州钧窑烧瓷大师苏倾白有办法烧出一个一模样的花瓶。”
太子猛地把他拉起来,雀跃道:“小圆儿,不亏我平时这么喜欢你,快传令请他进宫吧。”
“可是,殿下、、、”小圆子有些犹豫,吞吞吐吐地说:“今儿是中秋节,禹州距离皇宫至少也需要一天的路程,不如小的将花瓶碎片送过去,待苏大师烧好了,再带回来?”
“小圆子,烧制一个花瓶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奴才不知,这得看器形、花纹难易等。”小圆子又一次胆战心惊地跪了下去。
“你先下去吧,我一个人去花园走走。”
小圆子提着气,小心翼翼地走开了。
没过多久,太监来报,瑜妃娘娘在锦园宫设宴特地请太子过去赏月。
太子冷哼一声,“不去!”
“太子殿下,中秋佳节乃是合家团圆的时刻,普通百姓家里,尚且一家人其乐融融,吃饼赏月,今儿皇上难得放下政务,欲与子女一享天伦,太子可不要扫了大家的兴才好!”
迎面走过来的女子,端庄地行了个礼,整个皇宫,敢以如此口气不卑不亢地跟太子说话的宫女,除了御前奉茶的谢冰展还有谁?
太子无奈地看了她一眼,脑子里灵光一闪,猛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我记得你说过,你是翼阳谢家的?”
冰展不知他何以有此问,简短答道:“是”。
“好!”太子将手里的袋子递给她,“这是你妹妹送给别人的一个花瓶,你看曾见过不曾,能否将它原原本本地画出来,我着人再烧一个。”
冰展走近桌子,将碎片倒出,虽已经习惯了他的鲁莽蛮横,当她看到花瓶碎片时,还是发出一声惊呼。
“太子啊!您是造了多大的孽啊!这么好的一个花瓶竟被你打碎了?”
“再好的花瓶能有皇宫里的好吗?”他不屑地说。
“宁璎怎么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人呢?这个荷口天球瓶原本有一对儿,是娘在烧瓷大师苏倾白家中相中,费了好大的劲才求来的,说是以后给女儿们做嫁妆用的呢,殿下,您可真是暴殄天物了!”
太子顾不及她的抱怨,却抓住了她话中的重点,“你是说,还有个一模一样的?”
冰展愣了愣,知道改口已经来不及了,态度坚决地说:“还有一个,但我不能给你!”那可是谢家女儿的嫁妆啊!她在心里坚持道。
“好妹妹,你就把它给我吧,你要什么,我都愿和你换!”
冰展冷笑道:“我想要即刻离宫回家,立刻坐到家人身边,殿下您能做到吗?”
瑖若讷讷到,“即使我向父皇求情,你回去西南至少也要十来天。”
“那我想当太子妃,您能做到吗?”
太子看她一脸认真的表情,脸色微红,随即明白过来自己被耍,正了正脸色道;“大胆谢冰展,竟敢调戏本王,你不想活了吗?”
“调戏?呵呵!女婢可不敢调戏太子殿下!”谢冰展抿着嘴轻笑起来,周围随身服侍的宫女,也微低着头,面色怪异。
“好妹妹,我知道你是最温柔,最体贴,最大方,最善良的了,你一定要救我于水火,把这个花瓶送给我啊!”太子索性抓起她的胳膊摇啊摇,撒气娇来。
谢冰展叹了口气,“殿下要的东西,冰展又怎会不给呢?只是殿下记得今日说的话,日后若冰展有做错什么的地方,还望殿下开恩。”
“我就说父皇如此看重冰展妹妹是有原因的,咱们去锦园宫吧。”太子说着,亲昵地拉着她的手,被她一把甩开了,“殿下如今也大了,这样与宫女拉拉扯扯,被闲人看见乱嚼舌根子,传到皇上耳朵里可不好,以后还是注意一些吧。”
太子知道她是为自己好,笑嘻嘻地垂下了手。
锦园宫的花园凉亭里,远远传来温声笑语。
小公主康玉铃远远看见他来了,欢笑着扑进他的怀里,“太子哥哥,抱抱。”
太子极不情愿地将她抱进怀里,“都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人抱,羞不羞!”
瑜妃坐在皇帝的左侧,正对着他们进来的方向,略施粉黛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双手有意无意地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腹部。
太子抱着玉铃,没有行礼,“儿臣给父皇请安了,见过瑜妃娘娘。”
“今儿月色甚好,若不是妾身将皇上请来,太子殿下也不会光临妾身的锦园宫,妾身还得好好感谢皇上呢。”瑜妃说着,晃晃悠悠欲要站起行礼,忙被皇帝扶住了,“你既身子不方便,也不易饮酒,就好生坐着,咱们一块儿赏赏月,叙叙家常。”
“父皇倒是很体贴。”太子漫自说道,将一颗晶莹剔透的葡萄剥了皮塞进小公主的嘴里。
瑜妃满意地笑了,一如今晚的月亮般莹亮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