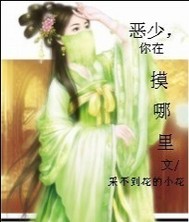怀衫在行进的过程中做了一顶黑斗篷,一来可以遮遮太阳,二则程皓不是飘来的警惕眼神让她有些心烦,虽然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被他盯得久了,也会产生不安,这不安让她对于自己的身世产生了一丝踌躇。如果自己以前是个十恶不赦,大奸大恶这人该如何是好?这额头也不知是怎样撞伤的,莫不是夫君一怒之下将自己推到,可她怀了他的骨肉啊?
一路上,她面上虽然镇定如常,心里百转千回,最终索性眼不见为净,就算自欺欺人,也好过无端妄测。
方才在打斗过程中,她被迫摘下斗篷,此刻重新戴上。帽子底下是一件月白薄衫,着实与这晦暗的颜色有些不搭,因此多多少少吸引了几分场中人的注意力。
皇帝、太子和秋褚宫宫主亲自下人迎接远道而来的盟友,几位首领彼此紧握住手寒暄了一刻,赶紧安排众位弟子的歇脚点。
秋褚宫一下子增添了数万众人,将幻月山填塞地满满当当,又因男人居多,女子进进出出多少会有些不方便。是以晚池在他们来之前就已将僻静处的竹林馆腾了出来,让夫人将所有的女眷迁移了进去。
怀衫于是很荣幸地被宫主夫人领进了竹林馆。
宫主夫人程氏单名一个敏字,正是程剑派掌门的同胞姐姐,现年五十有几,看起来到像刚进四十。
程夫人年轻时以古灵精怪闻名,五岁时于自家遇见在武林大会上将擂台当戏台,捉弄终生无数的秋褚宫宫主唯一弟子,十三岁的秋晚池。
晚池断不会想到自己刚刚赢来的美名就葬送在了这个长得像糖人儿般粘人的小娃娃手里。
原本是他顽皮心起故意吓唬她,没想到反被捉弄地落荒而逃,以至于五年后的武林大会,当他以一人之力挑败擂台上三十多位各门派弟子后面对她一人时,不得不又一次仓皇而逃。那一年他十八,她刚满十岁生日。
再过一个五年,二人喜结连理,婚后依然喜欢玩儿些相互捉弄的小把戏,晚池武功造诣日深,却不得不承认夫人是她的克星。
程夫人却是个极明白事理的妇人,两人一路攀谈,她已将怀衫的大致情况于不经意间打听清楚了,听闻她失去记忆,心里泛起一丝狐疑,及至知晓她怀有身孕,又体贴地将竹林馆唯一一床宽阔舒适的大床让了出来给她。
夜深人静躺在船上,长大眼睛,静听着房间地上地铺里传来的均匀呼吸声,月光自窗户里射进,给酣睡的人披上一件清凉柔和的睡衣。
她极轻地叹了一口气,从来都没有与这名多人同处一室,这个房间也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她轻悄悄地披衣起床,小心翼翼的穿过地铺,当然不会知道秋褚宫大多是习武的女子,在她打开房门的时候,已有很多人睁开了清醒的睡眼。
晚风有丝微凉,她披衣坐在院子中幽幽竹林下的小桌旁,呆呆坐着,这种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的感觉很好。
“叮铃铃!叮铃铃!”院外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响声,刚好三次,停下。
她朝外面望了望,起不情愿地起身,走了出去,“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
院外一棵大树底下立着满脸含笑的楼宗域。
“我今日看见了临水阁阁主戴云辉前辈了,也许可以向他打听打听你的事!”
“现在战事要紧,谁有心思理这个!”她的语气有丝不耐烦,看他一脸惊愕,才缓缓加了一句,“等一切结束后再说吧,我不及的。不早了,你早点休息。”
不知为何,自来到这个地方,她的心总是莫名地紧张、不安、焦灼。
第二日,三位少主和宗域觐见了太子,程皓将他举荐给太子,瑖若自是很高兴,他一点也不避嫌地将四人带到素雅居一处紧闭的房间。
门外何伯已经等在了那儿,见他们来了,拿钥匙开了一把锁,瑖若从自袖中掏出另一把钥匙打开另一把锁,才请他们进去。
房中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地上铺了一层厚实的木制地板,瑖若蹲下身移开石块木板,露出一个如井口般大小的洞。
六人进入洞中上上下下,不知绕了几个弯才出得洞口,却是到了两壁山崖底下的一个山谷。
谷底有一处深潭,很少有人知道涯月洞的潭水大多是流到了这里。
何伯和瑖若一块儿从潭底捞起了一带黑乎乎如手掌大小水淋淋的圆球。
“这个就是薛籽鑫当年留下来的霹雳弹,薛流碧带着大批军队围剿竹林山庄,何伯暗中带着一批人运了一部分霹雳球到这里。”
“薛流碧竟然攻进了竹林山庄?”程皓看了看黑球,沉声问道。
“是啊!薛籽鑫的旧部们集体失声,隐忍十几年就是为了他们的少主回归!薛流碧若不是一切筹划妥当,也不会一击得逞!是我们小瞧了他们的实力!”
“那么现在我们有多少胜算?”
“那就要看我们谁能够先复苏霹雳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