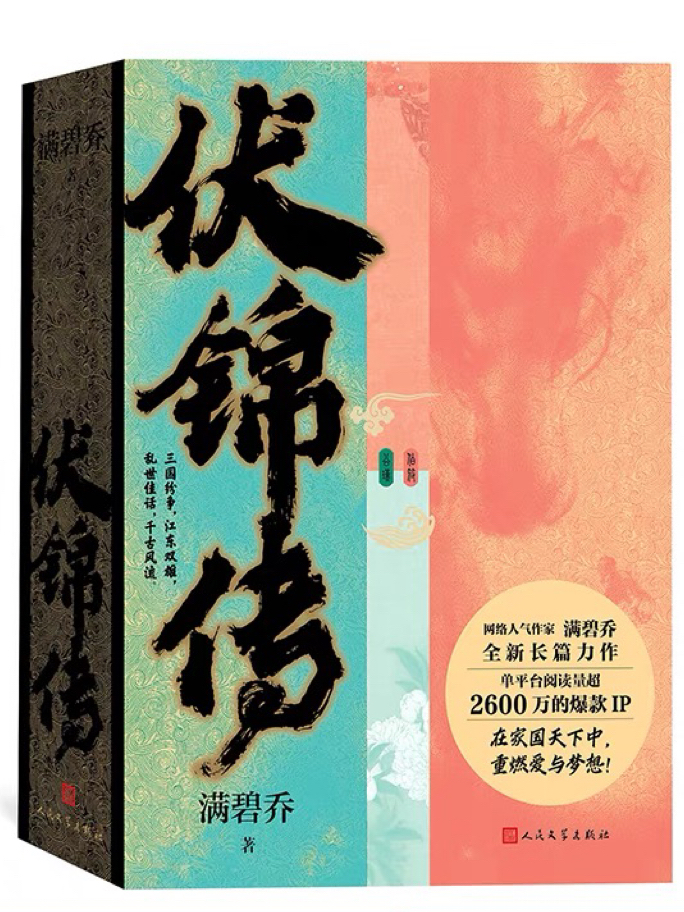怀衫呆了下才牵着孩子离去,没过多久,她伸出出现一双无声的眼睛,贴着墙面泠然注视着她渐行渐远的影子,嘴角噙上一丝浅笑,转身缓缓离去。她怀里的小孩子睁着漆黑明亮的双眼,不解母亲的表情的变化,眉头微微蹙着,肉呼呼的小嘴嘟着,用力嗦了口手上的糖人儿。
她在狭小的熟稔地小巷中穿梭而过,沿着墙根没走几步,踏入一座建造恢弘但已有些年岁的大院儿。院门的牌匾上一块漆黑的模板,上面铸上去的五个烫金大字只有些残留的笔画。
她踏入院子里,手上除了抱着个孩子,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不像是逛街,倒似特地去给还一个糖人儿似的。
“小姐回来啦?”坐在门口石墩上打着哈欠的老夫子看到一抹俏丽的色彩,揉了揉眼睛,笑眯眯问候道。
“哎!老伯!”她冲着老伯暖暖一笑,踏入隔壁的当铺,掌柜抬头看了她一眼,从左上站起,走到前台,恭敬地俯下身。
她点了点头,抱着孩子走到后院,房门开阖,三人瞬时没入黑暗之中,原来这间房外表和普通的卧房无异,窗户纸从外面看是雪白,内里却漆黑一片。掌柜小心翼翼地摇亮火折子,点上一座煤油灯,垂首她对着她立着。
“雪绣坊的消息没错,是她。”她有些疲倦地拖了张椅子坐下,丹昕吃完糖人儿,黏糊糊的小手在她素雅瑖滑的外裳上擦了擦,她也浑不在意,瘦削的瓜子脸埋昏黄的烛光里,沉默着。
“看来我们无法用她达到我们的目的。”
“将赌注押在她身上原本就是个错误,也许我得考虑再嫁了。”她淡淡地抬起头,目光看尽掌柜的眼睛里,“张伯丹昕以后就交给您了,我宁愿她日后有个被人唾弃爱慕虚荣的母亲,也不想让她卷入这一场风云。两年的时间已如此难熬,我们还有几个年要去等待,丹昕却不能等,您可否立刻命人将她送走,送到一处诚实可信的农家,让她平安长大。”
“可、小姐、这可是主人唯一的骨肉,您的忍心与血肉相离吗?”张伯犹疑地说到,面色有些许不忍。
“不想,可不想又能怎么样?难道让她嫁过去受尽别人的白眼?”
“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么?一旦康玥晁性命危急,南疆那边是不可能没有动静的,到时候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利!”他的脸上绽放出兴奋的光芒,目光里满是期待和憧憬。
“他是天子又居住深宫,靠近又谈何容易。所以,我更要嫁过去。”
“嫁给柳枝源,就真的可以接近皇上么?”
“至少有那么一线生机。”她下定决心后就不再说什么。张伯吹熄油灯,抱着小丹昕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黑夜如潮水缓慢地朝她席卷而来,她闭上双眼,僵硬而麻木地搜寻着,
明知周身除了一片漆黑就是无边的空虚,她仍不屈不挠地搜寻着,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丝昏黄的光芒,一盏油灯在远处若隐若现,握住油灯的那个人,昏淡的白装,若袅袅雾气,用嘴轻轻一吹,就能散了的。
“流碧哥哥!”她却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急迫地朝他追去,那袭模糊的身影永远那么遥不可及,只拿一双爱怜的目光柔和地看着她,泻落一地的疼惜和无奈。
“流碧哥哥,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你可否告诉我?”
“冰展,放下吧。永远放下吧。带着我们的丹昕去过平静无忧的生活,远离这一切吧,我们再怎么挣扎,都挣不脱那个牢笼,那就让自己过得轻松些,可好?”
“可是那些你的梦,你的伤,你的痛呢?流碧哥哥,我知道你不曾忘,那些我们忍辱负重向望不能相守的日子,我原不该脆弱,而是带着这一切义无反顾地往前前走。流碧哥哥,你一定要好好看着我,看着我如何让他们血债血偿!”
怀衫这些日子不时朝雪绣坊跑,因为她给瑖若设计的那件衣裳,不时有新东西从头脑里冒出来,不是这儿挑个边儿,就是领子上绣朵暗花,不得不朝他们买些颜色、用碎了的窄布条。
如此过了十几天那件衣服总算做成功了,但她还觉得不是也很满意,心里躁地很,于是拿着衣服,想麻烦店主看看还有哪些地方不妥,以期再做一次大的修改,这样剩下的几天就找着方法打发了。
她如往常一样抱着恕儿从农舍出发,脚步轻快与任何一个路人并没有任何两样,只是她的周身,要么身后隔着几步,要么并排着在对面的摊位,总有几个人不远不近地跟着,若不出现意外,是不会打扰到她半分的。
她走到大街上没多久,模糊听到火鞭噼噼啪啪的声音,这才发现两旁的街道商铺上都张灯结彩,要么门廊上挂一串火红的辣椒,要么绕着两盏灯笼,“这是谁家娶亲,居然如此大的仗势?”她在心里想着并不在意。
迎面走过去,行人自觉地朝两边推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骑纯种白马,座椅上的人巍峨雄壮,刚硬的铁甲上用带子绕着一朵红花,更添了一份铁汉的柔情。那人约莫四五十岁的年纪,须髯飘飘,双目如炬,这样看来,倒使人忘记了他的年龄,整个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他整个人本身身上来了。
怀衫将恕儿从地上跑起来,避开到一旁耐心等待着,没过多久,白马的身后跟着一头同样体型雄姿勃发的黑马,一身红衣、披着盖头的嫁娘稳稳当当地坐在上满,紧贴着他迤逦而行。
光是这份默契以及气势就能为京城各家人士津津乐道了。谁知将军一时兴起,挑起了新娘的红盖头,她的脸上闪过一丝讶异,随即淡淡的笑了。目光如水,只看着马头,对于四周打量的目光视若无闻。
人群不知为何静寂了半响,就像世界突然凝滞了一样,“这个新娘子长得真美呵。”不知谁一生低呼,人们争先恐后地附和着。
怀衫也禁不住抬起头远远打量着她,略施粉黛沉静的脸庞,一双细滑的柳眉,嘴唇微微弯着,始终保持着一份端庄典雅的微笑。光是这份镇定已足够与众不同了。
将军果真是个性子豪放的人,他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头伸到新娘的耳侧,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中,她听后也只是看了他一眼,宠辱不惊地朝前得得行进。
“我要让整个天下的人都记得你的样子,记得你是我柳枝源的妻子,这样你就永远是我的了。”他一声爽朗豪笑,策马扬鞭,疾驰而去。
盖头遮到额角的新娘子并不示弱,用力踢了踢马肚,拉紧缰绳赶了上去,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在众人视线里越驰越远。
“柳将军自二十八岁远守北后从不曾起娶亲的念头,这次回家探亲,反倒成就一桩美满的婚姻,果真是天赐良缘啊!”身旁一人对着同伴低声说着。
“也不知道这女子是何方神圣,竟能在短短几个月里俘获他的芳心。”
“也没听说是哪位大户人家的小姐,莫不是早就在北境认识了,借探亲之名,回家成亲的?”另一个人猜测道。
各种各样的声音夹杂进耳朵,怀衫的脚步却因一句话而停留了很久,“这柳将军的哥哥虽是当今太子的岳父,却是凭着一身真本领,固守北境,才得到皇帝的中用的啊!”
怀衫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柳枝源奉命去北境的时,皇帝从草野登上皇位不过五六年,想到柳尚书还有这么个襁褓中的嫡孙女儿,故为太子许下了娃娃亲,那时他们就注定了会相守一生,为了江山稳固,也为了各自家族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