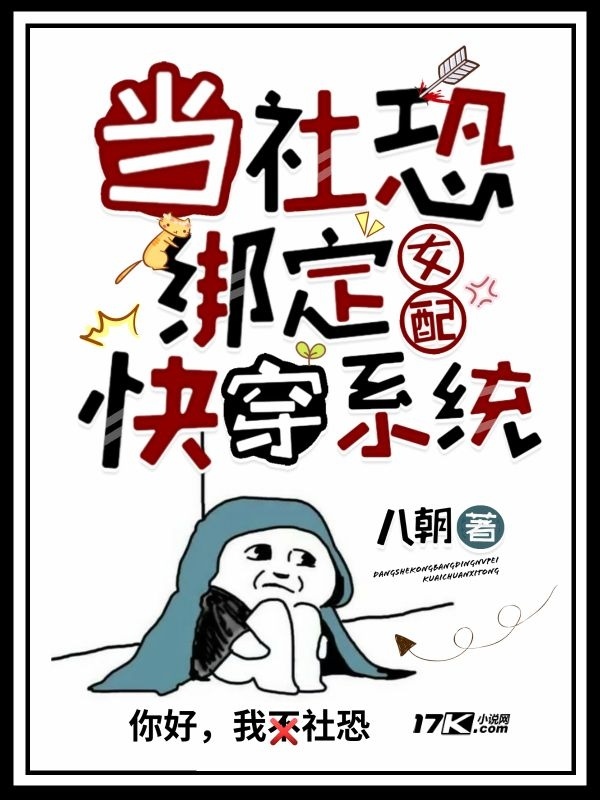下了火车,在当地长途汽车站,程成和肖安见到了女人的丈夫。孩子见到爸爸,兴奋的只要爸爸抱着。几个人用汉语客套了一番,两口子又用自家的“外星话”做了简单的交流,最后终于登上了开往大苗山的大巴。
说是大巴,其实就是一二线城市淘汰下来的报废面包车,允乘十几人的那种。这破车除了喇叭哪都响,这要在卫东市的二手车市场,顶天了也就卖个一两千。
车里座位上的座套还算齐整,只是好像从来没洗过,原本的花色又加重了十多个色号,甚至有点发黑了。肖安率先上车,排着车内的乘客往后坐。这一坐下去,整个人都被四周的霉臭味儿包围了,加上前座的乘客有点儿狐臭,这味儿,呛得他差点吐了。不过好歹他挨着窗户,打开车窗的那一刻,肖安似乎找到了重生的感觉。
一路上的颠簸,耗尽了车上每一个人的体力。
程成坐在肖安旁边儿,和女人的丈夫坐一排,中间隔了一个小过道儿。为了不让自己坐吐了,他觉得有必要分散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大哥,怎么称呼?”程成把头转向女人的丈夫。
“我叫***。”提起自己的名字,男人有点不好意思。
“这么说,您球踢的不错呀?”肖安从程成的肩膀后面探出头来,加入聊局。
“嗨!他们都这么问过我,”男人无奈的摇摇头,“我哪会那个。”
“郝大哥,你是大苗山人吗?”程成有一搭无一搭地问道。
“对!我就是在那出生的。”***把头歪进过道儿,眼睛一直盯着汽车的挡风玻璃,坑洼不平的土公路像是被快速扯动的胶卷,在车底下碾过。这男人对多年未归的“家”,似乎有些期待。
程成看向***。眼前这个人,个头儿跟他女人差不多高,比女人还瘦,早已谢顶的头皮,仅剩一圈黑白掺杂的硬发碴子薄薄的浮在耳后。看不出他的年龄,唯有沧桑还在雕刻着他的面庞。
程成心里发酸,“郝大哥,你看还有多久能到啊?”
“快了!翻过前面的山,再走几十里地,就到大苗山寨了。”***瞄了瞄车外白花花的日头,“差不多傍晚咱就能到了!”
程成暗暗叫苦,心说你***说话也太夸张了,还有一座山呢,到你这就算快到了?他干脆眯起眼,不再说话,心里跟这座山打起了持久战。
过了许久,车停了。这时的天已经擦黑。
程成被***拍醒,颠簸了快一天,胃里一直在翻腾,硬是让他生生的压了一道儿。此刻突然被人拍了一巴掌,所有的弦儿被崩断,程成差一点儿吐出来。
在这站下车的就只有程成和肖安,还有***一家。
周边的一切山石树木慢慢陷入昏暗,唯有破面包屁股后面的两盏小红灯渐行渐远,消失在蒙蒙夜色中。
随之而去的还有肖安心里面最后一撮撮安全感。背后的大山漆黑延绵,无边的尽头淹没在深蓝色的夜空中,像个巨兽正等待他们自己送上门来。
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安静得连趴在***背上早已熟睡的孩子的鼾声都能听得清楚。肖安小心翼翼的跟在***身后,坚持让程成踮后,唯恐这深山老林里有什么玩意儿不小心成精把自己抓去结婚如何是好?毕竟自己警察还没有当够呢不是?
几个人排成一队沿着脚下土得不能再土的叉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倒不是因为素质有多高,而是脚下的山路太窄了,根本容不下两个人并排行走。半山腰上,丝丝凉风扑面而来,倒比在车上时舒畅了许多。
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他转身对身后的两个外来客说道,“二位,咱们得从这里下去,这条路通咱们山寨。”
肖安上前跟了一步,顺着***手指的方向看下去。卧槽!肖安一闭眼,这也叫路?无非是少长了几颗草罢了。跟这比起来,刚才走的山路都可以堪称“阳关道”了!这都不算什么,***所谓的这条路还有着将近七十度的大斜坡!黑灯瞎火的都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怎么下嘛!
“能不能绕路啊?这坡太陡了,你背着孩子多危险!”肖安急吼吼地“设身处地”的为***着想。
“大兄弟,咱们山寨就通这一条路。”女人感激地回应着,心里更是觉着这个艺术家志愿者心眼儿好。说着话,她头也不回,当先下去了。
肖安心中叫苦不迭,心说大姐,别“咱咱”的了,这山寨肖爷我再不想来第二回了。
***不再搭腔,抱紧孩子,也下去了。
肖安站在原地没动,他还在做着深层次的灵魂拷问,我是谁?我在哪儿?
程成从后面拍拍肖安的肩膀,“薇薇安,郝哥说两天以后有出山的大巴,要不你在这等等?”
两天?那肖爷不是快饿死了,就是被快饿死的哪位“爷”当点心了!肖安鼓起勇气再往坡下瞧去,连程OK都爬下去一大截儿了!
“程OK,你个没良心的,要不是肖爷找人买票,你这会儿还在卫东干瞪眼呢!哎!你等等我啊!”肖安硬着头皮探下了一条腿,可嘴上却是不饶人。
不行,这样不行。肖安急忙把腿收回来,他的脑袋嗡嗡直响,眼睛开始发飘,要是愣下,自己非得张下去不可。肖安灵机一动,干脆!背过身来,跟爬山似的往下爬,虽然慢点,但稳呐!以免跟保龄球似的把下面那几位也捎上就坏了。
打定主意,肖安慢吞吞地开始往下爬。可想象总是丰满的,现实还是骨感的。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太“说走就走”了,自己连双旅游鞋都没来得及换,还是上午临出来时穿的那双“骆驼”牌儿皮鞋。
山石多磨砺,这皮鞋不但不跟脚,还相当滑,肖安好多次,差点儿没在山腰上劈了叉。这还不说,皮鞋也没少遭罪,这段坡道,皮鞋似乎经历了它一辈子的坎坷,早上还相当“板生”的黑皮鞋,这会儿就跟泥捏的似的。
好容易下到坡底,没走几步又开始爬山,刚才还寂静无声的世界突然变得“蛙叫虫鸣”起来。不过程成和肖安没那心思品鉴游玩儿,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两口子后面儿爬了将近三个多小时,气管子都快捯炸了。
***和妻子反倒是健步如飞,从小在山里长起来的人,这点儿山路不算什么。
到达山寨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山寨不算大,但十分分散。月色中,肉眼能见的也不过是相距二三十米的两三处人家。程成和肖安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山寨里这种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这里的木屋都是被数根粗壮的实木“举”在半空的,只有顺着梯子爬上去,才能回到家里。
山寨里一片漆黑,只有***驻足的“高跷木屋”还有一线烛火。
“郝大哥,你家有人啊!”程成疑惑地看了一眼***,又努力的向木屋的窗户望去。
“是阿兰。”***有点激动,他来不及解释,当先一步爬上了木屋。
程成和肖安相互看了一眼,更加疑惑,听名字是个女人,不过敢当着媳妇的面这么急不可耐,那八成是姐姐或者妹妹吧?
“阿兰是我们苗语母亲的意思。”***的媳妇瞧着两个志愿者的神情怪异,急忙上前一步解释道。“我们回来之前托人给婆婆带了口信儿,所以她老人家一直在等我们。”
原来如此,程成和肖安也跟着女人爬上了木屋。
木屋比想象的宽敞,而且脚下的木板很结实,跟直接踩在地上没什么两样,只是回响儿大些。
还没等程成完全适应木屋里的烛光,就感觉从屋子深处突然窜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来,被***一下子抱住。吓了程成和肖安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