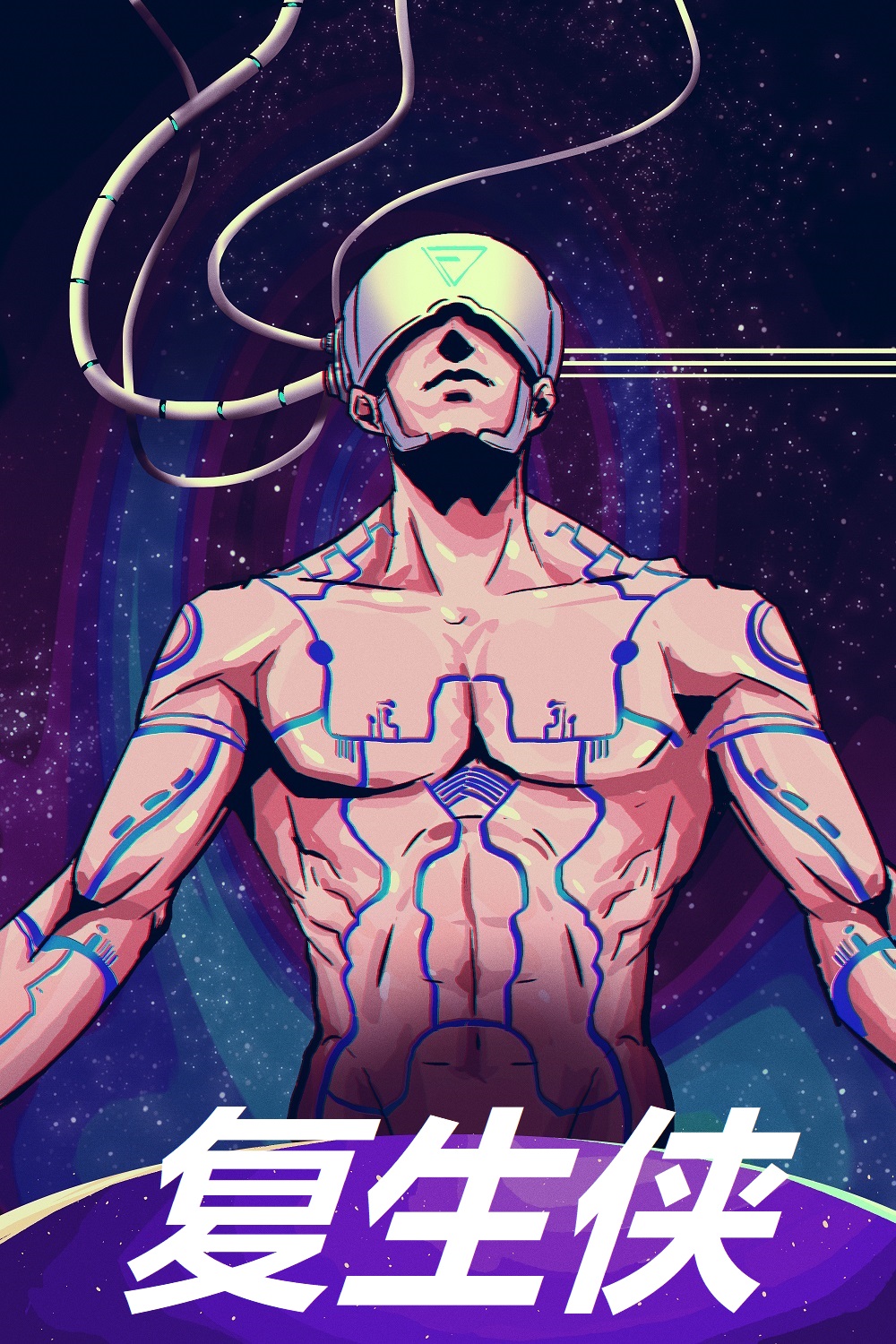那是一久七八年的夏末秋初,粉碎***刚刚不久,在老城一所不起眼,破烂的小学里,两个少年坐在了同一张学习桌。两人互相介绍,我叫大明,我叫建国。。。。。
两个人不爱学习,打着布丁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麻子脸的琉璃蛋,和撕下来用书皮叠的面包,和在烟糖公司垃圾堆上刨的烟盒,叠成烟纸,那是个年代最好的玩具之一。一个学期下来,书包里的书烂的没皮少页,纸面包和烟纸倒是攒的不少。玩这些游戏,他俩也有输的时候,输了就抢,抢还不给就打。于是有用不完的书皮,班上同学的课本有一半都没了皮。
期末临考,俩人啥都不会,好在老师义务为他俩额外开小灶补课,才期末考试勉强及格,没被留级。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年少不知愁滋味,大明和建国每天日复一日,就这样没心没肺,嘻嘻哈哈的渡过了每一天。直到两人有惊无险的考入了同一所中学。
那个年代生活条件苦,那时的大亨和大明,人比黄花瘦,两人穿着洗的发白了的裤子,一双布鞋补了又补。吃喝上面,除了过年过节才能沾上些荤腥,吃个炒菜这些奢侈的美食,在平时里,别说这些东西,就连喝口鸡蛋挂面汤,那都是痴心妄想。翻看小人书,特务总是大吃大喝,馋的俩个人咽口水。。。
办法总是有的,那时候家家有电视的不多,在家属院的楼上都有自己按的天线,他们下学后就跑到楼上去撇天线,天线有铜,有铝,卖了钱,就去新市民街路口,哪里有个南方人挑扁担卖混沌,俩人用换来的钱去买混沌喝。两毛钱一碗馄饨,两毛钱一个肉馅的盒子,咬一口‘滋滋‘满嘴流油,喝一口馄饨,美到心底了。但吃的时候总感觉警察拿着枪,在后背站着指着你的头,有些别扭,但又顾不上那么多了。
有时候还能剩几毛钱,心惊肉跳的买盒邙山的地锅炮,加上一盒火柴,跑到人民公园的大象滑梯上面,你一根,我一根的怼。不会抽烟,却抽的猛,抽的快,一会捣的满嘴片的焦油,苦不拉几的。虽然很苦,但感觉自己一下长大了许多。丁儿俩总有很多想法,安阳河里钓麻虾,爬上树去掏鸟蛋,磨的裤裆都是大窟窿,有一次他俩忘记是那一个了,没抓稳,从树上粗溜下来了。树干磨烂了本来就补过了的裤。
那个年代,物质贫乏,可玩的地方不多,两个精力充沛的男孩子那能安静的坐下来。大明和建国,每天除了睡觉能安生一会。剩下的时间,都在无事生非。给老师的28大车放气,拽班里小女生的辫子,往厕所茅坑里扔啄木鸟,炸的同学一身屎尿,往隔壁女厕所扔土坷垃,女同学天天去班主任那告状,总之有他们的地方,鸡飞狗跳,人喊马叫,暗无天日,人人怨声载道。每次叫家长,大明的父母回去除了口头教育一番后,接着少不了一顿好打,大明的鬼哭狼嚎伴随着他爸手中的鸡毛掸子,上下翻飞,散落了一地的鸡毛。
然而建国的父母几乎很少来,班主任也很少让他叫家长,虽然每次犯错捣蛋的都少不了他。建国的父母是残疾人,家里就他一根独苗,父亲是盲人看不见,母亲虽然不是盲人,但走不了路,坐在一块木质的板子上面,下面按了几个轮子,用手撑着地面,滑动板子移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建国是从小受苦习惯了的人,大明家条件好些,常隔三差五的带建国回自己家吃饭,每次建国都是狼吞虎咽,从开始吃到最后,不抬头。大明的父亲在报社上班,母亲在一家具厂当工人。
初二的夏天,班里插班了一位女生,一位漂亮的女孩子。
四面齐剪的整整齐齐,乌黑漆亮的头发,一身洁白的连衣裙,苗条的身材,皮肤白净细腻,羞涩的一笑,两个小酒窝。女孩子站在讲台上大方的介绍了自己叫什么名字,然后坐在班主任指定的位置。
班里只有坐在最后一排的大明和建国是一人一张桌,没有同座,也没人敢和他俩坐同座,不仅没人和他俩坐同座,班主任还把他两个分开,一人一张桌,可想两人坐在一起上课,该有多么让人头疼。
阿芳被安排和大明坐一起,大明连忙用手擦了擦凳子上的浮灰。阿芳坐下,大方的对大明报以微笑,不经意的四目相对,大明口干舌燥,心中一阵春风清爽的拂过,吹过他的心田,整个一堂课迷迷糊糊,像是在做梦。
从此他变的不再是他,每天提前来到班里,把课座用袖子擦了又擦,直到亮的能映出一头汗水的自己,然后憨笑着把课本摆放的整整齐齐,自己也坐的笔挺。上课注意听讲,下课也不知是真是假,装着不懂,向阿芳请教学习上不懂的问题,阿芳总是不耐其烦一遍又一遍的教到大明说会为止。
有一次建国被人用板砖开了瓢,气呼呼地找大明去帮忙。平时大明立马就跟着他去了,然而这次大明,拒绝了他。
‘以后,你别再找我耍了。。。‘大明转身留下一句话,头也不回的走了。
‘大明,你,你,你到底咋了。。。‘大亨绝望的,迷惑的歇斯里地望着大明远去的背影。吼叫着。
女孩家住在大明家前面俩路口,但每次下学大明都跟在女孩后面,直到看到阿芳走到家属门口,才往回走。
阿芳也知道,但装着不知道。每次到家属院门口,都回头对大明一笑。大明手指无措,慌忙的往树后躲,一头撞在树干上。
晚上大明匆匆的吃了两个大馒头,喝了一大碗稀饭,跑到自己屋子里,关上房门,把姐姐梳头照的镜子拿出来,轻触头上鼓起的大包,好像熟透的桃子,轻轻的搓揉皮就掉了下来,大明疼的呲牙裂嘴,却幸福的笑了。门外是父亲的厌恶的谩骂和母亲心疼的唠叨。
有人在人民公园见过阿芳和大明,有人见过俩人在放学的路上牵手回家,有人见过大明在早上下第一节课的时候,从怀里掏出两块烤红薯,阿芳满脸惊奇,满脸通红,一人一块啃着吃,满满的香味,整个教室里香喷喷的味道。大明揉着被烫红的胸口,傻傻的笑。阿芳眼眶中充满了泪水,声音有些颤抖,‘你啊,神经病‘
元旦的时候,大明送给阿芳一张明信片,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海报,上面写了一番祝福鼓励的话。
阿芳送给大明封信,大明激动了半天,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信纸,上面却一个字都没有。
那一年,一场大雪来的有些早,冬季运动会如期举行。大明穿着一身蓝色运动服,嘴里‘呼哧,呼哧‘吐着哈气,在空气化为一股股的白烟,两只手掌不挺的搓着,产生出热量连忙捂住耳朵,男子八百米长跑开始了。大明望望不远处的阿芳,她挥舞双手,喊着加油,四目相对,大明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在裁判的一声哨响,飞一般的跑了出去。一圈200米。大明头两圈领先,班主任也漏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第三圈,在转弯处,大明跑的太紧,突然脚下滑了一下,摔在地上,惯性太大,打了几个滚。大明勉强站起来,脸色也挫了一大块,一瘸一拐,最糟糕的是鞋底也掉了,脚露在外面。
大明下意识的看着远处,阿芳担心的看着她,双手捂着嘴,不知如何是好。大明一咬牙,心一横,把那只鞋甩在一边,光着一只脚,甩开胳膊,继续奔跑。全班同学都惊呆了,继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都扯着嗓子喊起加油的口号,整个操场沸腾了。
跑完最后一圈,大明最后一名。当他颠簸着走完那最后十几米,脚上的袜子早也磨透了,脚被跑道上的碎石子和煤渣上扎的流出了血。
同学一哄而上,把大明架到凳子上。一抬头看到满眼通红的阿芳,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我没事,我一点都不疼‘。大明说完挣扎着又站起来,脚底一软,一个仰八叉,四肢朝天摔了个实实在在。
哨子一响,一身雪白运动装,一双洁白的回力鞋,衬托着阿芳修长匀称的身材,男生们都看傻了。阿芳跑的飞快,就像一只雪白的海鸥,掠过操场,从同学们的面前掠过,直接扎进大明的心海中。
同学们都在跑道前欢呼雀跃,阿芳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她快乐的向大明挥手。突然,天昏地暗。。。。。。
大明把建国身上的兜翻了干净,又东拼西凑,买了个烧鸡和一些水果,第一个跑到医院去看阿芳。
‘我没事,你看我气色多好‘阿芳招呼大明坐下。阿芳住在双人间病房,礼物放在桌子上,地上,堆起老高。有麦乳精,高档糕点,奶粉,竟然还有雀巢咖啡。有些东西大明只在家里14村的黑白香花电视机上见过。
阿芳的妈妈招呼了几句,出去了。大明和阿芳呆呆的沉默。大明突然笑了,问阿芳‘你看你,还真是一点事都没有,我看你过几天就能回学校上学去‘
‘恩‘阿芳使劲点点头,眼中闪动着泪花。左面的脸上包着块大大的纱布,晕倒脸着地摔出了血,让人看了心疼的不得了。
洁白的床单,洁白的窗帘,阳光慵懒的照进来,照在阿芳有些疲倦又粉扑扑的脸上,旁边坐着‘呵呵‘傻笑的大明。
过了三天,阿芳还没来上课。大明眼巴巴的看着窗外的校门口,望眼欲穿。
早上天还没亮,大明就跑到灯塔路小学门口,那有个烧红薯的炉子,烤红薯的老头的儿子是他同班同学,他知道那炉子里每天都留着俩干瘪的红薯老板不收。他捞了两三个,连忙揣进棉袄里,天好冷,下着急促的雪花,冷风直往怀里钻。大明一溜小跑着去了医院,路上已经有积雪了,跑的有些急,摔了几次跟头,不管摔的多狠,他双手都紧紧的捂着胸口,里面是滚烫的烤红薯,阿芳喜欢吃。
推门一看,才知道阿芳在他看望她的第二天就出院了。回家的路上,大明昏昏沉沉,不知道咋回的家。
母亲心疼的给大明用酒精在胸口消毒,大明的胸口烫出了几个小拇指般大小的燎泡。大明楞楞的看着天花板,形同雕塑。父亲闷头抽着烟,嘴里照样是喃喃的谩骂着,母亲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抹着酒精。
班主任把大明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的骂了大明一顿,‘马上就中考了,至从阿芳和你同桌,你学习成绩刷刷的往上赶,最近是怎么了?又破罐子破摔了?你这样对的起阿芳吗?班主任一激动,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上。吓的大明一激灵。
接下来的一段话,犹如晴天霹雳,让大明想都想不到,防不胜防,彻底傻了眼。
阿芳的奶奶是日本的遗孤,中日战争后阿芳的奶奶嫁给了中国人,经历了*****,粉碎***,到改革开放,一系列的运动,所幸阿芳的奶奶毫发无损,她爱上了养育她的这个国家,并一辈子没回去。
阿芳的日本亲戚在中日友好建交后来大陆几次,来探亲的时候找到了阿芳的父亲。从此每逢佳节总有书信的来往。虽然阿芳的父亲可以回到日本去,但阿芳的父亲从没那么想过。但为了阿芳,他不得不这样做。阿芳是急性心肌炎,在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还达不到治疗这个病的水平。
就这样,阿芳通过海外关系,去了日本。
大明机械一般的回到了教室,坐到自己的座位,‘咣当‘一头扎在桌子上。双手抱头,一堂课没动一动。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滴落在课桌上。一滴,两滴,三滴。。。。
大明回归,建国喜出望外。整个年级重返鸡飞狗跳,人喊马叫,暗无天日状态。
都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两人坐在学校楼后面高高的粪堆上面,‘建国,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啊,我的理想就是将来男女老少都的求我办事,特奶奶的,让他们打小看不起我‘建国死命的琢了一口地锅炮,恨恨的说,眼中泪光闪闪。
‘你的梦想呢?大明。别光说我啊‘建国拍着大明的肩膀。
‘我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拿刀‘大明一脸平静。
建国一脸惶恐‘拿,拿刀。。。‘
‘不是拿刀,是拿手术刀,我要当医生。。‘大明满脸憧憬的望着一轮夕阳,喃喃的说‘白大褂,多么洁白,和阿芳的白色连衣裙一样。。。。
‘咱俩拜把子吧。‘建国手舞足蹈。
‘恩。。。‘大明眼含热泪。
片刻,建国买来两瓶小烧。点了三根香,跪下来磕了三个头。抬头,一人头上粘着个塑料袋,一个脸上黏着一张卫生纸,相视大笑。
看着瓶底浅浅的酒精,大明仰头喝了个干净。
‘呵呵,你说巧不巧,你说可笑不开玩笑,我,我和阿芳竟然一个摔倒一个晕倒,妈的,该死的运动会,哈哈哈。‘大明笑的很难看。
建国不知所措。
‘噗通‘喝醉的大明倒在粪堆上,嘴里嘟囔着,喘着粗气,两行热泪流淌嘴里,‘好咸,真特么的苦‘
那天的夕阳很美很美,大明看着却很凄凉。
就此别过,一晃,过了好些年。
在聚宾楼,同学会上,大明和建国又聚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