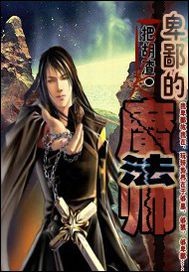他转身又跑,来到一个灯火通明的极其宽敞的大厅,里面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他喘着粗气停留了一秒,以便观察一下,该往哪个方向跑。他看见了一个装饰典雅敞开而无顶的咖啡馆,其上方的犹如超大尺寸的肋骨似的巨型拱顶构架,看起来就像是用金线编织而成的,还看见了黑板,不知所措的他,顷刻之间竟觉得自己是进入了一艘巨大无比的宇宙飞船。他此刻竟然泛起一种荒谬绝伦的念头——这里是宇宙飞船!咦?奇怪宇宙飞船是什么东西?他扭头向右,看见了一个很大的免税商店,有人手里拿着大皮夹子走进去,有人提着大塑料袋离开,他明白了,这是一个航空港。他所在的这一层标的是“上层”,中间有个巨大的洞口,可以从最下层一直看到最高的玻璃穹顶。
不管在哪儿:反正他必须在被追上前从这里消失———尽管周围闹哄哄的,他也能听见从楼梯间里传出来的追赶者的脚步声。他又拔腿开跑,可是刚跑了几步,他便嘎然而止。
原来在前方很远处有金属物———这东西刚才是隐蔽在一个墙壁凹进去的地方的———在明亮的光线之下闪烁了一下,便见那边随着一个根本来不及弄明白的飞快的动作,一名路过的身上穿着一件长及脚背的皮大衣的行人的脖子就被割断了!
托尔吃惊得双目圆睁。他竭力喊叫,可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却只不过是一串沉闷而沙哑的声音。那行人的脑袋还在他肩膀上原来的位置停留了似乎长得不得了的两三秒钟,才噗嗵一声掉下,在铺瓷砖的地上滚了几下,鲜血随即从这个陌生人的无头躯体上喷射而出,而这躯体继续保持立姿,又坚持了令人不堪忍受的一秒钟,才在他手握两只咖啡杯的双手松开之前,倒在了地上。
四面八方响起了尖厉刺耳的喊叫声。人们纷纷乱跑,虽然他们全身完好无损,但其无头无脑地瞎跑,与被黑皮肤男人砍断了脖子的人毫无区别。
黑皮肤男人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大弯刀,脸上若无其事地从刚才隐藏的墙壁凹处走出来。
随后,在离死者和他的大滩鲜血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听起来像是两把钢刀在相互使劲砍杀。
托尔吓得直喘粗气。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把锋利无比的刀剑快得不可思议。两个身穿长大衣的人,在离他不到五步远的地方相互砍杀的场面,仿佛是从一部历史惊险故事片中剪下来镶嵌在眼前一般。刀与剑在航空港大厅里的人造空气中划过,发出嘶嘶的响声。
兽爪十字!托尔在古代战士的武器上看见过这种符号。此时,他在梦里见到的场景又在他心眼前闪现出来,模糊了他观看战斗场面的视线。这个陌生人手上的,正是托尔梦里所见的宝剑!托尔想像着刀剑冰冷的钢铁碰上自己手指尖的感觉,犹如婴儿用很不灵巧的动作去触摸一般。
“小伙子!”
手执宝剑的战士的喊声,猛然将托尔从白日梦中拉出来,使托尔返回现实之中;或者起码是进入现实世界的疯人院中。在他眼角的余光里,从地下停车场跑出来追赶自己的人,正朝自己跑过来———与他相距顶多两步之遥。托尔脚不离地,一旋转便转到左面,但随后又立即转回来,弓身从惊讶的追赶者身旁一飞而过,继而冲进楼梯间,顺着楼梯向下疯狂奔跑。
他内心惊恐以极,一边尽力一步跳好几梯,顺着通向底层的楼梯飞,一边在心里思忖,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航空港。这一切通通不属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他早就知道。但这世界却如此荒唐、疯狂而又野蛮,简直无法让人理解。他必须尽快回到修道院的家里,那是他迄今安度人生的地方,他只想在回去之后把门闩上,永远不再想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所。他得赶紧逃脱绑架者的追杀。
托尔到达底层时,除了自己的,听不见别人从楼梯间追下来的脚步声。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慢奔跑的速度,他不停地用左手把标有拯救人脱离苦海的“出口”二字的门推开,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地冲到门外。这时,他才短暂地停了一下,为的是要确信,在候机大楼前面的人行道上行走的人群之中,没有混杂着挥舞刀剑嗜杀成性的新时代骑士,也没有被砍下来的头颅在地上滚动。
一辆车窗玻璃不透明的黑色豪华型马车缓缓地沿着大道开下来,直接停在他的前面。托尔想也没有想便跑过去,弯腰通过开着的车窗朝汽车里面看,他绝望地想,求救吧,不得了啦!刻不容缓地需要求救!警察都跑哪儿去啦?警察?部队?放跑了这些疯子的疯人院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又在哪儿呢?
托尔的眼角余光里出现了一名带剑的战士,他也在同一时刻里从接待大厅跑到楼外来,在候机大楼前面慌慌张张地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求求您!”托尔气喘吁吁地朝着豪华车里的人恳求道。车里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女士面带笑容看着他。“您必须救我!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女士笑而不答,但托尔却把她的微笑理解为是要他钻进她的车里去。于是他便钻进车里,而后还没有忘记把车门关好。
“喂,托尔。”
托尔吓了一大跳,困惑不解地看着年轻女士。见鬼了,她是从哪儿知道自己名字的?他只在一眨眼的工夫,就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她如何得知他的名字,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眼前的这种情况下,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万分惊恐地伸手去扳车门上的开关手柄,使劲摇了几下却没有成功,显然这车设有保护儿童安全的装置,所以从里面是打不开车门的。而紧接着驾驶座旁边的车门却开了。不等新钻进车里的人把门关上,马夫就驾起车。车轮立即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呼啸而去。
刚才以一个优美的恰如猫一般灵巧的动作落座在车上的男人转身对着他,上半身深深地弯着,脸上呈现出懒散的笑容。这正是那两个在上层层相互斗剑的人中间的一个!
托尔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发出惊呼声。他的脑子里犹如有一只飞快旋转的万花筒,最后,得出了惟一有可能的答案:这个刚坐进来的男人被打败了。不管这些把飞机场变成你死我活的械斗场,在这里进行殊死搏斗的男人是什么人,他们与古罗马的角战士———古代的角战士既然愿意拼命,他们便如愿以尝得到了死———没有丝毫不同之处。
托尔闭上双眼,一边竭尽全力把从泪腺里涌出而流入眼睛的无助而绝望的泪水再挤回泪腺里去,一边默默地开始祈祷。他觉得自己恰似一只任人摆布的羔羊,被装在牲口车里运往屠宰场。既然神已经迫使他无辜地陷入这样的恐怖事件中,那么就应该对他承担某种义务。例如派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把自己解救出去,而后逃到一个远离这个疯狂世界的另一个大陆,将自己保护起来。